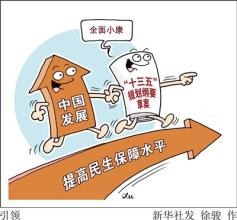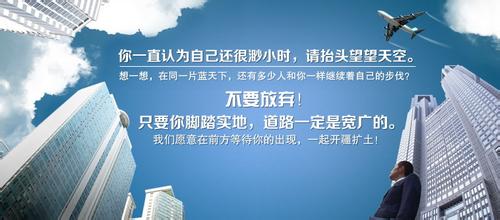曾瀞漪:我记得在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之后的一个星期,有媒体这么说,哎呀,你们现在这些人不要再对中国批评了,你越批评中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它是越不会升的,给中国一个空间吧,你们要了解中国。所以我们现在也许在这样一来一往的过程当中,西方真的是比较能够了解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的政治操作或者他们的表达方式会是怎么样的。 我们就看到在金融海啸之后,很多人在提出是不是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一旦有西方国家或者是有中国的学者提出所谓中国模式的时候,有一些中国的学者说,是,我们有中国模式,但是有一些中国学者也比较清醒,说我们不认为现在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大家应该清楚的看到。所以在西方一种比较吹捧的过程当中,你怎么看,应该怎么去理解中国所谓的经济发展的模式呢? 张力奋:唱好的有些东西可能会为中国今后的10年和5年留下一些不好的东西,或者埋下了一些问题的种子。所以比如说,像在过去的两三年的时间当中,比较多的一个讨论,也就是中国的增长模式能不能持续。所以我们现在谈中国模式,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模糊。当然,第一个层面比较简单的,我们可以是说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 这一点,我想彼此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不管是学界,还是政界,几乎已经有了一个共识。认为以这样的一个高能耗、高劳力成本,这样的一种以加工和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中国是很难再持续下去,所以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模式本身来来说,几乎大家已经是说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第二个层面,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制度性的问题,中国模式曾经有一个说法是北京共识。基本上是指在一个社会从比较专权向自由经济的过渡当中,如果政府还是能够保持住它非常强有力的市场和经济的干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能够产生高增长和高效率。 这个可能是目前有不少西方的领导人,特别是在金融海啸之后,会觉得很羡慕中国领导人,它能够对整个社会的资源,经济的资源,市场的干预,它能够有那么大的自由度。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讨论中国现在所谓的发展模式,开始在对整个一个基本的市场,资本主义的价值采取一个完全否定的态度。 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就是现在这样一个状况下,要把整个一个西方的经济制度,一个市场制度现在就把它笔抹去,我认为这个时间过早。所以我自己个人的看法,现在讨论中国的模式可能还是件过早的事情。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在过去的10、20年当中,在谈到中国的发展的时候,往往有一种感觉,有一种做法,似乎中国的经验是很独特的,几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其他文化都不能涵盖这种经验。其实这种说法我认为是比较片面的,不管是我们看70年代以后,四小龙的经济崛起也好,包括拉美的巴西在70年代曾经也有过6、7年时间,这样的一个经济奇迹,年增长率都是超过10%,其实中国过去10、20年所经历的东西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这样的一种高增长是否能够持续,而这种持续以后,是否这个增长本身已经埋下了很多问题的影子。

我们就可以看到巴西其实在70年代以后,80年代末期,它是经历过一个非常、非常低荡的经济萧条,特别是一个非常高的通胀时期,而这些情况在中国以后是否会出现,我们现在可能都会打一个问号。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