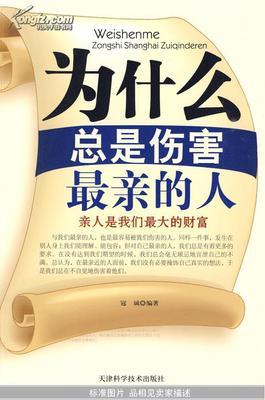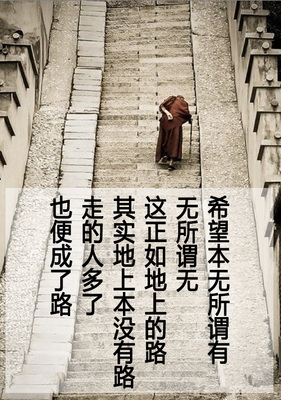同年5月,美国诊断产品公司DPC被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监会处以480万美元的罚金,其在中国的子公司天津德普生物制品公司被控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向中国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及国有医院医生行贿,总额达160多万美元。 2005年也是中国医患纠纷频发的一年,“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引起举国上下关注和讨论。国家审计署在这年6月发布的报告中,披露对卫生部及北京市所属十家医院2003年度的财务收支及相关药品、医疗器械购销情况的审计结果,称2001年以来这些医院收取药品和医疗器械厂商等支付的各类折扣、回扣等约3亿元。 最关键的推动力来自发改委酝酿中的一个政策改革。2005年下半年,发改委价格司表示,针对医疗器械行业价格和管理混乱的情况,已将医疗器械的价格管理问题纳入“重点研究”的范畴,并派遣价格协会组织专门的调研组来研讨改革路径。 发改委的思路是对医疗器械高值耗材进行限价管理,通过固定供应商出厂价到医院价之间的差价率,来挤掉流通环节中的灰色部分,从而达到降价目的。 其间,强生中国管理层与改革设计部门官员有过多次沟通,对相关部门锐意改变行业潜规则的决心留下深刻印象。种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强生在2005年11月以谨慎的姿态启动了销售模式的改革。 与波科不同,强生仍然保留了经销商,只是将市场和销售功能收归已有,经销商则转以物流配送和收款功能为主。强生的这一做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直销,但由于市场和销售掌握在自己手里,也就实际控制了灰色部分。经销商不再需要去促销、和医生打交道,只从事物流配送。 强生自己也一直在为转型做准备。几年来,不断地在招兵买马建立自己的销售队伍,人员已从最初的20多个扩充到现在的150多个。 此外,强生也聘用了一些新的拥有物流经验的代理商来取代、整合原先的小经销商。在南京,强生原来有三家小经销商做。筹备调整销售模式前,强生找了北京一家有多年医药行业物流配送经验的大型国营代理公司来整合南京经销商。 强生保留部分原有经销商另有一层考虑,即希望通过这些经销商继续维持和客户的关系;并由经销商负责解决医院拖欠应付款这个大问题。 “滑铁卢” 强生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相对温和的、循序渐进的调整来避免“自杀式”的业绩下滑。在规划上,也是先从两个城市试点,再逐步推开。 虽然在做出决定前,强生已对可能遭遇的困难有所准备,但试点地区销售下滑之猛仍然超出了预计,下一步的推广计划随即暂停。据透露,强生最初对损失的估计比较保守,以为不会超过三成,实际上却达到了70%。 对于强生遭遇的“滑铁卢”,经销商并不意外。上海的一位经销商曾坦率地对强生说,“你既要名又要利,做不到。” 其实,记者采访的数位强生经销商均承认,直销早晚是个趋势,经销商也早晚要面临转型。但在他们看来,强生作这个决定时机还不成熟。“这需要有国家政策及行业自律等条件来配合。”一经销商向《财经》记者说。 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强生前地区销售经理向《财经》记者解释,2006年强生支架销售出现如此大幅度下降,由多种因素造成。

首先是强生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强生自己的销售人员没有和医院直接打交道的经验。强生药物支架的有效性通常在三个月左右,缺乏备货数量经验、跟踪服务和管理经验造成了很多报废和损失。更重要的是,2006年同时有两家新的国产药物支架上市,对市场形成巨大冲击。即使不改变销售模式,竞争加剧,强生也会流失一部分市场。 但显然强生销售模式的转型加剧了困境。 强生本来认为,通过已有的两次招标降价,给医生和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已经逐步缩水。随着招标政策的继续,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小,医生对收入下降会有一个适应过程也会有心理准备。但从实际结果来看,这种看法对医生的接受程度过于乐观了。在南京,换了一个经销商后,原来四家大医院客户中有三家不再进强生支架。 事实证明,强生对于政府决策的效率和进程也过于乐观。如果发改委实行差价率控制,灰色收入的水分将被继续挤压,强生的销售模式调整就更易为市场接受。但强生期待的由发改委主导的限价改革并未如期启动。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