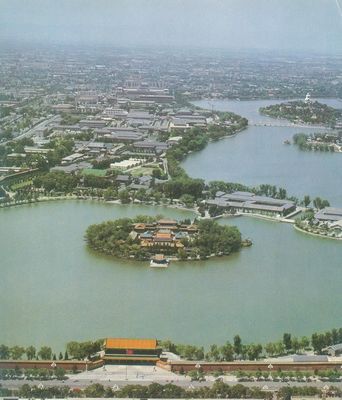二十多年前我还在杭州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去当时以生产“青春宝”“双宝素”出名的杭州中药二厂参观调研。记得厂长冯根生十分自豪地介绍自己工厂设备的现代化管理程度以及厂区的清洁美丽。他特别引以自豪的是,厂区里面绝对无人随地吐痰。那时随地吐痰的现象尚相当普遍,在马路上经常可以看见手臂上戴着红袖章的老太太,手提扫把和簸箕,随时准备抓获吐痰的人,被抓者一律罚款5角。我十分好奇,就问冯根生是以什么方式达到这个目的的。他不假思索地说,“方法很简单,那就是重奖重罚。工厂规定每吐一口痰罚款50元。”
那时我每个月的工资不过62元,50元绝对属于重罚了。因为自己的心理学训练,我忍不住问了一句:“既然大家都已经养成了不随地吐痰的习惯,那么现在能不能把这个制度撤掉呢?”冯根生立即说:“那可不行,如果现在把制度撤掉,吐痰的现象肯定会重演,而且还可能更厉害,因为吐一口痰值50元钱,不吐白不吐!”

他的话先让我大笑不已,继而引起了我对奖惩之真正目的的思索。很显然,冯先生惩罚吐痰行为是因为他觉得吐痰肮脏,破坏环境卫生,滋长病菌,是很不文明的行为。为了培养大家对吐痰行为的正确认知他采取了重罚的手段。换言之,惩罚本身不是目的,让员工意识到并且认同他对吐痰行为的态度,才是真正的目的所在。如果在使用惩罚的过程中忘记了背后真正想要灌输的理念,那么,就会发生员工将惩罚本身看成目的,一旦惩罚撤出,吐痰行为又会重现的结果。
使用金钱进行奖励有时也会产生类似的现象:即把金钱作为目的,而忘记了使用金钱奖励背后的原因。比如,有些员工很有思想,经常主动为公司的发展献计献策。为了鼓励更多的员工献计献策,公司决定对提合理化建议的员工支付加倍的报酬。补偿员工付出的额外努力当然应该,但由此产生的长远效果却很可能是出人意料的。
最经典的研究结果可能要算Titmuss在1970年发表的《礼物关系》(TheGiftRelationship)一书中反映的现象了。他在书中对比了英国和威尔士的无偿献血制度与美国的有偿献血制度,发现英式献血制度更能满足需要输血病人的需求,其血液的质量更好,数量也多。因为是无偿献血,所以主动去献血的人大都有相当的自豪感,为自己能通过自己的献血拯救别人的生命而经历崇高的情绪体验。而在美式的有偿献血制度下,许多去献血的人只是为了得到奖励(钱),而本来感觉到崇高神圣的人反而失去了献血的动机。
还有一个经典的案例来自美国的一个日托幼儿园。该幼儿园每天的开放时间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6点,长期以来都没有对在下午6点以后来接孩子的家长采取措施,因此总是有一些家长会迟到,延误幼儿园老师的下班时间。为了让更多的家长准时接回孩子,幼儿园制定了一个惩罚制度,那就是在6点之后,每迟到一分钟罚款1元。一个月下来,他们发现在6点以后来接孩子的家长人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比制度实施之前有了显著增加!
我和我的同事最近对奖惩后效的实验研究结果,与上述发现也有异曲同工之妙(Chen、Pillutla Yao,2009)。在这个实验中,我们主要研究团队成员在社会两难困境中的合作行为,并设计了三种实验情景来鼓励合作。
在一种情景下,我们对团队中合作量最多的成员用金钱进行奖励(奖励组)。在另一种情景下,我们对团队中合作量最少的成员给与惩罚(惩罚组)。在第三种情景下,我们想参与者宣灌合作的重要性(宣灌组),但不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奖惩措施。与此同时,我们也设计了一个控制组,不给奖励、惩罚也不宣灌。
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三个实验组中参与者的合作水平显著要高,证明了奖惩制度对提高合作行为的有效性。有意思的是,在实验的第二阶段,我们撤销了奖惩制度,观察参与者愿意贡献给团队的合作量。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我们发现此时曾用过奖惩制度激励的团队成员,合作量显著低于上一阶段,更具戏剧效应的是,该合作量居然低于控制组成员在第一阶段实验的合作量!也就是说,通过奖惩制度技法的合作行为相当命短,一旦撤出,还不如从来没有使用过奖惩制度的控制组!我们后来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意料之外的结果(unintendedconsequences)”。
更令人意外的是,“宣灌组”被试的合作量,不仅在第一阶段大大高于控制组,而且在“宣灌”撤出之后,其小组成员的合作量依然保持,显著高于控制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意料之外的结果”这种现象。当使用物质奖励或惩罚去巩固或消除一种行为时,就好比把胡萝卜和大棒挂在别人的眼前,容易诱导他人把自己的合作行为,与得到胡萝卜和避免大棒结合起来,而忽视了使用胡萝卜和大棒背后的实质。也就是说,使用物质奖励/惩罚会将行为的外在原因显性化,久而久之,个体就会将自己的行为动因归结为由于外在原因造成的。因此,一旦外因撤除,就不再有行为的动机。而只有从内心深处对理念的认同,才能将合作行为保持良久。从这个角度来说,以下的故事更是明证。
故事说的是一个资深心理学家如何将在他家附近踢球的孩子“撵走”的事儿。该心理学家的房子后面有一块很大的草坪,喜欢踢球的孩子们放了学就成群在草地上踢球,又笑又闹,噪音很大,妨碍了心理学家的静心思索。他想把他们赶走,但又知道硬赶肯定不奏效。于是,他想了一个计策。
第二天下午,孩子们照常来踢球了,在他们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心理学家来到了他们面前,让他们暂停一下。孩子们停了下来,心理学家笑着对他们大声说:“孩子们,你们喜欢踢球实在是太好了!为了奖励你们,老爷爷今天给每人发100元钱。”说着,他就拿出一叠100元钱的纸币,给每个孩子发了一张。大家都很开心。
下一天孩子们又来踢球的时候,心理学家又出去了,奖励孩子们踢球,给每人发了80元钱;再到后面一天,他给每个人发了60元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之后,有一天,心理学家来到孩子们的面前,十分抱歉地对他们说:“孩子们,爷爷的钱都用完了,所以今天和以后都不再能发钱给你们,请大家谅解。”孩子们自然是十分失望,于是不再来踢球。心理学家终于如愿以偿。
这是一个成功地将孩子们对踢球的内在兴趣转化成外在诱因的极端例子,进一步印证我在前面论述的道理。由此来看,奖惩不仅仅涉及制度的建立,更需要了解它所可能引起的心理效果才能把它用得恰到好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