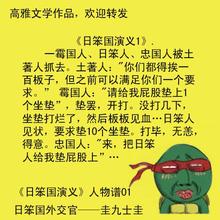记者:前30年中国企业处在大变局、大转型时期,那么新甲子时代,中国企业可能处于什么样的商业环境?
张亚勤:中国过去60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30年是自力更生、走向独立的30年。中国和世界几乎没有任何交往,更多的是“闭门造车”。第二个30年,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真正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这个过程中,全球化的背景使竞争的模式与规则都进入了更广阔的舞台。
记者:中国企业如何应变?

张亚勤:这样的趋势会促使中国向“中国智造”的新模式演进。中国企业需要适应这样的变化,无论在中国市场竞争还是到全球市场竞争都需要全球化的心态。
记者:中国企业未来究竟面临哪些问题?
张亚勤:未来的30年和过去的60年将非常不同。我们将面对很多的挑战,比如高消耗、低利润和低附加值。这需要一种长远的心态。
未来30年,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强国,因此全球对中国的期待将完全不同。这些期待包括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对环境的保护,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不仅要打造人才、技术、资金、市场这些硬实力,也需要打造创新能力、全球化视野、品牌和领导力,还包括这个企业在生态链中的辐射效应。
记者:未来新商业文明对中国的企业会有怎样的影响?
张亚勤:对每个企业来说,新的技术催生了新的商业文明。一方面是全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又是越来越区域化,就是市场越来越本地化,产品越来越多样化,服务越来越个性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每个市场和地域又有很强的特征。
其次,互联网不仅仅是技术工具,还会影响思维和运营的模式。创新的周期越来越短,从五千年的四大文明,到百年的科技创新,到PC和互联网都只有几个月的周期。很多商业模式是因为新的技术而存在的,比如电子商务、物联网。新的业务和商业模式正在被催生。
记者:是否会在中国催生出微软这样的企业?
张亚勤:从微观讲,在IT领域,中国不仅会产生中国的微软,还会诞生世界的微软,但不一定在操作系统层面。而在宏观领域,包括新能源、节能环保、汽车、生物等等,中国企业都有机会领导世界。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可以与跨国公司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中国的市场是最大的,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中国企业的相对实力增加了很多。未来中国的企业将有更多的机会。比如基于云计算和移动互联。因此中国企业要敢于在新的领域用新的方式超越。
记者:中国企业还有哪些缺陷或不足需要弥补?
张亚勤:大的国有企业没有压力和动力着眼长远。小的企业没有实力看长远。很多企业的成功来源于企业家的直觉和对市场机会的“赌注”,都有急功近利的问题,只看短时间内的盈利。未来的国际市场竞争需要更多的国际化视野和训练有素的企业家心态。
记者:改革开放30年,基本上是一个国退民进的过程,现在则是国进民退。未来企业所有制形式会发生什么变化?
张亚勤:虽然中国市场的需求足够大,但理想的格局是国家不应继续扶持国企造成垄断,国企应该尽可能减少。我认为国企越少越好。即便有,也应该有很强的监管措施。国家的经济主体应该是民营企业。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因为他们是国民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
记者:你为什么认为中国企业不需要太多的研究院而需要更多的工程院?
张亚勤:我认为,大部分企业需要的是面向市场需求、面向应用的技术,尤其是两到三年的技术储备,让企业都去做基础研究,是一种误导。
自主创新很重要,但不是什么都关着门埋头自己开发,这样会处于被动落后的状况,并不符合产业的发展环境。在某种阶段,购买技术是更快捷的方式,技术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中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得到。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现在这么多年企业的创新能力并没有提高很多,还是靠政府的扶持,并没有真正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记者:你对未来最担心的是什么?
张亚勤:随着市场越来越规范,国际的游戏规则将成为主流,就需要更多企业家素养和国际化的视野,更需要一种机制让企业有序经营。形成企业的品牌,而不仅有企业家的品牌,不能继续急功近利。
教育方面我也有点担忧。十年前我非常有信心,希望看到国内的科研水平与欧美差距越来越小,但现在感觉挺失望的。现在有种说法,“中国大学里大楼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教授越来越像明星,明星越来越像教授。”学校的很多硬件基础设施比欧美都好,但却没有引进著名的教授,做一些尖端的研究。在这方面,虽然不能说和国外的差距拉大了,但至少差距没有缩小。
记者: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有什么影响?
亚勤:我不能说这是普遍的现象,但如果教授们不能静下心来做研究,不能首先教好书、做研究,这种泡沫心态对未来30年教育科研系统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谁都想大而全,比如大学不仅自己做研究还想开公司做市场。企业不仅做市场还想自己做研究,都是定位错误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基础研究不够基础,而企业应用技术不够应用。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