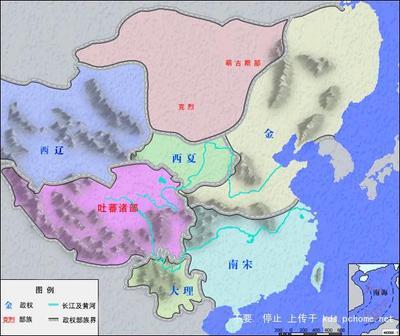1999年9月30日,星期四。北京。
即使单单从天气来看,这也是风云变幻的一天。初秋的北京原本清爽晴朗,这天下午却突然下起了大雨。雨越下越大,一夜没停。只有彻夜未眠的人才知道,在凌晨3点的时候,雨势开始慢慢转小,变成了钟摆一样的滴答声。好不容易熬到5点,起床的人看看窗外,松了一口气。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将是阳光灿烂的一天。
住在北京西直门南大街6号国务院第二招待所里的这25个年轻人,他们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公民一样,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开始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庆典。唯一和别人不一样的是,在之后的十年,1999年10月1日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将改变他们一生的轨迹——也许还将改变这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和商业进程。换句话说,他们将结束某一段历史,并且亲手开启另外一段历史。
就这一点来说,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心知肚明,并且暗下决心,像是怀揣着一个即将大白于天下的秘密那样兴奋。另外一些人则还在权衡和犹豫中,他们面容严肃又犹疑,拿不准在这个命运的交叉口是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不过,所有人都明白,无论他们做出怎样的决定,时光都不可能永远停驻在这一刻——没错,在中国留学史127年后,他们需要传承某种传统,完成属于自己这一代的使命。
现在,到了可以公布这份25人名单的时候了。按照原始排序,他们分别是:黄劲、邓晖、刘怀竹、郭延鹏、彭泽忠、杨子江、李彦宏、邓中翰、田源、朱东屏、吴敏春、赵亦林、刘平堂、曾国庆、张健存、吴越、马延辉、周向军、扈传平、董大为、韦锡波、江晓平、施嘉诺、阎超、李向兵。
你一定可以从中发现一些熟悉的名字。其中有些名字已经成为传奇,还有一些名字有待成为传奇。你还会惊讶地发现,十年过去了,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最年轻的、生于1968年的年轻人,一个叫做李彦宏,一个叫做邓中翰。
1999年10月14日,国庆观典之后不到两个礼拜,邓中翰在北京海淀区北土城路103号的一家仓库里创办了中星微电子公司。2005年11月15日,中星微在纳斯达克上市。
1999年12月24日,20世纪最后一个圣诞节的前一天,李彦宏登上回国的飞机,在北京创办百度中文网站。2005年8月,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当天股价从发行价27美元飙升至150多美元,创造了有史以来外国公司在美上市的最大融资记录。
实际上,这个“1999年硅谷留美博士企业家合作团”,源于教育部1996年设立的资助优秀海外留学人员短期回国服务的“春晖计划”年度活动。与往年不一样的是,这一年的“春晖计划”和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馆合作,邀请25名硅谷留学人员归国,除了在各大城市考察、大学演讲和领导人接见之外,他们还将在国庆节这一天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观看1949年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阅兵式。
即使今天看来,这也是一份极其精英的名单。这25人全部拥有美国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都有美国工业界5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并且在这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他们都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技术项目和创业意向。他们绝非泛泛之辈,全部在硅谷从事互联网、电子科技和生物医药等高科技行业,头衔则是各家公司的总裁、副总裁、高级工程师、高级研究员和全球产品经理等。他们中年纪最大的51岁,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年纪最小的刚满30岁,正是急于改变自己命运的年纪。
这简直是一次精英大批发。以1999年10月1日为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天之后的半年以内,几乎所有25人都回国创业。这25人并非一个团队,也并未造就一个时代的集体性的商业奇迹,但是他们开启了一个潮流。
“他们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五代归国留学生。”欧美同学会会长王辉耀说,“他们和以往四代留学生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是第一代试图以商业和企业的方式报效祖国、实现自我的留学生。”
1999,改变一生的一年
1999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将被载入史册:克林顿性丑闻案件审判、日美汽车企业合并、叶利钦辞职、中国完成加入WTO谈判……不过,对于邓中翰而言,这一年只发生过一件事情。他只被一件事情折磨——回国,还是不回?实际上,答案在很早以前就是清晰的,他也明白地听到过某种召唤,但是真正到了抉择的时刻,他举棋不定。
邓中翰有做选择的条件。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和物理学硕士学位,有在Sun和IBM的工作经验。毕业不到两年,他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创业家。他从英特尔创始人之一David Daw那里获得一笔风险投资基金,在硅谷创建了集成电路公司PIXIM,担任首任董事长。他的公司市值很快达到了1.5亿美元。
关键在于,邓中翰才刚刚满30岁。一个如此优秀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什么抱负倒真是咄咄怪事。而保持优秀已经成了邓中翰的一种习惯。从中学时代开始,他就是大队长和学校的升旗手,一个孩子王和三好生的混合体。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访美、朦胧诗、摇滚乐、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些时代事件全都在他脑海里留下印象,但是全都不深刻。对他影响最深的是陈景润和华罗庚的故事,还有叶剑英的那句诗“攻城不怕坚”。他在中国科技大学的4年时光几乎都是在实验室里以疯狂节奏度过的。后来,他承认说,他是个“有科学家情结”的人,并且相信“技术救国”。
但如果你就此认为他是个“科学怪人”,那你就错了。从1992年开始,他在伯克利度过了5年时光,见识过大学裸体运动和篮球狂热,价值观已经增加了自由和活跃的因子。1995年,他以博士身份在Sun工作,参与研发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中央处理器,并且亲身经历了一个伟大的产业革命时代。这一年,硅谷的所有话题都围绕着CPU、互联网和摩尔定律,网景、雅虎和思科等新技术公司先后上市,英特尔总裁安迪。格罗夫成为《时代》杂志的1995年度人物。
这不但是时代的转折,也是邓中翰个人的转折。“30年代的美国梦指的是创造财富,但硅谷人的美国梦是指能够用一个技术来改变这个产业,改变这个工业,甚至于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当然,随之而来的是上市,获得大量的财富,进一步扩张、收购等等。我已经实现了改变生活的美国梦,但是我需要通过个人的奋斗改变周边,改变这个社会,改变一个世界。”
在硅谷,邓中翰认识了一个叫做李彦宏的朋友。在邓的印象里,这是一个“闷骚的年轻人”。当邓中翰在琢磨创业的时候,李彦宏埋头写了一本叫做《硅谷商战》的书。2009年8月,李彦宏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引用了一本讲述母校北大历史的书《精神的魅力》里的话:“这真是一块圣地,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数代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的操守和抗争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的魅力值。科学与民主,已成为这圣地不朽的魂灵。”他还说:“这些话指导我做人生的选择,做我自己的思考,去选择最适合我做的事情,去选择真正能够对社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改变、产生影响的一条人生道路。以技术之忧,复兴中国文化,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共识和使命。”
1999年,以他们二人的资历,显然还承担不起这样的使命。不过,工程师的天赋加上硅谷美国梦,这的确是一代留学生的精神基因。他们有相似的成长路径,作为八十年代的知识精英赴美留学,是新一代的科学人。他们渴望成功,但是不再渴望成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相信,以自己的智慧、技术和力量自可以创造一个完善的世界,而企业只不过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他们希望创办自己的纳斯达克上市企业,让市场成为检验成功的标准,并且通过技术和商业的成功来改变世界。一旦成功,他们即是完成了从一个科学家到企业家的转型。
可能是怀着一种高于个人事业心的使命感,或者说家国情怀,如果有机会,他们希望能够在祖国实现自己的梦想。机会很快就来了。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硅谷留学生就经常有机会回国参加各种活动。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1998年,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访美期间会见在硅谷创业的邓中翰,希望他能够回国,以硅谷模式发展中国半导体工业。邓中翰承认,自己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和国内接触。“谈未来的园区,盖多少房子,这些我倒没多想。不过有个领导谈到,我们国家如果没有两弹一星,那么我们不可能赢得多年和平的发展环境,给改革开放带来契机。未来芯片、核心技术这些也要在中国发展起来——这些东西跟我还比较容易挂钩。”
有一次,邓中翰回国进行学术考察,和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领导吃饭。后者管他叫“新华侨”,邓中翰说:“我不该叫华侨,我又没入美国籍,我随时准备回来。”在美国的7年中,邓中翰始终没有加入美国籍。不仅如此,他还一直动员自己身边的朋友不要入籍。这似乎是个潜藏在内心的信号——一个中国人,回到自己的国家是早晚的事情。
1999年10月1日,这一天成了一切抉择的切入点。
这几乎是一代人最大的庆典。25人团的团长、现任安博教育集团总裁黄劲回忆了当时的行程——“在这一天观礼之前的两周,我们作了一次全国考察,全部是省级领导接待,包括辽宁、天津、江苏、上海和北京。接着,又在几所大学作了有关信息技术的报告演讲。最后,10月1日这一天,所有人都上了观礼台。如果你面对天安门,我们就在天安门左手边的第三个格子。我们四点多就起床了,真正入场已经八九点。这一天,从白天观礼到晚上烟火表演,我们一直在这里。我们哭啊,喊啊,激动极了。最后从台上下来,就没有一个不准备回来的,全都要回来创业。”
黄劲至今保留着一张日期为1999年9月30日的24人合影。当时,他们还准备了一条类似于“小平你好”的横幅,上面写着“硅谷学子回家了”几个大字,准备在国庆观礼当天拿出来。这个打算被取消了,他们只是在教育部门口举着横幅合了影留念(李彦宏因故缺席)。现在从照片上看,这都是一些衣着打扮不怎么起眼、但是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他们也许并不全是朋友,但都是伙伴。这天晚上,合影之后,他们一起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一次国宴。回到招待所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们仍然在一起聊天,畅想未来。
“那天晚上,我们聊着聊着,都觉得机会来了,真的是一腔热血,想要回来做点事情。我还说,现在回来是最好的时机,如果十年以后回来就晚了。现在看来,真的是这样——如果李彦宏十年之后回来,他再厉害也做不成百度。”团员之一、现任中康德众医院管理公司创办人马延辉回忆说。
这天晚上,马延辉在日记本里写下这么一段话:“这样激动人心的一天,如果不尽快回去,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邓中翰清晰地记得,10月1日这一天,他站在观礼团的最前排,发现北京的天特别特别蓝,阳光特别特别好。陆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武警特警、预备役部队一次又一次从他面前走过的时候,他正在和他自己作斗争——“回来吧,时机很好,很多企业不盈利都能上市呢。”“国内的做事方法太复杂了,到处讲关系,听起来很复杂。失败了怎么办?企业我不能控制怎么办?政府的钱随时调走了怎么办?”“你31岁了,已经不是个孩子了,你要为自己未来的路作一个决策。”
当天下午,仿佛是为了最后下个决心似的,邓中翰带着自己的创业团队去了长城。当时的照片现在还在,邓中翰指着照片说:“白云蓝天,太梦幻了。我觉得有这样的蓝天,一定就有更美好的未来。”当天下午,邓中翰在长城把话挑明了——“要干这个事情。今天不是回来做第一笔国家风险投资,也不仅是做中国第一个芯片,而是为国家的未来出自己的一份力。”
2009年,未完成的梦想
2009年夏天,邓中翰已经是成功的企业家。他回忆起来,在自己尚未如此成功的时候,已经使用了一些商业技巧,为自己回国以后的事业做准备。
当时,邓中翰最大的顾虑就在于是否能够得到公司的控制权和政府领导的信任。曾经有位政府领导打电话找邓中翰没找着,就说,“怎么能把国家的钱给这么不可靠都找不着的人”。还有一位领导推心置腹地对他说:“生意做不好赔光了都没事,但是在钱的问题上千万不要犯错误。”
面对阻力,他试图通过一次谈判和一篇报告解决问题。1999年4月,他在递送李岚清的一份报告中附了一篇题为《中国21世纪的高科技产业——从硅谷的成功看我国的高科技产业》的文章。现在看来,这对于邓中翰来说是一篇青春无悔的文献——文章中屡屡出现“世纪交替,风云际会”、“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崛起与繁荣富强”、“有中国特色的高科技产业”等等措辞。这简直不像是个留美学生的手笔。不过邓中翰感慨又得意,他在采访中6次提到这篇文章,说:“当时很好玩,眼光也很深,就怕领导不让我用硅谷公司的模式来做芯片,写这文章就是为了试探,向领导证实我的方向。”
文章发表不久,邓中翰和政府官员完成了至关重要的一次谈判。在这次谈判中,他被确认担任未来公司的董事长。
对于另外回国创业的24人,获得政府的支持都是至关重要的步骤。黄劲在1999年回国之前刚刚在美国结婚买房,并且在硅谷注册了自己的半导体公司。1999年10月2日,观礼的第二天,她参加当时教育部副部长韦钰举行的欢迎晚宴。韦钰问,你们这些人谁是有意做教育的。黄劲说,“就是这个问题促使我后来不仅转换了地域,并且转换了行业。”她在硅谷创办的安博集团回国转做教育相关软件开发,并且获得了教育部的一笔基金支持。
回国初期,邓中翰、李彦宏、黄劲、马延辉,这四个人组成了一个类似骷髅会的秘密组织。他们都是单身在北京创业,都是同龄人,都有相似的成长经历,也都有理想主义的创业激情,也都面临相似的水土不服的问题。他们定期在硅谷或者北京的咖啡店里聚会,有时候互相诉苦,有时候彼此介绍商业伙伴,有时候,甚至在对方捉襟见肘的时候借一些钱救急。
这四个人里,黄劲的性格和男人一样开朗坚强,她爱穿男式的衬衫和休闲裤,什么都不怕的样子(马延辉唯一一次见到她哭还是她结婚的时候)。李彦宏和马延辉一样性格内向,不多言语,但是韧性强。马延辉还记得,当初李彦宏在北京友谊宾馆租办公室的时候,几次资金困难,差点挺不住收拾包袱回美国,不过最后都扛住了。邓中翰被认为是四个人中最擅长交际,性格最有感染力的一个。他现在回忆创业的难处,无论是仓库办公还是资金短缺时拿个人资产抵押,全都轻描淡写或者付诸笑谈。
不过,世俗的成功与否标准对他们也有约束力。
“其实,我们这些人里,真正成功的也就是邓中翰和李彦宏两个人。他们的光环掩盖了很多东西,对于其他的人也是很大的压力。”马延辉说,“最终,这25人,有三分之一创业成了,三分之一回美国了,还有三分之一去了别的公司做高管。”
十年来,尽管这些留学生有技术,也有自己的海外融资渠道,并且因为留学生的身份而获得了很多官方便利,但是最终仍有一些人创业夭折。
“困难太多了。一个是政策,政府当初的承诺很多都没法兑现,我们一回来,发现没人理了。一个是钱,国内融资太难了,我们自己去美国融了钱回来,外汇管理局还管着不让随便花。还有理念的问题——李彦宏一成功,他就好像成了一个没有丝毫缺点的完美偶像,但我认识的李彦宏不是这样的。中国商业就是成王败寇,硅谷就不是这样,它永远接受失败,永远可以从头再来。”
马延辉毕业于加州大学医学院,回国创业之前做过大学教授,也做过医药公司研究人员。十年来,他最不想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你公司做得多大了?钱烧得有结果了吗?上市了吗?”他最大的烦恼是去什么地方谈生意都得穿有牌子的衣服坐有名气的车。他的妻儿现在仍然留在美国,马延辉被迫到处飞行,做商业或者家庭旅行。他气馁的时候也想,要不是当初一心回来,留在美国做个研究员,一年几十万美元也不错,压力还没这么大。
1989年,马延辉去台湾访问,在台北故宫门前留下一张照片——这是一位典型的八十年代时髦青年:喇叭牛仔裤、尖头皮鞋、蛙式变色墨镜和迈克尔。杰克逊式的爆炸发型。20年很快过去了。马延辉知道,自己比起20年前苍老了不少。前不久,他的儿子从加拿大来北京看他,他在奔驰车里又放起了摇滚乐。情怀还在,意志多少有些消磨。

马延辉看着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觉得伤感。20年前,他在台湾和王永庆、施振荣一起吃饭,了解到正是第一代留学美国的台湾留学生回台创业,这才改变了台湾的整体政经面貌。20年后,他感到很惋惜:“我们这么多人,花了十年的青春,走到现在,除了李彦宏和邓中翰,却并没有走出一条归国留学生的创业模式来,以供后人模仿——以后的年轻人要走的路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出现而变得更容易一点。”
百度上市的时候,马延辉和黄劲都发了祝贺短信。但是自那以后,李彦宏出席聚会的时候越来越少了,偶尔出现,还得戴上墨镜。马延辉很希望李彦宏能够写本自传,不是写他的成功之处,而是写他的失败之处。(李彦宏自己说,“创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经历各种各样的艰辛,经过痛苦和失败的挫折,这一点在百度的成长过程当中也是非常明显的。”)“李彦宏这个人不可复制,不是说你照他做就能再来一个百度,但是他的作为可以复制。他应该把自己的经验写下来。”十年前,马延辉在随25人团去大学演讲的时候,所选择的主题是“胰岛素在治疗糖尿病中的应用”——他说,如果换做现在,他一定不会跟年轻人讲学术话题,一定会像当年惠普或甲骨文的老板那样做一番励志报告。
这四个人,他们都是在九十年代的加州硅谷认识的。1993年,崔健去加州开演唱会,他们全都去凑热闹,只不过当时还互相并不认识。当年崔健唱:“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如今马延辉觉得,自己被世界改变,多过自己改变世界,并且丝毫不是以自己当初所期望的方式。
前一段时间,马延辉在美国回北京的长途飞机头等舱里碰到了邓中翰,两个人沿途聊了13个小时,意犹未尽。最后,两个人的对话是这样结束的——
“你做公司已经成功了,你需要另外一些手段去推动你的目标,改变这个社会。”
“在公司之外,我是在思考国家的事情和产业的事情,想去推动。”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