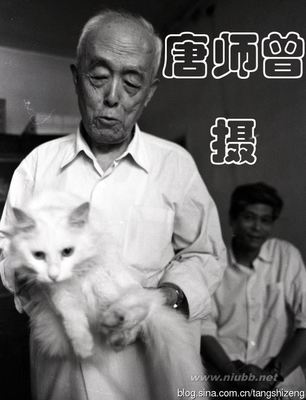导语:作为时代最醒目的学术符号,季羡林在学术上却是何等孤独。他的各类风波争议比专业贡献更易引发关注。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既无法摆脱早已公开拒绝的“国学大师”帽子,也无力阻止自己陷入各种利益争夺的漩涡。
对包办婚姻不满,但没有勇气摆脱,季羡林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与妻子分居。他与儿子也隔阂重重,十多年断绝联系,直到去世前一年才重新相见。
“研究”季羡林 的人不去图书馆,都去医院了。在被各类出版社和“学术机构”反复争夺的同时,他最重要的三部著作《弥勒会见记》、《中亚佛教史》和《糖史》都缺乏真正的研究者。
作为时代最醒目的学术符号,季羡林在学术上却是何等孤独。他的各类风波争议比专业贡献更易引发关注。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既无法摆脱早已公开拒绝的“国学大师”帽子,也无力阻止自己陷入各种利益争夺的漩涡。
7月19号,北京八宝山,季羡林追悼会刚刚结束。
休息室内,一人端起了季羡林生前养的两只乌龟,立即有人大喊:“有人偷乌龟啊”!原本肃穆的现场一片混乱,记者们迅速围了上来。这一幕随即被冠以“乌龟门”演绎于媒体,并与季羡林生前一度沸沸扬扬的“字画门”加以联系。
争吵从季羡林的生前延续到了身后。“乌龟门”迅速演变为媒体上的恶语相向。其中一位是季羡林的老秘书李玉洁,她说季羡林之子季承害死了他的父亲。如今也躺在病床上的李玉洁看上去相当虚弱:“十多年都不照顾父亲。我不想多说。”
此后一天,季承在本报记者面前抛出了一连串严厉的指控,“李玉洁血口喷人,诬蔑中伤”。按照他的说法,李玉洁不仅藏匿了季羡林生前的存款,还盗窃了一批字画,“阻挡我们父子相见,累死累病都不值得同情”。
在季羡林去世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秘书虐待”,“父子决裂”,“财产之争”相继闯入公众视野,真相和谎言难辨。重重争议当中,季羡林走过了最后的时光,在日渐苍老的年月里,对于他的形象塑造和遮蔽并存。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伴随着反复的被争夺和被围观,季羡林却愈发孤独。
“我一个孤家寡人”
最后6年,季羡林绝大多数时间在301医院度过。6年里,季羡林只回过北大住处朗润园三次。“他想家里的大白猫,想家里存放的书画,想楼前河里的荷花。”季羡林在北大的邻居乐黛云教授回忆。
第一次回家时,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白猫扑到身上,季羡林的眼泪就“扑哧扑哧”地往下掉。
朗润园的房子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很久了,那时候房子里住了季羡林的婶娘和妻子。每到周末的时候,女儿婉如、儿子季承都会带着孩子来看他。季羡林则经常坐在楼门前的长椅上看他亲手种下的荷花。
季羡林最后一次回家是去年7月4日。他看了看自己的书架,翻翻别人送给自己的字画,和老邻居寒暄了一会儿,在301医院派来的3个护士的陪同下,他还摇着轮椅去了趟未名湖。
邻居乐黛云记得,那天,在勺园吃饭时,因为孙女季清携带着两个重孙女从美国回来,季羡林少有的高兴。
因为长期的别离,季羡林和孙辈的关系反而要好过儿子和女儿。让老人惋惜的是,先是孙子季泓去了美国留学,接着孙女季清又去了澳大利亚;最后外孙何巍又去了加拿大。加上后来和儿子的决裂,家里早已空无一人。“总之,在我家庭里,老祖走了,德华走了,我的女儿婉如也走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在写这篇《求仁得仁,又何怨!》文章的1995年,季羡林与自己的儿子季承公开决裂。
季羡林的传记作者、《人民日报》前记者卞毓方新近出版的《晚年季羡林》第一次披露了1995年季羡林父子的决裂。从去年开始,跟两人相熟的卞毓方一度试图调和这对父子的关系。让卞毓方奇怪的是,他在向北大季老的弟子那里打听季承下落时,没有人愿意告诉他联系方式。一直到2006年,在季羡林的外孙女那里,才打听到季承的北京电话。
卞毓方的调解工作并不容易。“我跟季老的弟子们吵架说,如果季老不和儿子和好,走的时候一个亲人也没有,你们能够给他披麻戴孝吗?父子之间有什么了不起的矛盾?”按照卞毓方的看法,围绕在季羡林身边的人,并不愿意季承回到季羡林身边。
拿他赚钱,或者赚名
对于父子决裂,多年以来北大流传的说法是,儿子季承拒绝出钱安葬母亲,且与季羡林的保姆结婚,季羡林无法忍受。“我是最大的孝子”,愤慨的季承不接受上面的说法。按照他的解释,决裂源于当初父子间爆发出来的意气之争。“季羡林对婚姻不满,从而迁怒于子女,他觉得孩子们只孝敬母亲,不孝敬他。”让季承也让记者们苦恼的是,在这一点上他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
种种不同的说法充斥在季羡林的最后岁月,而父子矛盾在“字画门”事件中集中爆发,至今仍无定论。新近的困惑是,数百字画和珍贵手稿等遗产,捐给了北大还是留给了家人?尚未发布权威官方结论之前争论会一直持续,类似字画门的逻辑再次上演:互相指责但并不公布证据,媒体无从证实也无从证伪。“字画门”之外,围绕季羡林的争夺同样激烈。林林总总的出版物展开热销。7月25日,在北京王府井书店,关于季羡林的传记类和励志类人生哲理类书籍占据着最为醒目的位置。

据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出版的“季羡林作品”就有31种之多,价格多在30元以上。他大概是去年文化界中出书最多、收入最多的学者之一。2006年到2008年年底之间,季羡林的稿酬和题字润笔费超过200万。
这样的争夺在季羡林有生之年就已展开。《病榻杂记》出版前,数十家出版社加入了竞争行列。季羡林与图书编辑的合照频繁出现在各种“季羡林作品”或者相关报道中,不谈经济回报,能够接近季羡林并出版新著,对出版社而言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荣耀:那意味出版社获得了大师的垂青。借季老一束光照耀自己的情形,远不止存在于文化界。
虽然在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宣称绝不封笔,但衰老已不再允许95岁的季羡林写更多的东西了。正是在2006年前后,季羡林即将出版全集的消息就已在出版界传开。文化界众所周知的规矩是,在世者一般不出版全集,一旦出版则意味着弃笔。“对于出版者而言,无非就是赚名或赚名,而出全集一般都赔钱的。”一位深谙季羡林出版物的人士回顾,不止一家出版家出手争夺,其中包括1992到1998年间耗时6年将24卷《季羡林文集》出全的江西出版社。最终它如愿摘得了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一等奖桂冠。
江西出版社对全集出版权颇为重视,甚至专程派人赴京争取。就技术而言,这家出版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只要在文集基础上增加6卷即1998年之后的文字全集即可功成。然而这份诚意并未取得当时身在医院的季羡林本人的垂青。在全集版权争夺中败北后,江西出版社一怒之下再版了他的文集,“让全集不好卖”。
“市面上大多传记和杂书我基本不看”,季羡林北大东语系同事、季羡林文集的副主编张光璘看来,它们中的大部分来自现存的散文和媒体采访的排列组合,然后冠以“季羡林说和谐人生”等书名问世,并无研究和出版价值。
若以更为严肃的学术眼光审视,其中最受学者诟病的包括季羡林研究所出版的五本一套、限量发售且定价不菲的丛书。事实上季羡林研究所的主要成果就是出版类似书籍,对于他的真正学问,连同这个山东省拨款逾千万的研究所本身,都被批评者视为盲从崇拜、不良动机,行政意志和低等研究的混合物。
被戏称为季羡林热的“季风”拷问着什么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严谨的学者们根本不屑逡巡于季羡林的“故事”,他们的看法跟北大季羡林工作室图书管理员的看法一致:针对季羡林,尤其是他最重要的三部著作《糖史》、《弥勒会见记》和《中亚佛教史》都缺乏真正的研究者,“研究季羡林的人不去图书馆,都去医院了”。
这或许可以说明北京大学为什么没有开过季羡林的学术研讨会,没有成立季羡林研究所,说明被新闻界和出版界视为国宝的学者季羡林在学术上是何等孤独。晚年季羡林只能通过散文和新闻跟社会取得沟通,也因此被误解,被伤害。
和谐社会需要这个符号
即便是作为时代最醒目的学术符号,他的各类风波争议却比学术贡献更易引发关注。
像很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季羡林的身上的时代烙印挥之不去。建国后的种种风潮和运动耗去了他们的中年,年逾七旬的季羡林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自己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糖史》等重要学术著作均完成于他的晚年,70岁到90岁之间。
然而单凭这些冷僻的著作很难解释为什么连一个打工者都知道季羡林,无法解释他何以能够获得举国皆知的地位。除了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生前他还是五十多个国家级学术团体的负责人。在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界,很难找到出其右者。
就学术而言,解放前从德国回国的季羡林因资料短缺无法进行他的专业研究,开始转向印度文化,而晚年一些新近出土的珍贵资料和偶然的兴趣,推动季羡林在多个领域内有所著述。
与冯友兰、朱光潜等端坐书斋的学者不同,他热心社会事务并参与其中,即便是潜心学术的1980-1990年代,发表在多种报刊杂志上的散文扩大了他的声誉,而在改革开放后言论逐渐开放,以公共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也从另一个角度扩大了他的知名度。
按照传记作者的描述,80年代末的《留德十年》在学生们间名气已经很大。在戴墨镜穿喇叭裤西方思潮持续涌入的年代,他抛出的“21世纪东方文化独领风骚论”既不精美也缺乏论证,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文化界引起轰动。李慎之等一批知识分子在国内掀起了一片反对之声。
回望思想史上的80年代,季羡林撰文为胡适平反需要冒着背负自由化罪名的风险。在季羡林的学生张光璘看来,不论观点本身,当时禁区密布的公共领域内,敢为风气之先使得季羡林成为一个“开门者”的角色。
张光璘用“学术开放问题上的先锋”来形容80年代的季羡林。“在那个年代,其实不是政治问题的文化问题,也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
假设八十岁之前去世,季羡林只会是一个普通的教授,无法获得日后其自称为运交华盖的隆隆名望。
1998年是重要的一年,当年出版的《牛棚杂忆》作为国内反思“文革”的几乎唯一的出版物,为他带来了更大的声誉。
但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北大百周年的纪念和阐释浪潮中,北大存在于在自由主义和太学传统的多种阐释路径中,季羡林旗帜鲜明地打出爱国旗号。在《我看北大》一文中,他说“我个人始终认为,北大的优良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校庆那天,四代北大人推锤敲响百周年纪念的钟声,身为老年北大精英的代表,他身穿中山装面带微笑,站在最前方。
这样的照片,跟他在和谐社会的倡导下屡次谈论和谐一样,很容易登上媒体版面。“时势造英雄”,卞毓方如是解释作为一个社会现象的季羡林,“他的出现符合社会需要和人们的心理需要,社会需要改革开放和政通人和,需要这个符号”。
儿子季承丝毫不否认存在另一个季羡林,那是外界造神运动的产物,“他被捧得太高了”,季羡林去世后第15天,他的儿子季承语气高扬,两手像卷起一团纸一样甩向空中。
甩不掉的大师帽子
虽然自嘲为“杂家”,但一旦进入媒体,他被冠以各种学家的美誉,扭曲难免发生。媒体塑造了他全知全能的形象。而当有关他的一系列争议爆发,一些后来的媒体显然缺乏更为精确的判断,“反面的说得更加激烈,正面的拔高得厉害”,季羡林的一个学生评价说。
更为吊诡的是,季羡林至死都没有摘掉他公开拒绝过的“国学大师”帽子。
有资料显示,国学被推向中国前台可以向前追溯到1991年。当年的国家教委的学术座谈会上,与会者中传出“反传统的观念将会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的声音。
国学需要兴起。1993年的《人民日报》报道北大的国学探讨,季羡林位列其中。此后的多位国学大师在出版界和新闻界应运而生,各个大学开设国学班。大师一词迅速流传在1990年代蹿红,此后致力于推动国学复兴的季羡林,是被戴上国学大师帽子中的一个。
次年《人民日报》发表季羡林的文章,其中国学的任务被定义为“激发爱国热情”。内涵和外延至今仍不清晰的情况下,国学热强势兴起,大师热尾随而至。
大师的名号让季羡林更多的陷入争议。2008年年初,复旦大学教授、自称“关门弟子”的钱文忠进入季羡林的病房突然跪拜,摄像机尾随而至,在央视播出后引起轩然大波,另一个学生社科院葛维钧随后撰文批评。
这篇叫做《钱文忠讲座中的梵文错误并及其他》的长文,几乎是季羡林“一心向学的弟子们”一致的呼声。文中学术与媒体、学术与名望被严格划分,因百家讲坛走红的钱文忠被排除在学术之外。犀利言辞指向钱文忠“季羡林关门弟子”一说,“倘若掷诸报端,流入传媒,就难免自炫邀捧之讥”。
事实上另一个跪拜季羡林的刘波才是季羡林的关门弟子。十多年前在北京友谊宾馆大厅名流荟萃,共同见证了刘波跪拜季羡林的入门仪式。刘此前承诺向季羡林海外基金会捐赠200万美金,用利息支持学术。即便几年之后刘波的博士论文更像是一篇抒情散文,在北大通过困难,但照常毕业了。
记者出身的刘波策划的《传世藏书》包括了四库全书以及其他古籍中的重要经典,季羡林任总编给《传世藏书》权威之感。这套售价6.8万的丛书,令全国顶尖的26所高校和研究者共2700多专家加入其中,历时6年才全部完成,成为90年代中期的文化佳话。
但几年之后,刘波东窗事发,欠下巨债外逃,人们很快发现他编纂《传世藏书》意在进入资本市场而不是弘扬文化。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他至少通过丛书套现2亿。“季羡林先生被别人利用,每次引起争议的都不是他本人而是靠近他的得利者”。
而在北大一些学者看来,包括字画门在内的诸多争议,“季羡林也有责任”。为尊者讳,这样的说法从未出现在正式的报道中。
在生命最后岁月,季羡林做出了一个让颂扬者下不来台的举动,他在2006年发出呼告:“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一并摘去的帽子还有“学界泰斗”和“国宝”。然而就在这年,95岁高龄的季羡林成为央视感动中国人物,温家宝总理再次到医院探望为其祝寿,因此引发了更加猛烈的颂扬之声。
外界似乎更加相信他是大师中的大师,奖项仍旧纷至沓来,两年后,印度莲花奖、日本学士院客座院士和德国哥廷根大学杰出校友的奖杯,又递到了97岁老人的手上。直到去世前1个月,记者们仍然在采访他,“ 6月10日下午,央视主持人王小丫曾来到301医院,“代表《开心学国学》节目拜访了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
熟悉他的人看过这段视频,“季老消瘦了很多,恐怕时日不多了”。
在一些文字中,季羡林说自己无意刻意追求名望,而另一些时候他则说自己也有功利之心,但这似乎都不足以涵盖他置于荣耀中央的所有感受。然而,持续的颂扬和争议有时让他不厌其烦。摘掉三顶帽子的那年,他已经95岁了,他再次陷入舆论漩涡,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龄。
谁的季羡林?
作为一个与死亡渐近的老人,季羡林说:面对死亡,他既不高兴,也不厌恶。
他属于北京五棵松桥西南角的301医院(中国解放军总医院)北楼4层的一个副部级待遇的高级病房。他感谢过医院里所有的人,他们从死亡线上几次把他拉回来,“301是中国的符号,301是中国的光荣”,“既治好了我的病,也治好了我的心”,季羡林曾写到。
他属于晚年照顾他的秘书们。2008年前的十多年中,老秘书李玉洁、继任秘书杨锐操办了季羡林的所有事务,也因为字画门和乌龟门种种争议受到了伤害。无论如何,她们是季羡林和世界沟通的纽带。
去世前的10个月,他属于他的儿子季承和这段备受争议的天伦之乐。他属于这个13年前不幸破碎而后重聚的家庭。季承说,决裂的13年里双方都在反思。
他属于一直围绕他的重重利益之争。从字画门到乌龟门,镶嵌在眼花缭乱的传言中每一个对立面,每一个人,都称自己在保护季羡林,都称有人在伤害季羡林。季羡林因种种不同的价值被这些人各自反复使用。
他属于北大。即便是在字画门减损了季羡林的美誉度,但被质疑的北大仍在两难中维护他的声名。去年12月在北大召开的“言论自由与公共理性——季羡林字画门研讨会”上教授们拒绝向媒体投降。一位与会者说,“新闻的发布者可以用部分的真实说一件虚假的事情,形成一个虚假的非正义的气氛,以社会正义的面孔呈现出来。”
他属于终其一生无法摆脱的孤独。年幼寄人篱下,青年包办婚姻,与爱人无共同语言,一生渴望被爱而不得。爱人和女儿死了他从不参加葬礼,而是躲在图书馆以写作宣泄情感。
他属于三十年来急剧变化的时代。某种程度上时代塑造了它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也从个体反衬时代。
而今,“国学大师”季羡林,“学术符号”季羡林,“字画门”中的季羡林,孤独的老人季羡林,已经逝去,只属于八宝山公墓里一个有待分配龛位的骨灰盒。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