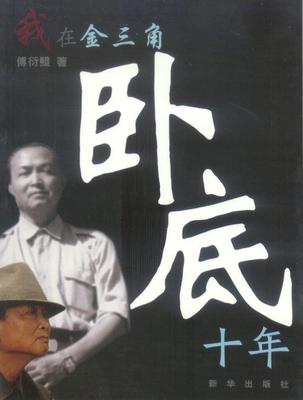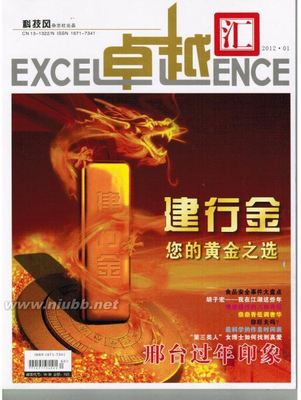他,祖父卢作孚的盛名是伴随终生的烙印,尽管他从未真正意义上见过祖父,惟一的接触是五六个月大时祖父的一个吻;他,2007年加盟海尔地产只因张瑞敏的召唤,尽管他本已打算退出江湖,到西部自己曾经当知青的地方做公益事业。卢铿,毁与誉对他来说已不再是困扰,而如何在无法独善其身的地产圈,将积淀多年的独立思想转化为更大的生产力,或许值得期待
“你可能想象不到,我从一内心是支持90/70政策的,只是一开始我就意识到它无法一刀切地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这并不是卢铿说出的惟一惊人之语。他还说:“在今年一月份,我首先提出全行业微利;今年上半年,地产业将进入全行业亏损阶段。”在我们谈话的中间某个时刻,他的语气又一次斩钉截铁起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成本越来越高,但是利润却越来越薄甚至亏损的时代,这是一个不好玩的时代,我们称呼它为冰河世纪,谁都可以做房地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也许并非如此刻意悲观,但是假如他把这些观点全部放在私人博客里,一场观念风暴势必会从互联网的某个不知名角落酝酿、蓄势,进而爆发。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已经多次置身于这些风暴的中心,在那里,面对掌声、抨击还有谩骂。
现年59岁的卢铿从1999年就开始经历这样的状态,他并未表现出任何的不适应。1999年12月6日,他致信王石,在那封“面对新世纪,中国呼唤新住宅运动”的信笺中,他在全行业首倡“新住宅运动”。这封信获得了多位地产界意见领袖的认同,也从此成为卢铿以一个地产思想者的角色出现在地产业舞台上的标签。同年,中城联盟在广西创建。日后,中城联盟提出了一个与“新住宅运动”理念相似的年度主题——居住改变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这个主题与“新住宅运动”同脉同源,高度契合,卢铿则先于诸多同行置身地产业的先锋语境。
这是一封宣言式的使命感十足的信笺,它随后激起的赞扬与非议同样众多。在日后的岁月里,卢铿保持着自己爱好思考、反思,并经常在纸片上写下言简意赅、稍纵即逝的观点的习惯。他提醒他的来访者,如果一个人将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本职工作上,后果将是你无法胜任本职工作。他鼓励说,“应该关注你身处其中的大环境,你必须得经常想到它们。”
他正是这么做的。在记者与之谈话的北京昆仑饭店的咖啡厅,他座位边有一个装满了杂志、书籍与纸片的大袋子,在一个普通的文件夹里,一张张A4纸写满了序号,每个序号后面都是一个简短的思考议题,这些序号已经排到了300多号。
假如你和他聊天,他的回答经常从一个话题游移到另一个,专业的数据、相关的例证、看似宽泛的背景知识从他口中流利地一一说出。这得益于良好的阅读习惯。这样的思维习惯难道与他显赫的家庭背景没有太多关系么?作为上世纪30年代最知名的实业家卢作孚先生的嫡孙,卢铿很难回避这些。事实上,他职业生涯中的每一次重要职务变动,他的家世都会附带被饶有意味地提及。
这是挥之不去的标签,但是更多是一种暗示。卢铿在香港出生,除了五六个月大时被祖父吻过之外,他从未真正见过自己的祖父。“那更多是一种下意识,你的出身让你必须努力,将事情做得更好。”他说道。
作为一个明星职业经理人,卢铿姿态谦和,风度十足,语气平缓,也擅长描绘蓝图。在这个动辄遭遇民意抵触、政策调控的地产业浸淫十余年后,卢铿仍然保持着理想主义的特质。尽管他也毫不留情地批评地产业的粗糙与原罪,对普遍存在的低水平现状痛心疾首,他甚至已经承诺向本报写一个地产业三十大痼疾的连载专栏文章,但是,他仍然对地产业能够更好服务于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保持着持久的激情。在过往十年,他享有着对行业既挑剔又辩护的巨大声名。
卢铿再次接受本报访问,正值第五届国际绿色建筑年会在北京举行。在这个国家,“绿色”和“节能”已经成为最时髦的政治与经济语言之一。在访问中他提出了绿色人居的第二条道路,这是一条提供更市场化解决方案的道路,与官方行政主导色彩浓厚的第一条道路形成互补。
对话
寻找冰河世纪中的蓝海
十年痼疾仍待解决——关于行业
中国房地产报:与十年前比,地产全行业仍然面临哪些痼疾?
卢铿:地产行业存在大量的问题,很多在10年前发现的现在依然存在,官方与业界都在努力克服,但效果并不明显。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包括绿色节能建筑推广(不力),建筑风格(低俗、单一),恶性竞争(严重),保障房介入(对市场冲击),拆迁(依然存在问题),毛坯房太普遍,政策波动风险大,农村缺乏规划,建筑容积率过高,政府过分依赖土地财政,以及地产的辩论存在太多谬误等。
最近,我正准备写《十年地产市场化背后的原罪》,其中会详细提到上述问题究竟如何影响着今天的中国房地产。
中国房地产报:您所谓的恶性竞争具体指什么?地产市场化方向不就是鼓励更充分的竞争么?
卢铿:全行业号称有6万家有资质的开发商,这很说不过去。很多不懂行的都进去了,包括不懂行拿了地王的,这都是对资源的浪费。另外,国家公布的闲置存货有1亿平方米,这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拿了地的待建建筑量达到24亿平方米,还不包括未来地方政府将继续批的数目。当数十亿平方米的潜在量放在那里时,房地产市场就很乱了。
中国房地产报:如今地产市场的大调整很可能令这些问题更加难以解决,经过这轮调整,整个地产业的生态会发生什么变化?

卢铿:房地产将进入新的十年,格局也会发生根本变化。之前的十年大家希望土地涨价、房子涨价,但是,今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房价不再涨或者仅有小幅波动。住宅与商业地产将进入一个成本很高但利润越来越薄甚至亏损的时代,这或者是不好玩的时代或者是困难的时代。之前人们都想进来,之后或许都想出去。如何在这个冰河世纪里找到自己的蓝海,只有创新。创新管理,创新产品,通过创新寻找价值。在后工业时代里,人们希望在品质、品位、艺术等领域追求,所以开发商要学习。
中国房地产报:您为何提出了一个“小户大家”的理念?
卢铿:所有的成本都与面积有关,如果你省下这些面积,也许会过上另一种不同的人生。而重要的一点是,爱因斯坦说过,在他们那个年代,人的寿命大约只有五六十岁,他计算过,人的一生中约有17年时间既不在床上睡觉,也不在办公室工作,干什么呢?不知道干什么,但正是这17年决定了一个人的成败,这17年如果用得好会有很大成就,如果用不好,可能一事无成。你可能在社交,在学习,在阅读聊天,这一点正是我的“小户大家”理念中所提到的。我们的会所既不是财富的会所,也不是专业的会所,而是家庭的会所。住房部仇保兴副部长很认同我这个理念。
产融结合的纽带——关于海尔地产
中国房地产报:如您所言,海尔地产算是地产业的新军,它如何应对这样的变局?当初进入地产行业,是财务性回报的诱惑,还是一个战略选择?
卢铿:海尔进入地产是应运而生。之前有很多人请教张首席(张瑞敏),他曾说不做地产。6年前也是小规模在做,我去时规模也不大,今年也才20亿元销售额,明年可能突破30亿。但是他有很多资源可以嫁接,对于做大房地产很有利,比如,与银行、政府及并购对象的长期信任关系。
此外,海尔本身有自己的金融系统,如控股青岛银行,是长江证券第一大股东,(张首席)是海尔纽约人寿董事会主席,(海尔)有自己的财务、投资公司。另外还有一些自己的工业用地,这些地之前都在郊区,(成本很低),现在都变成了市中心。
集团认可的定位是,海尔地产作为海尔集团下属企业,承接海尔集团战略任务,即做美好住居生活的服务商,作为海尔内部资源的整合平台,发挥很好的价值通道。我们的模本做得漂亮的时候,很多开发商会去找海尔做订购产品。一个订购额可能达几千万元。最后,地产将成为海尔新的利润增长点之一。海尔家电做得很辛苦,只有2%的税前利润,但地产可以轻松做到10%。即便是一个项目做两年,算下来也可以做到7%~8%。
中国房地产报:您从商这么多年,也见识过很多的商业概念和商业战略。您内心是否真的相信商业模式的魅力?
卢铿:商业模式很重要,并购就是种模式。收购一些做不下去的项目,然后进行开发,或者,干脆在集团层面进行并购,这也是种模式。(我们在这方面的优势在于,)首先,银行相信我们,我们有品牌的优势;其次,我们有产品的理念优势。也就是说,我会用我的优势去拿到别人未必拿到的一个机会,或者是我拿到后可以做得更好的一个机会。而且,张首席一直希望我们把产融结合做起来。
家庭背景赋予了天然使命感——关于自己
中国房地产报:从您的博客以及您平时关注的话题与视野看,您有一种很强烈的精英分子的情结,是这样么?
卢铿:事实上,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一直不希望自己是一个开发商,如果我成天想着开发商的事,可能就不是我了。有很多时候,不能成天想地产的事,要把你的灵魂与思想从你的躯体里拔出来去想想别的事,想一些看似无关的事,会令你的本职工作更出色。(对于这种定位,)现在有很多说法,叫做公共知识分子、意见贡献者或者你所说的中产精英人物。
我们这一代人很容易有使命感,除了自己手头做的事情之外,总是想着其他领域的事情。社会就如同一个大木桶,企业就如同其中的一个小纸船,我们拼命努力,希望从这边划到另一边,去实现我们的理想。但是,如果木桶哪一天破了,水全部流了出去,那么,船也就不存在了。因此,企业的领导人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意识,如果集体缺乏,这将是一个危险的社会。
中国房地产报: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您从您的家庭背景受益很大么?外人一般都会想当然这么想。
卢铿:肯定会有影响,总会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家庭背景下,你会有更多的责任。我爸爸小时候在家里扫地,他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叔叔看到了,很赞赏他能够从事家务活,因为他那时候应该属于高干子弟了。他叔叔就对他说了一句话,“做你爸爸的儿子不容易”,这话影响了我爸爸一辈子,后来爸爸又告诉我们,也影响了我们一辈子。这是潜移默化的过程。
其实我从小到大,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无论是思想还是视野,都多多少少受到我祖父的影响,甚至于我来海尔做事。当时张首席与我谈了三个小时,其中有一个小时是在谈我的爷爷,他对我爷爷的历史很熟悉,令我很惊讶,这也打动了我。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张首席与我的爷爷是同一种类型的人,如果说我爷爷是前一个时代企业界的楷模的话,那么,张首席应该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楷模。他们都会研究很多社会问题,研讨一些哲学问题,想到国计民生的事情。
中国房地产报:您见过您的祖父么?有没有考虑将他的故事搬上荧幕?
卢铿:我五六个月大的时候,在香港他见过我,可是我并没有真正见过他。对我而言,家庭的背景以前是压力,现在是动力。上海电视台正在筹划拍摄他的电视剧,名字就是《卢作孚》,共36集,目前正处于审剧本的阶段。卢铿,1950年3月11日生于香港,祖父卢作孚是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旧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公司——民生实业公司的创始人。
1952年返居祖籍重庆,1982年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毕业,1982~1984年在冶金部武汉钢铁设计研究院工作。1984年下海。
历任:武汉大通实业有限公司开发部经理,香港大通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新加坡维信集团驻中国首席代表,华新国际集团总裁,上海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现任海尔地产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祖父的惟一遗产:
卢作孚虽是民生公司总经理,死后却无财产传世,卢铿得到的惟一财产是祖父题词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
语录: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不仅需要“小康,足矣”的观点,可能还应当倡导适度的清贫。有哲人告诫我们,“人生的最佳状态是保持轻度的贫苦,因为只有适度地容纳对立面才有利于主体的稳定存在。”中国的人口太多,如果为了经济目的而拼命地鼓励重利求富的全民趋向,很有可能导致整体上的战略失衡。
●西方国家都曾多次遭遇过房地产泡沫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所以中国的房地产一直是学者和媒体们特别关注的方向。不同立场的人们在关于楼市的争论之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偏向和利益趋向。其实,房子并没有疯,是人疯了。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城不在大,有“魂”则赢。城市的真正魅力不在于其规模和形式而在于其文化灵魂。如何找寻、反思、策划和营造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建设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的城市不应该成为在人文精神上“失语的都市”。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