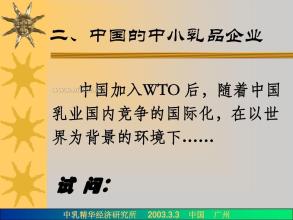控制与反控制
尽管双方在合资之初即约定合资公司的管理权归中方,但事实上达能对此并非心甘情愿,资本玩家的逐利本质决定了达能一直想全盘控制合资公司。这一点,在合资公司的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上就显现无遗。达能委派的董事对中方管理层的权限进行了苛刻的限制,而其中最让管理层无法接受的就是“任何一个超过一万元人民币的固定资产开支项目都需备一份详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方认为这样的限制表明了外方的不信任,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根本不可行,例如一个进口设备的零部件更换动辄就会超过一万元。中国的市场尤其是饮料市场情况变化巨大,管理层不可能在每年的12月份就将次年所有需要的开支列入准确的财务预算。由于董事会基本上是每个季度召开一次,如果合资公司的管理模式如此僵化,是不可能应对中国市场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的,因此,这一限制自然遭到了中方的反对。
一段时间以后,由于管理层的不断抱怨,加上最初五家合资公司的出色的业绩表现也让达能感到满意,于是达能亚太当时的负责人、合资公司的副董事长伊盛盟在1996年11月25日写信给宗庆后,提出了一个新的工作方式,即达能只在董事会层面发挥作用,而让以宗庆后为代表的管理层放手经营。
随着合资公司的发展和不断取得出色的市场业绩,达能的一直希望能够取代宗庆后实施合资公司的管理控制,屡屡劝说其退休、考虑接班人问题,以至于不胜其烦的宗庆后不得不给达能的总裁法兰克·里布写信进行抱怨。由于中方强硬的坚持意见,达能接手合资公司的计划一直未果。
达能显然不愿意看到娃哈哈在宗庆后管理下的快速发展,更不愿意看到达能收购的企业在与娃哈哈的竞争中步步退缩,因为这不符合其通过资本垄断市场的战略意图。达能斥巨资收购乐百氏,一方面是因为娃哈哈品牌毕竟不是达能的,达能对娃哈哈只是基于合资而享有收益。达能寄希望于缩减对娃哈哈的投资,通过资本运作直接收购乐百氏、汇源这类已经占据相当市场份额的成熟企业,只要能够维持住原有的市场份额,即可获得可观的利润,并且风险也相对较小,从而最终达到多元化品牌控制竞争,实现市场垄断的目的。另一方面,投资娃哈哈的新产品、新项目,则必然要冒更大的投资风险。资本玩家的特点显然决定了达能并不是一家致力于产业开发和拓展的公司,例如,2004年,当宗庆后就某一项目征求达能方面意见时,伊盛盟在一封给宗庆后的信函中就明确表示“我们(达能)经不起产品的失败(风险)”。这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达能的投资取向。因此,对于娃哈哈提出的众多投资建议,达能往往不是直接予以拒绝,就是推诿了之。面对中方管理层提出的合资公司产能缺口问题,达能不愿冒任何投资风险增加投入,而是要求娃哈哈以寻找代加工厂来解决,并放手让娃哈哈通过自身途径设立非合资公司来解决合资公司的产能问题,对于新产品开发,也是让娃哈哈自己承担全部风险,而达能则可以坐收其成。
达能对新投资项目决策的推诿和优柔寡断,严重制约了娃哈哈的发展。宗庆后曾在2003年11月16日写信给达能全球总裁里布,表达了对达能这种不愿投资只想坐享其成心态的强烈不满:
“但是我们发现与达能的合作已经发生了一些问题,作为我们公司需要发展,而且为了对付日益激烈的竞争更需要发展壮大,否则就没有竞争力,作为达能既都想参与又都迟迟没有明确态度(在此我要郑重说明的是我们并非一定要达能投资,资金、技术、人才我们都没有问题,纯粹是为了友谊),速度似乎变慢了,我们提议了几个新项目,如方便面项目,一直在等达能的回音是否参与投资,但现在快年底了,一些优惠政策将会到期,因此我们希望在年底前实施这个项目,但一直没有达能方的消息。”
“也许我们之间存在一些文化差异或对工作方法态度的不同,但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市场,市场竞争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要激烈,我们必须快速行动,而不是花大量时间等待研究结果,否则就会丧失机会。”
不仅如此,由于达能的秦鹏一方面担任娃哈哈合资公司的董事,另一方面又是乐百氏的董事长。这一双重身份使他一面在娃哈哈合资公司的董事会上详细了解娃哈哈下一步的经营策略,另一面则为乐百氏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推动其与娃哈哈相竞争。为此娃哈哈的管理层也多次抱怨秦鹏让他们感到左右为难。
在达能收购乐百氏后,宗庆后就在合资公司董事会上明确提出了抗议:
“另外就是要解决乐百氏的问题,不要让我们腹背受敌。实际上今年计划完不成与乐百氏的竞争亦有相当大的关系,以前可以毫无顾忌地与其竞争,现在中间夹了个达能的秦鹏,导致该竞争时没有去竞争,造成很多被动,特别是瓶装水与铁锌钙奶受的损失较大,所以亦希望要妥善解决好这一问题。否则的话明年我们准备不论是谁,一律开打,竞争到底,不然我们将没有后路。”
刀锋急转
达能虽然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资本玩家,但毕竟不是一个产业经营家,尤其是在中国这么一个市场情况对其完全是陌生的国家。短短几年之后,达能就发现它它的战略意图并未如愿以偿,乐百氏一步步滑入亏损的泥潭,其他陆续投资的汇源、正广和、益力等众多饮料企业的表现也始终乏善可陈,达能在中国的业绩因此大受影响。而与此同时,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开拓,娃哈哈则一路高歌猛进,
面对这样的难以控制尴尬现状,达能亚太的管理层不得不另做打算,再次调整中国战略。最终,达能将其目光锁定在娃哈哈的非合资公司上,在达能看来,这是一块极为诱人的蛋糕,2006年的总资产已经达到56亿元,年利润为10.4亿元。如果能够将这些企业一举纳入其囊中,达能亚太的管理层就可以“一俊遮百丑”,而其中国区的业绩也将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出于这样的考虑,达能在2006年下半年开始发难,指责娃哈哈违反合资合同,私自发展非合资公司,侵犯了本应属于达能的利益,要求以净资产价格收购非合资公司,来解决这一“问题”。
昔日一向赞誉有加的合作伙伴一夜之间忽然刀枪相向,娃哈哈在震惊之余,自然是一口回绝了达能的要求。而为了迫使娃哈哈屈服,达能也先后采取了威胁、利诱、四处告状、人身攻击、全球诉讼等种种手段。达娃之争自此揭开了序幕。
最初,达能方面提出可以在低价并购非合资公司的同时,向宗庆后提供6000万美元的补贴,这一非份要求很快就被宗庆后拒绝了。
在这之后,达能的态度就变得也更具攻击性了,不断写信进行威胁。据某些媒体事后报道,达能的秦鹏甚至亲自前往娃哈哈总部,“劝告”宗庆后,“跨国公司启动法律程序是十分可怕的”,“如果不答应,达能可以动用100亿元来和你打官司,不要为此落得身败名裂”。而达能新任的亚太区总裁范易谋则面对媒体公开威胁宗庆后,“我要让他在诉讼中度过余生。”
但看上去宗庆后并不吃这一套,双方就非合资公司的问题僵持了许久。从2007年年初开始,达能又陆续与商务部以及浙江省和杭州市政府接洽,状告娃哈哈和宗庆后,并且指出让达能收购非合资公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同时进一步明确了要启动法律程序的意图。
对于达能到政府部门告状,杭州市政府在2007年4月5日曾出面协调,希望双方保持克制,不要在媒体上打口水仗,双方的代表均答应了这一要求。但就在当天下午,达能就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面对媒体对娃哈哈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指责。达能的这一偷偷出拳行为,导致了娃哈哈一度在媒体上陷于负面评价的被动状态。
此后,宗庆后本人持续受到了大肆的人身攻击,有媒体上公开指责他“偷税”、“侵吞国有资产”、“持有美国绿卡”等等,甚至出现了“宗庆后是加拿大公民”的谣言,好事者借机大肆质疑宗庆后的全国人大身份的问题。但在国内、国外有关部门的详细调查之下,这些谣言都一一不攻自破。

随着2007年5月开始,达能陆续在瑞典、美国和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对娃哈哈及其关联方提起诉讼,双方的纠纷正式进入了法律层面。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双方也互相提起了众多的诉讼和仲裁。中国商业史上规模最大的合资纠纷从此轰轰烈烈地进入了高潮阶段。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