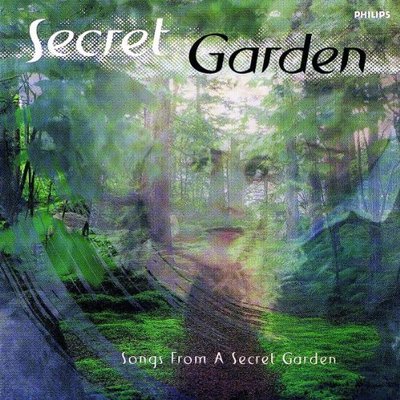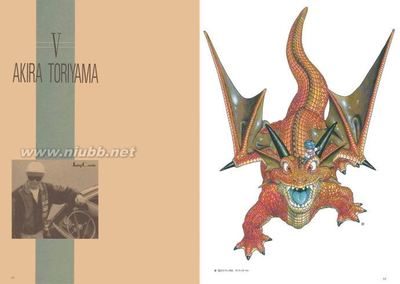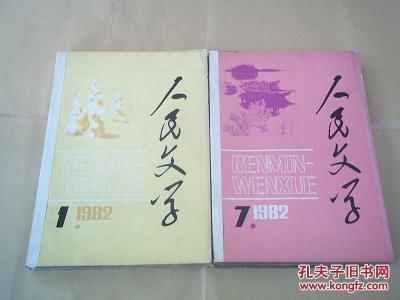“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严冬卧读陈智德君新著《地文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觉昔日各种绚烂,反照今日香港的彷徨,突然就想到江淹《别赋》这个棒喝一样的开头。《地文志》,于作者智德、于读者我,均是一场声势颇大而骤然收结的告别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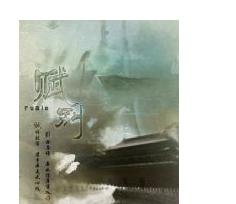
往日从智德或其他香港前辈、老前辈口中笔中,均有闻我城过往文化史上种种不可能的奇迹,奇迹由奇人造就,“奇迹”二字又抹杀了奇人们筚路蓝缕的血汗,一个半个世纪过去,如露电泡影,只剩下一个恍恍惚惚的时代光晕,教我们追忆时徒生憧憬,继而唯被怀旧消磨。智德一直在梳理那些尚未沦为一个笼统的“怀旧”幻象的人与细节,这次他终于找到一条可以明晰珠串它们的链子,那就是他自己的半生年华,一卷《地文志》写来,不但是对香港一代文苑风流的追忆,更是对一代青春的心灵史的回访。
因此他要架构的迷宫不同于一般的“人文地理”,地文志不同于古代的艺文志,也不同于地方志,大地有文,如水经注的水经,成文成经,有赖笔墨连缀。在香港长久被目为“文化沙漠”(亦有自嘲自贬)的时代,本地的文脉潜行并未自怜自矜,而那些作古的遗民、隐逸的文字耕耘者、神秘的书店奴隶……谁都没有留意有一个少年(此后是青年、后青年、前中年)郑重地与他们擦肩而过,把他们零星的火光都收集在自己的文字里,几十年后,用一本《地文志》建一个惜字亭。
地即文,生活即文学,这一点我们现在迟来的发现,从《地文志》看来,少年陈智德早就体悟了。如果你能想象他仿佛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收获季最后的拾穗者那份狂热和目光炯炯—他总慨叹“吾生也晚”,我却羡慕他能“攀上时代的车边”,他能在童年体验消逝的各种城市飞地,在少年时亲临初悸的社运现场,在青年投身高山剧场也即香港乐队文化的盛衰……这一切当他今日回溯,发现旧时代不但给了他怀旧的宝藏,更多给了他抗世者的气格和演绎这气格的铿锵文字。告别也是继承,在陈智德的文心中,可见他已沾染透了他所写及的抗争者或遗民的孤绝。
通过文学与地志写社运史、精神史,夹以诗人独有的伤逝情怀以及从伤逝中打磨出来的洞察,这里面作为诗人的陈灭对追忆者陈智德贡献尤大。《地文志》上卷最精彩的那几篇文章,时刻可见诗人的身影徘徊,或独语,或与其他幽灵对话。许多片段简直可以作为散文诗抽取出来独立成章,让我想起在钞古文时写《野草》的鲁迅,想必也是一样的从黯淡心境中回身竭力敲打出未甘沉寂的火星来。如“虎地”一文,从难民的魑魅,到一间大学的魑魅,到诗人们的魑魅,到自身的魑魅,浑然不觉地辗转而成,像写《横时雨》的丸谷才一,表面是考据是援引,其实在在是作自己不灭的青春祭。
作为一本文学作品的《地文志》,注目许多此前均为“传说”的香港断代文化史,视野广博又具体而微,其情低回熨帖,其笔痛幻交错,无论以散文论还是以文史随笔论,都是杰作。而从史料梳理与文学地理写作的角度看,它与小思老师的《香港文学散步》、《香港的忧郁》等名著互补,令我城那个不断被雾霾磨蚀的另一面精神的轮廓,继续挣扎呈现。赋别之后,文字仍有一缕离魂,与我们同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