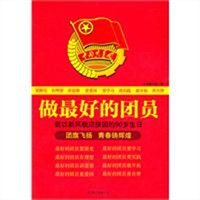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不是我的,而是一个陌生的日本女人的。这个陌生的日本女人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但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她带着那至今也不属于我的一万块钱,走进了我的回忆。
但这个不属于我的一万块钱,却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发展,事隔这么多年,我依然无法忘记它给我的思想带来的冲击和启迪。
那是20年前的一个春天,大约是1987年4、5月份,我为出国,去北京王府井那儿的中国银行分理处,去换国家允许我带出国的50美元!当年出国的人,估计都去过那个地方,那里好像是北京唯一指定换出国外汇的地方。
1987年,国家允许个人出国的换汇指标,50美元。精神文明丰富的中国物质文明之贫穷,由此可见一斑。
就是在那个窗口等待之时,我看见了我生命中的第一个一万块钱!一个日本女人,手上拿着那一叠钞票,在等着存银行。而且,那叠人民币,还不是一般的人民币,而是人民币外汇券。
人民币外汇券是80年代一种特殊的货币,只有外国人可以使用。比例大概是人民币的1:5倍,换言之,那个日本女人手上拿着的,不止一万人民币,而是一万五千人民币。
当时的我,几乎什么也没有想,只是默默地看着,没有感觉。这么多钱,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想过。当时的我在北大工作,虽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精神生活确实丰富,但经济上却非常拮据。诗曰:六人一间房,幽会要清场,月薪近一百,食油配八两。
在这样的物质环境下,我居然不感到穷,更没有任何改变这种贫穷的什么具体愿望和想法!当时我甚至觉得,安贫乐道,君子固穷,那是一种美德。后来在国外听到崔健那首“一块红布”,我才好像悟一些什么……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当时我在国外,已经“有地儿住”了,但我依然为那被歌声唤醒的过去生活而感到震撼和悲愤!……原来那块红布的作用,是让人忘记没地儿住,而且还让人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依然感到幸福!
出国前,那一块红布也遮了我三十年,让我浑浑噩噩但却“幸福”地生活了那么久,直到在国内终于感到实在无法混下去了,才想到要出国寻找幸福并至少知道了什么是幸福!
然而,即使就在那块遮天蔽日的红布笼罩下,我眼睛的余光还是看见了眼前这个日本女人手上那一万元人民币外汇券。它在我心中引起了如此深层的爆炸,以至于我在离开那里好多天之后,才感到那一万人民币对我的冲击波的力量,这个冲击波的力量,可以说一直到今天还在蔓延!
那一万人民币外汇券对我到底产生了什么冲击?
我记得我回来告诉我身边的朋友,今天在中国银行看见了一万人民币外汇券。然后,我给他们算账,我在北大月薪100,如果要凑到那么多钱的话,需要不吃不喝150月,12年半,才能达到这个数字。当时我已经三十岁,也就是说,根据我当时的收入状况,我要挣钱挣到42岁,才能挣到此时此刻这个日本女人轻松捏在手上的那一堆彩纸!
从来没有为金钱郁闷过的我,就在这个计算中,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渺小,卑微、无奈和可笑!我未来12年的岁月,折合成国家给我的金钱,为什么只值这个女人手头捏着的那点纸钱?
TMD。即使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我也依然不禁对三十岁以前的迷茫愤愤不平!我不仅不要面子,我TMD也不做徐老师了!徐老师也要养家活口!徐老师也爱钱!我为什么不爱钱?我为什么不能爱钱?我为什么不能大张旗鼓地说:我爱你祖国,以及钱!
我生谁的气?我生我自己的气。我对当时的我自己怎么就不能让自己的老母、老婆,以及尚未出生但注定一出生就要找我哇哇要粮吃的徐超徐赶他们,也拥有那么一叠人民币外汇券!先把家庭的事情弄好,然后再去解决社会的问题——事实上,所有一切社会问题,只不过是个人和家庭的问题的集中反应而已——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够教育自己的公民,努力把个人和家庭问题自己解决好,岂不就是帮助国家和政府解决了社会的重大问题?……
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两不误,经济收获与精神财富双丰收……TMD,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明确确立那种目标,努力追求那种责任,拼命实现那种成就呢!
我承认,我当时做不到,因为,那是一种积五千年文明牛粪之大成养成的人格,它是一种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打扫干净的“奥斯亚吉的牛圈”。不经历脱胎换骨的精神折磨和摧残,无法扫尽。后来我出国奋斗的漫长过程和痛苦经历,证明了我现在的论断。
生于50年代、长在60年代、成熟在70年代、思想解放在80年代的我们,对于金钱财富物质市场的观念,是一种非常扭曲的观念。扭曲不在于我们接受的那些红布教育,扭曲在于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党转变工作战略之后——原来我党是在1978年之后才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来的,这就是现实!——整个社会价值观念和机会变异带来的那种对固有思维的冲击和摧残!
拨乱反正,政策上的一切也许容易,但人心上的一切才是最难最难的。
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走出金钱意识、财富意识和市场意识的沙漠,
犹如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法老暴政统治下的埃及,是一个民族的新生。
问题是,摩西带领犹太民族走出埃及,是一种可见的行为。不走的人,会被摩西的下属驱赶鞭打着上路,实在不想走的,留在埃及也许就意味着死亡。
而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走出金钱财富和市场的沙漠,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心灵深处的精神大迁徙。它看不见,摸不着,关键就在你是否信它是否跟它,是否在实际行动中采纳和追求它。这是一个别人不知道,自己也不确信的过程,它是一种茫茫大海中看着北斗潜心夜航的信心远征!

在茫茫大海上,柳传志走出来了,俞敏洪走出来了,张朝阳走出来了,无数人都走出来了……
走在前面的人,可能成为了时代先锋、社会精英、成功典范,但留下不走的人——那些依然意识不到金钱机会、财富机会和发展机会的人,却非常可能沉浸在没有风险没有动荡没有困扰的环境中,慢慢没落,渐渐衰亡。在百舸争流、一日千里的时代面前,成为人群的沉舟,成为社会的弃儿,成为家庭的叹息……
而我,深深庆幸自己没有落在社会后面,虽然我未必走在时代前面。也许生在江南小镇,没有京城关系的我,对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有一种本能的拥护和认同,因为改革开放,改的就是机会不均等,放的就是机会被压抑。
但我总觉得,如果不是生活种种机缘巧合、一波三折的话,我很可能只会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当作一种思想学说,只会歌唱在口头,而不会落实在手上,使之真正成为我个人人生价值追求的一部分。
但是,在王府井附近看到这个日本女人手上一万元人民币兑换券,一举撤下了蒙在我眼睛上五千年文明腐朽丝线织造的红布,擦亮了我的眼睛。
诗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来寻找美金。”从此,随着出国,我开始了从一个传统追求依附并期待从依附中得到物质保障的知识分子,向一个独立自由知识分子转变的伟大历程!
谓予不信,请看另一篇文章《我初到美国时的经历》,那就是这一伟大进程中的第一次泸定桥!
向前进,向前进,自由的责任重,传统的腐朽深。
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徐小平,打工为活命!
向前进,向前进,自由的责任重,传统的腐朽深……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