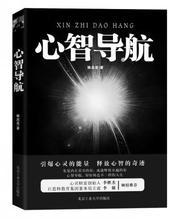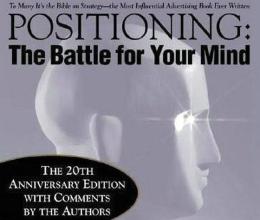李嘉诚居然承担下来了。他不再上学,他最先努力的乃是适应社会这所学校,到茶楼做“茶博士”,到舅父公司里做小职员,在五金公司做街头推销员,虽然艰难,然而却可让一家人能吃上饱饭,而且他也很快了解、熟悉了社会的各色人等和谋生的诸种方式。社会对于他不仅是严厉的、残酷的(他完全了解到在那里不能做着感情的交易,他的情感也因此很少外露,他避免一切感情的冲突),而且对人的每个举动都有着呼应,“天道酬勤”,世道无欺,他来了,他看到了,剩下的只是他如何自处和报世,他如何展开、“征服”和成功。应该说,李嘉诚做得相当出色。少年的欢乐、人性的懒散和嗔欲,在他身上几乎找不到什么迹象。他的精力几乎完全花在生意上了,花在与人与钱打交道上了,花在挣取他和家人活命的资本上了。令人惊奇的是,他丝毫没有放弃学习,他用到废品站收购旧教材的方法自学而掌握了基本的知识,包括英语这样的交流工具。学习甚至成了他生活和事业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他仍每天坚持听英语新闻。这样一个人的成功几乎是必然的。
凡是跟李嘉诚同过事的人都对他的能力有着极深的印象,几乎没有人认为他会甘于平庸:寄人篱下,做一个小小的打工者。他在刚刚步入商场时表现出一种学生的心态,除了像学习功课一样地努力工作外,李嘉诚将他认可的做人准则放到工作中,放到处理与他合作的老板和工友的关系中。以诚待人,这个少年对环境的老实姿态,延续成为他的做人方式,李嘉诚因此在商场上获得了很高的信誉。数年之后,他已是经理人了,并很快拥有了自己的塑胶公司,那样近乎手工作坊的企业,李嘉诚命名为“长江”。从塑胶企业开始,他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极好地担当了自己的家庭。在塑胶行业,他领先风气,并且也较早地预感并应对其衰落。父亲的“盈亏有定”的教育在实证中一定给他留下了印象。他涉足地产业,每有举动,似乎逆流而行,但他取得了成功。60年代他虽然一度入籍新加坡,但总的来说,在弹丸之地的香港,阴晴不定,时来风雨,人心飘忽,李嘉诚显示出了难得的定力。在歪打正着的印象背后,他是一个掌握了人生辩证法则的大师。他在市道低迷时收进,几年后他的产业成倍地升值。到70年代初,他已是香港小有名气的成功商人了。
无论李嘉诚是否以商人自居,他的作为却已超越了单纯的社会角色。用时下流行的话说,他追求第一,在每一领域里都追求最好的,不仅要在地产业超越百年老店英资置地,而且他把公司包装上市,他收购英资,在市场上最重要的领域里他竞争过了英资。与其他华人资本家一起,取代英资成为香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力量。不断挑战自我,永不放弃学习,使得李嘉诚在众多的领域里都能进入最高境界。他能够将塑料杂志上的信息转化为他工厂的主要产品;能够及时发现香港产业发展的方向;能够熟练地应用股市来进行他的企业扩张;能够精确地计算出一个上市公司的合理股价;甚至紧随全球经济波动确定他在其它地区不同领域的投资。到八九十年代,李嘉诚的发展已超越商人一词的简单含义,从一个街上遇人就推销的混生活的少年进入了当代世界精英人物之列。在传统产业里称雄的同时,李嘉诚也能在新经济里呼风唤雨。他不仅与世界著名的企业家银行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还与一些国际政治家交上了朋友。他的家族市值一度占全香港的1/4.他一个人的财产相当于我们中西部几亿人的财产总和。用古人的话,他已经“富可敌国”。在大陆、台湾的政治神话远遁之后,李嘉诚给予了另一种神话,黄金白银时代的神话。人们不用强迫即释服,不用劝说即跟从。这是一个生活在我们中间却把我们的欲望调动起来的超人。
三
在追寻李嘉诚独一无二的性格品质时,我们应该考察他成长中作用于他的可能的情况,这些情况需要“还原”成我们易于感知的人情世故的实在图景,李嘉诚的心路历程应该是我们能够猜想也能够沟通的。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在沉默和崇拜外获得平常的心态。当少年李嘉诚要独力支持全家人生计时,他会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呢?生活的艰难对他的思想和做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事后的追述总会让人感叹造化的神奇,如西哲对西方历史的解释,“剧本早已写好,只是等待历史的展开”。解读李嘉诚的人生轨迹仿佛如是。
如前说,李嘉诚有一个正常的童年,并受到的良好的教育。其对李嘉诚的影响是极难得的。马克思曾称赞希腊文明,以为那是正常的儿童,其创造的文化有一种高贵的品质,健康的心态,是后来者不可企及的典范。李嘉诚出身并非大家、 世家子,他出生于小知识分子家庭,在生活和世界的边缘,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也是健康的,他们聪敏、灵气、良善、温情,不走极端。但对大部分受过良好童年教育的孩子来说,接下来是青少年时期的一帆风顺,如果没有意外的悲剧使他们颠离生活的轨道,他们将信守自己生活的真理,并以此解释整个生命历程的诸种经验。多数人会由此气宇不大,成为社会里的一类型,而非独特的“这一个”。然而,文明转型的艰苦降临在每个个体生命和家庭,无论自愿或者被迫,他们都必须重新寻找生活的基础,必须重新建构对于生活和世界的认知。在此意义上, 那个时代的草根知识分子及其后代,都在参与着对社会既有规则的改造。对于具体的个体生命来说,是某些偶然的、神秘的因素规定了这样的努力成为悲剧或闹剧,从“自铸伟辞”的革命者沦为神坛下蜷伏的奴婢,或者成为自立法则、自创王国的大师、巨匠。李嘉诚幸运地成为后者。

李嘉诚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这种情况使人对世人真面目、世态炎凉有过早的洞察。他所尊崇的父母在生活面前的无力,也一定导致了他对人生的早熟的体验。早熟的生命,总是蕴含着不尊重生命,对人轻视、敌视,对公正平等的深深 的怀疑乃至嘲弄。生存环境残酷,则往往会导致偏狭、报复的心态,导致了机心、谋略、实用等等。
但是儿时的良好教育以及对家庭的责任担当,使得李嘉诚能够避开那种早熟的人生虚无的一面,而对人情世故有着实在的把握:在求人中,生自励自助之心,同时也获得对世界同情的了解和爱。其良好健康的心态发展至此不是偏向乖戾,而是更为壮实,这一健壮的人格,对人性有基本的洞察把握,又绝无幻想、浪漫,即对什么是付出,什么是获得有入骨的理解。而避免感情外露、感情的冲突,在市场上搏杀不无冷血残酷,对敌人的算计能以10年20年为期,其坚忍、工于心计也许正由于这少年时的不幸。
也许对李嘉诚的人生境界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其父亲李云经先生了。李嘉诚年少时曾在半夜醒来,看见父亲仍在灯下批改学生作业的背影,这件事给李嘉诚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文明史上总是有一些最平凡普通而也最伟大的场景,充分说明了生命的自我实现形式:无私、爱、无人闻问的付出,只对天地或说自我负责,至于世人理解这生命到什么程度,就不是他所关心的了。对李云经先生这种小知识分子,我们社会里最常见的理解方式是:穷酸一辈子,那么辛苦,什么也没得到,不值得。我们蒙垢的灵性忘记了感动,忘记了正是这样千千万万的人在支撑我们的文明。
从李嘉诚多年以后多次谈及此事看,父亲及其行为已成为一种象征。父亲和那一场景是对李嘉诚人生境界最有力的挑战、警示和支撑。不能只为名利,只做一个名利之徒,人生在世,有可能成就一种高尚的境界。李云经先生的为人,是作为儿子的李嘉诚不可超越的,那一境界只可以追随,可以参照。李嘉诚在社会上再怎么成功,如果他不能像父亲一样对世界有忘我的爱,如果他不具有父亲那样的境界,他就不可能告慰一生穷窘的父亲。
德国大诗人歌德有句广为人颂:我年轻时领略过一种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这是我的烦恼。对李嘉诚亦如是。领受过,就起作用,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李嘉诚由寄人篱下到富可敌国,也就是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个人的生命状况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然而,我们看不到他有什么张狂和戾气,他仿佛无视自己财富的滋长和力量的扩张,只是沉稳地、老谋深算地注视着下一单生意。这期间既有职业金融家的敬业精神和职业伦理,又有着传统文明对财富的韬晦之术,有着传统的对世道人心的提防。纵观李嘉诚一生,他一直坚定地维护着自己的“规矩”和本分。中西文明在他身上,在他那一代香港商人身上有着较好的结合。 西方文明在中国的展开极为复杂,国人只有在极短的时间里像日本人一样饥渴地、疯狂地学习,更多地时候在自傲与自卑、敌视与谄媚之间徘徊,而西方文明扮演了掠夺者、施惠者、肢解者、友爱者、守旧者、激进者各种角色,最终纷纷被扭曲、消解;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神权的辩护士,自由主义成为腐败和剥夺的保护伞。传统的命运也是如此。而李嘉诚们在无言中,在亲身履践中将敬业与勤奋、财富积累与本分、自尊与孝顺成功地统一了,正是在这方面,李嘉诚给我们的启示是有益的。
四
需要说明的是,李嘉诚在50年代的成功之后,在已使自己和家人衣食无忧之后,为什么没有改行,为什么没有读书?
在创业初期是有要像父亲那样从事教育的想法儿的。“知识改变命运”,他后来更深刻地领悟了,并以此为题拍摄了专题教育节目。他告慰父亲的方式之一就是捐助公益事业,在大陆,最为称道的是建设汕头大学和附属医院。他在汕头大学先后捐助20亿元,尽管这所他一手创办起来的大学至今在学术方面、在毕业生对社会的贡献上并无可观。李嘉诚对教育的认知促使他以父亲的姿态来监督弟妹的学业,同时自己也学习不辍。但是,李嘉诚在刚刚成为企业主之初的“小富即安”或转业想法并没有影响他后来事业的扩大。在当时的香港,竞争迫使企业只有不断地发展壮大才能生存下去,近乎自然的要求使得李嘉诚最初的想法不自觉地消失。李嘉诚进入塑胶行业仍然是一个模仿者,年轻和善于思考使得他敢于尝试新事物,发现并生产塑胶花使得他很快在行业中树立了领袖地位,并为他积累了相当的财富,这种求新本身也会改变他的初衷。
对李嘉诚来说,很容易发现,如果不把读书作为一种做人的方式(立言),如果只是把读书当作一种工具、手段,那么职业已无分别,重要的是从知识中获得内在的自信和外在的能力,重要的是做人和做事(立德和立功)。
我们的传统以为“太上有三不朽”,其上为立德,其次为立功,其次为立言。其实,德也就在功和言中。做人,他已在绝境的拼搏中感受到人的自由。在他所处的香港,个人在归属感上的受限和无能为力(父亲和儿时教育给予他的家国情怀至此已苍茫无限),使得对个人最具挑战最有诱惑最有机会的是市场,这是生命力量实现的最好地方。这也许是李嘉诚被逼入市场上发现别有洞天,一样可以实现人生多种需要,而终扎根于市场的原因。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了解李嘉诚何以在商场上拼搏了一辈子,何以终生如此勤勉。李嘉诚曾总结说,一为挑战自我,一为让股东满意。在身份认同不太紧要的香港,他对自我实现的要求更为强烈,他要在自创的王国里的成功也极为强烈,那里有着对一种共同体和个体价值感受的真实情怀。
那也是东西方文明、资本、社会的聚焦之地。香港的幸运在于,它在冷战的岁月里,在一种动荡然而又基础稳固的条件下,成就了一个全新的华人群体。香港的50年,其社会环境有如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不断持续创造性的社会变迁。这种政治经济机制和社会环境叠加在一起,使得人的活力一旦发扬,成就是惊人的。政治、文化方面的无以突破,却给了行政、经济领域无限的机会。
尽管李嘉诚们对政治一直保持距离,在商言商,颇有欧美早期的清教徒之风,但他们的生活和事业已与政治、文化、文明和国家牢牢地系在一起了。这一点尚无多少人注意到。50年代从事加工企业与全球性的政治动荡相关就不用说了。从60年代末开始,李嘉诚在香港的所有收购举动都与内地政治变化有关:内地“文革”造成的香港移籍潮让李嘉诚在1967~69年收购了不少廉价地产;70年代后期内地“文革”停止,实施改革开放,曾经吃过共产党苦头的英资怡和在香港的信心出现动摇,李嘉诚趁机与其直接竞争并一举收购和记黄埔;80年代初,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的争端再度给市场带来动荡,李嘉诚逢低收购港灯和青州英泥;他甚至计划在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后联合其他地产商一举收购置地公司。这期间,李嘉诚借助政治气氛在股市中低进高出而大获其利的操作更是数不胜数,他不仅赚得利润,还因此赚得救市的声誉。
从穷困少年到“塑胶花大王”,从地产大亨到救市的白衣骑士,从超人到新经济的领袖,从管理大师到传媒高科技弄潮儿……李嘉诚的路还在继续,他几乎一直在捕捉先机,发出时代的先声。在一个行业、一个产业、一种潮流里领先,从小到大,从夕阳产业到高科技产业,到后来,跨产业、行业、领域,由经济到文化传媒到政府公共领域,他总能占据主动,引导前行;这位以资本为对象的战略大师一生学习不辍,敢于尝试新的未曾接触的领域。他对产业趋势的判断和市场时机的把握非常准确,从塑胶花到房地产,再到石油、电视以及当前对数码港、中药港计划的热衷,每次都不仅适应产业趋势的变迁,而且推动了社会的潮流。到后来,李嘉诚不仅富可敌国,而且与一个地区的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有了难解的联系。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那种知足、守常、中和、自给也在李嘉诚这里得到超越,用学者们的话说,他是跃进到现代化的永无止境的变动之中。
李嘉诚浓缩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上百年、几代人的历史,一穷二白到发达的进化历史。这种跨度之大在历史上是罕有的。
他是否一步步地失去了平常心?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