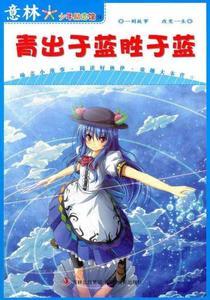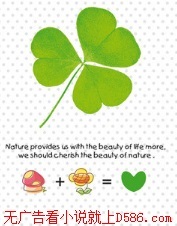特吕弗在电影《野孩子》中讲述了一个在丛林中长大的野孩子被带回文明社会的故事。野蛮如何被文明渐渐教化是这个故事的核心,但在电影末尾,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本能和天性的力量在野孩子的眼神里闪烁。这一幕启示我们,教育在驯化心灵的同时是否也对天性构成遮蔽?
历史行进到当代,“西方的没落”早已被斯宾格勒宣告得广为人知,这个问题的意义终于得以凸显。当人类被文明的病痛折磨得轻飘飘、软绵绵之际,释放天性、激发本能才是疗救之道。在文明的病体上施以野性的刺激,使其找回原始的生命力。这就是“野孩子”存在的社会学依据,也是其合法性的全部来源。
尽管形象粗野、作风生猛,但鉴于其本质上的恶作剧甚至撒娇气质,“野孩子”并不总是让人讨厌。尤其在创意紧缺、拒斥平庸的电影领域,“野孩子”的出现常常伴随着阵阵欢呼。布努艾尔、法斯宾德、昆汀、贾樟柯……我个人的“野孩子”导演名单早已列得很长很长,可是,我仍然迫不及待地想在这份名单上面添加一个名字:郝杰。
这个生于1981年的年轻导演已经拍了两部电影:《光棍儿》和《美姐》。两部电影都扎根于导演的老家——张家口市万全县顾家沟村,影片中都出现了野孩子的形象。前者兴致勃勃地用木棍戳捅着土墙的缝隙,这是其不多的游戏项目之一;后者则在美姐的嘴对嘴喂食中萌发性意识,进而一发不可收地恋上了她。当然,儿童形象并不是这两部片子的主体,但两部片子均由此切入,这既奠定了影片的狂放不羁、野蛮生长的基调,也昭示了导演的“野孩子”气质。
《光棍儿》聚焦农村老年光棍儿的性欲问题,迟志强《光棍乐》阿Q式的自嘲歌声掩盖不住汹涌的性饥渴,说荤段子、听黄曲儿是可以公开的精神娱乐,暗地里却有更多的解决之道:偷情、嫖妓、买老婆,甚至还玩同性恋。影片通过四个光棍闲坐聊天的场景结构全篇,正如《云之南》导演阿格兰德所言,这有点像古希腊戏剧的唱诗班效应,串联起整个村庄的人际网络。围绕性资源的分配,农村生存的真实图景得以展现,甚至还辐射到了历史、国民性等更为宏大的命题。
如果说二人台——走西口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民间小曲——在《光棍儿》里只是偶露峥嵘的话,那么在《美姐》中则是绝对主角。它歌咏、见证甚至推动着铁蛋与美姐及其三个女儿二十年的情感纠葛。导演借助这个故事隆重推出了二人台,因此片名《美姐》并不能准确概括剧情,英文片名《The Love Songs Of Tiedan》(铁蛋的情歌)同样不能,铁蛋的二人台情歌才最恰当。但这种对民俗文化的展示、以个人命运映照变迁历史的手法看起来实在眼熟,从《活着》(皮影戏)到《霸王别姬》(京剧),这是第五代的拿手好戏,连王全安也在《白鹿原》(秦腔)里玩了一手。因此,相比《光棍儿》,无论题材还是结构,《美姐》的独创性都差了一截。

当然,与上述导演的他者视角和奇观化表达相反,郝杰的优势在于身处其中。那些生活已经融入血液,他只需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听从直觉和本能的驱使,燃烧自身,表达自我,就能最大限度地抵达真实。因此,如果说贾樟柯让中国的县城第一次真实而富有质感地呈现于银幕,那么,郝杰则第一次在电影中表现了真实的农村。与贾樟柯电影诗意的抒情气质不同,郝杰的影像表达更为赤裸、直接、粗砺、野性,不讲究,不批判,不抒情,不美,只忠实记录自己对土地和生活的理解,而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真实质地赋予影片以最大的力量。
乐队众人的剪影在戏台上演奏二人台,化入小铁蛋在向日葵地里奔跑的画面,《美姐》的最后一幕不可谓不美,也不可谓不意味深长,但就是太不“郝杰”了。可见,野孩子也有乖巧时,但愿郝杰保持蓬勃的创造力,新鲜的气息常在,无所顾忌的劲头不减,生机勃勃,尽情撒野,在一路狂奔的路上不失本心,只与他本人越来越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