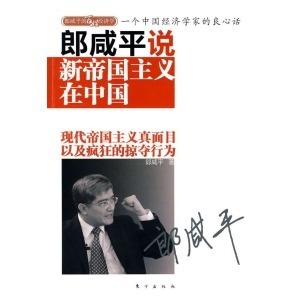没有公平公正交易就不可能繁荣,不讲诚信,不守规矩,交易成本就要增加。打击贪腐势力,建设和谐社会,正是为发展经济服务,为经济繁荣保驾护航的
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郎咸平选择了再次开口。如果说那场以国企产权改革为主题的大辩论,已经把郎咸平卷入了一个极大的漩涡,那么这次,他选择了一个可能更为敏感的领域—对腐败势力的挑战。
“近来发生的一系列官员腐败事件让我感到怒不可遏,痛不可堪。”郎咸平对《法人》说。当然,愤怒不应该是一个学者面对此类事件的唯一手段,对于在经济学领域造诣颇深的郎咸平来说,尤其如此。虽然他关注的很多问题已经超出经济学的范畴,但他的落脚点仍离不开商业规则的建立和商业环境的完善,而他用以分析论证的方法,也显示出了经济学者的理性态度。
每个人可以按照正常的企业经营准则来经营企业,施展你的商业才华,获得你应得的,正当的丰厚利益——“这是我的梦想”。
为了这个梦想,郎咸平又要投入战斗了——“当然,是以我自己的方式。”郎咸平说。
我为什么不研究潜规则
《法人》:无论是从文章还是演讲,都感觉你是个锋芒毕露的人,但你写的研究报告却比较平实,这似乎有点反差,你能给这个有趣的现象一个解释吗?
郎咸平:所以认为我锋芒毕露,纯粹是因为我透过研究而发表的观点和当下国内所谓的经济学主流的观点不同,而我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绝对不会因为畏惧学霸的权威而有些许犹豫,经过这两年多来的论战,现在整个社会基本上已经理解了国内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之中一些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地方,而且也已经理解了我的公开发言都是以事实或数据作根据,我绝对不是因为想哗众取宠而说一些偏激的话。过去媒体认为我偏激的言论,后来都证明了我观点的正确性。例如德隆和科龙的出事,国企MBO损公肥私等等问题。在以数据为本的前提下,我演讲时很投入,现场气氛比较激越,而且针对问题一针见血的提出我的观点,没有犹豫,因此与听众很能形成互动,这可能就是所谓的锋芒毕露吧。
但是我写的文章非常注意逻辑的连贯性,环环相扣,我从不把演讲的语言放在文字当中,我更不会用激情的语言来阐述我的观点,因此看我的文章就要很用心。在这种环环相扣的逻辑之下,编辑要修改我的文章就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只要删了一段,前后就连不起来了。所以可能读起来较平实罢了。
《法人》: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提出,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些不成文但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但你的研究是不把“潜规则”纳入演讲范围的,这是否可能导致结果上的偏颇?
郎咸平:吴思先生所谓的潜规则是非常深刻地描述。法制化的建设在外国很容易推行,但在中国就很难,因为法制讲的就是规则,而一个缺乏讲规则的民族,必然形成一套适合当地社会生态环境的潜规则,这就是吴思的锐利观察。我一再呼吁建立法制化的社会,就是要引导中国人从没有过的对规则的敬畏,因此就要打破现在的这些潜规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把潜规则纳入我的研究范围的原因。
腐败不符合商业逻辑
《法人》:我注意到,你对反腐问题的很多观点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你是不是觉得要解决经济长期发展问题就必须跳出经济学范畴而先行解决社会问题?
郎咸平:是的。在当下中国,腐败势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瓶颈,也是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要取得更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先要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这个就是功夫在诗外的道理。这一次的波及北京上海天津的反腐败战役缔造了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少有的新局面。大家看一下中国的民间和网上民众的反应就会知道,这次反腐战役获得了社会上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支持,这是一个好现象。
在过去28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当中,没有人可以否认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这个改革也伴生了一定的副作用,那就是腐败产生了,出现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政府中央决心反腐败,老百姓又痛恨腐败,因此中央和老百姓之间才能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共识。
《法人》:你提出的“腐败铁三角”中,政商关系(更进一步说,是政商交易)从来就是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依靠政商关系建立的经济秩序,有可能是一个次优选择吗?你呼吁要敢于冲破潜规则,但潜规则是否有“存在即合理”的可能?
郎咸平:我想从一个严谨的角度来谈问题。不用谈什么深奥的经济学理论,仅仅从最普通的商业逻辑看,商业的繁荣要依赖适宜的社会环境。没有自由就不能经商,没有平等就不能对价,没有公平公正交易就不可能繁荣,不讲诚信,不守规矩,交易成本就要增加。而腐败势力滥用公权力肥私,其对应的社会代价恰恰是商业环境的被破坏,社会环境的被颠覆。经济的发展是增加国民福祉的硬基础,你破坏了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你还奢谈发展经济不是缘木求鱼吗?反过来说,打击贪腐势力,建设和谐社会,正是为发展经济服务的,是为经济繁荣保驾护航的。我们中国,要想富民强国,只有依赖经济的发展,而严厉打击破坏商业环境的腐败势力,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吗?

胡锦涛总书记讲反腐败是当前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我个人认为这是懂经济的见解。过去20年的改革开放,国民受益颇多,但是,谁在其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呢?是社会大众吗?还是中央政府?都不是,改革中最大的不当受益者,是我归纳的腐败铁三角。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腐败的政府官员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勾结腐败的学者而形成的腐败铁三角,他们影响着媒体,欺骗社会大众,误导中央政府。大讲腐败是经济发展之必需,之不可避免,还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这是无知还是无良?在当下中国,诚信不足,监管不力以及商业环境不容乐观,背后基本上都是由腐败铁三角作祟所致。长此以往何谈经济发展呢?腐败铁三角打着改革的旗号大肆敛财,收刮百姓财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毒化了经济繁荣所必需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商业环境。这个是媒体所没有注意到的实际情况。
中央政府将反贪腐当作核心要务来做,是非常正确和有远见卓识的。因为贪腐问题已经严重制约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中国持续改革之中的主要障碍。贪官们网罗的特殊利益集团,也成为了中国社会进步的真正瓶颈。只有彻底肃清贪官们编织的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改革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社会才能安定和谐。现在中国社会上一切的不正常现象,一切的不合理,一切的不可思议,这都是因为腐败势力所导致。这样的例子在内地俯拾皆是。刚刚去世的霍英东老先生,投资四十亿元在他的老家南沙,竟也长期遭到了当地腐败势力盘剥侵吞。其实,种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实只有看透其背后是腐败势力作祟方可理解。
《法人》:在你看来,当前一些不合理的政商关系是如何影响正常的经济秩序的?
郎咸平:当前,一些腐败势力编造所谓一切为了经济发展的口号,在这个口号掩护下做的事情却极大的损害了正常的商业秩序。举例而言,美国法律不允许美国商人或美国跨国公司参与当地的贪污腐败,必须按照法律行事。但是如果这个城市是由腐败铁三角所控制,外商就可能要作出一个矛盾的选择,你或者选择加入铁三角参与腐败,否则你就不能得利,或者你选择道义清白而却又无法生存,你要怎么作选择呢?我知道你想要选择清白,这才是企业经营的正确准则,但现实环境允许吗?因此这次党中央所推动的反腐行动客观上是帮助了好的投资人,因为他们日后做生意的时候,能够选择一个清廉的中国而不是一个由腐败铁三角所控制的中国,党中央这次努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清廉的社会,一个更干净的商业环境。
对于任何一个正直的投资人而言,你肯定希望进入的是一个更加干净的中国,一个利益归于全体百姓分享而不是利益全归于特殊利益团体的经济体系,你不需要下跪乞求铁三角给你提供便利,而你更可以按照正常的企业经营准则来经营企业,施展你的商业才华,获得你应得的,正当的丰厚利益。这是我的梦想,因此我本人坚决支持中央的反腐行动。而且,你们已经看到,我本人早就奋勇参战了,当然,是用我自己的方式。
事实上,对于所有关心中国未来走向的人,都要关注中国胡温新政下的反贪腐进程,因为,只有反贪腐成功,中国社会的商业规则才能完善,投资者才能在中国安心地做生意。中国的经济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进一步腾飞。
铲除腐败须用“铁腕”
《法人》:你在几次演讲都提到了“严刑峻法”这样的词汇,这是解决你认为的中国信托责任缺失的主要思路吗?鉴于这不是一个新鲜的提法,2000多年前法家已经开出这样的药方,历代王朝也不乏实践者,但效果都不甚理想。你在今年8月份的一篇文章中(《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提出“我们需要系统地解决问题”。应如何系统的解决问题?
郎咸平:我最近虽然没有在媒体发言,但我关心这个社会的心却从未稍歇。近来发生的一系列官员腐败事件让我感到怒不可遏,痛不可堪,不得不再次提出我对这个社会的呼吁。但是我所批判的角度不同于以往,我认为我们光杀贪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系统地解决问题,我认为近期一系列腐败事件所引发的问题,使得我们不得不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恶性事件一再发生,令我莫名悲愤!这样的官员、这样的行为,我真的闻所未闻。由此可见,体制内腐败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和行政能力,不下狠手、不出重拳、不用重典,是难以震慑这股腐败势力的。
中央这几年一直在致力于反腐。腐败会亡党亡国,没有人比国家决策人物更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反了这么多年,腐败官员仍然层出不穷,前赴后继。这就引发另一个问题,腐败难道仅仅是制度不健全、个别官员道德水平下降、法制观念淡漠所致的吗?除了法律法规,我们的整个社会和民间就无事可做,就没有什么制约力量吗?其中,最令我担忧的就是一方面体制内腐败屡禁不止,另一方面民间道德风气败坏,原本的正义呐喊之声日益微弱,并且二者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形成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我中华民族原本应当有这种力量。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针砭时弊、匡扶正义。但现在,当腐败渗透、堕落侵蚀的时候,你看到还有振臂一呼的知识分子吗?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险象就在于此。民间有话语权的人不负责任的自甘堕落,与体制内腐败上下呼应。二者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真正左右民间舆情的重量级人物会炮制这样的观点:腐败是好东西,是次优选择,它能促进经济效率和增长。民间精英为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对腐败坐视放纵,继续提供一个制造更多腐败的温床。这种体制内腐败和民间堕落的并存与互动,成为我国当前腐败事件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我们不应再坐视腐败与堕落的恶性互动蔓延。要清除体制内的腐败,亦需对民间堕落进行整治,以促进形成良性的正循环。对待体制内腐败和民间堕落这两种势力,必须分而治之,同样高度重视,正本清源,切不可使二者沆瀣一气,互相鼓吹包庇,混淆公众视听。而应尊重法律,切莫为其开脱,必须动用铁腕,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铲除腐败行为,对于视公众利益和社会安危不顾之官员予以严惩。同时,在民间大力提倡、培养正义之风、浩然之气,形成“公序良俗”,再不容许邪气压正。
民企应当“做强做大”
《法人》:根据全国工商联数据统计了一下,在2006年民营经济500强中,前13名的营业收入都过百亿,第100名企业的营业收入也有20多亿,而在1999年的时候,民企500强的总营业收入才2000多亿元,还不如2006年10强的总和。从这个数据看,民企做大的趋势非常明显。但在你发表的观点中,对于民企做大(“民企目前的能力不容许做大”),似乎很不看好?
郎咸平:中国企业家有两大特质,第一是投机取巧,第二是浮躁。中国企业家怎么成功的,基本上是找到一个好的专业切入点,再加上碰到好的机运而成功。但是第一步成功之后,投机取巧的个性立刻显现,比如勾结地方官员批块地图利,或则抄袭仿造别人的产品等等,而不再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的解决企业成本控制等等问题。此外,中国企业家的浮躁个性使得他们想立刻进入世界五百强,这是我所谓中国企业家“世界500强的病态心理”,最好的办法就是收购兼并做大做强,以前TCL的李东升批评我的观点,他说企业不大一定不强,他这种错误的思维带给了TCL无穷尽的后患。中国企业家还没有做大的能力,我建议企业家改变思维,由“做大做强”改成“做强做大”,有小做起一步一脚印的解决企业方方面面的问题,争取在小范围内做强而后在强的基础上做大。
《法人》: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重要,但我们将以什么样的思路来发展民营经济,你在这方面有什么好建议?
郎咸平:我经常提的一句话——中国根本没有夕阳产业,中国的夕阳产业都是由夕阳思维所造成的,我建议中国的企业在任何领域都要有先做强后做大的心态,任何领域都能在这个思维之下形成朝阳企业。
回眸近期官商勾结大案
刘志华案
2006年6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因生活腐化堕落被免去职务。北京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今天审议认为,刘志华的错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决定免去其副市长职务。6月16日,刚刚从香港返回北京的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还没有走出首都机场,就被中纪委工作人员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带走。除了刘晓光,现已有数名北京房地产企业高层被中纪委叫去“协助调查”。
祝均一案
2006年8月,原为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的祝均一已被撤销职务,祝均一出事之因是,其在2002年前后挪用社保基金,为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提供高达32亿的“贷款”,该笔款项正是彼时福禧收购沪杭高速的主要资金来源,而福禧投资董事局主席张荣坤也已案发。此案同时涉及上海电气集团董事长王成明、上海电气董事韩国璋等高管。
何闽旭案
2006年6月23日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被双规。从2005年6月由安徽池州市市委书记升任副省长到被“双规”,仅有105天。一刘姓地产商供出了何收受30万元贿赂的事实。
徐放鸣案
2006年9月15日上午,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徐放鸣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徐放鸣在任期间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并受贿214万余元。
徐放鸣于1997年至1998年,接受北京诚奥达商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韩冰的请托,利用其主管金融工作的职务便利,向农发行推荐中国电子租赁有限公司承揽业务,使中电子获得农发行4亿余元的汽车租赁业务,而诚奥达公司也从中电子获得700余万元的中介费用。此后,在农发行深圳分行购买办公用房时,徐放鸣又向农发行推荐韩冰介绍的房屋,使韩冰从中获得200余万元。韩冰为感谢徐放鸣的帮助,分4次给予徐放鸣20万元人民币和10.8万美元的贿赂,折合人民币总计109万余元。
雷渊利案
2006年9月5日电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5日对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经济犯罪案件进行一审宣判,雷渊利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审理查明,1995年至2005年4月期间,被告人雷渊利利用担任郴州市苏仙区区委书记、永兴县县委书记和郴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的职务便利,在安排工作、承揽工程、解决政策优惠、减免费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周吉等人经手所送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21.0174万元。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