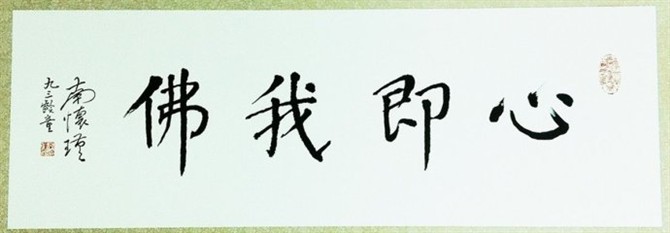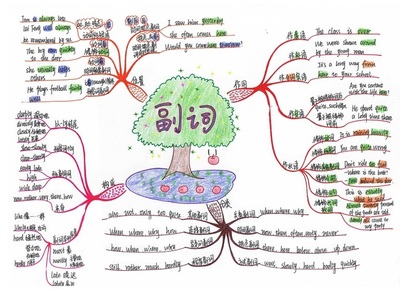金星的《中国制造:游园惊梦》
金星的《中国制造:游园惊梦》
金星一直勇于摈弃“鸡肋”。她在27岁放弃自己生来的性别,差点把自己的舞蹈生命断送在手术台上。33岁领养了一个弃婴,当起了单身妈妈。两年前她和德国男友汉斯结了婚,领养了三个孩子。近日,金星主演的《中国制造:游园惊梦》在上海举行首演,之后她将带着这个舞剧在世界巡回演出。舞者的孤独总是在台下。见到金星是在东方艺术中心的后台,长长的走廊上回荡着她略带沙哑的嗓音,还有被宽大黑色披肩遮盖的舞者的身体。数小时后上千观众将在舞台上看到这个身体舒缓绽放,披上艳丽粉红,吐露着杜丽娘纯粹而甜蜜的爱情芬芳。
金星说,那个舞台上的人才是真实的自己,跳着跳着,不管是杜丽娘、贵妃、卡尔米娜·布拉娜甚至是《狗魅》里的那条狗,扮演什么角色都不重要了。而生活当中的自己就是个角色,“ 可能我把这个角色做得准确,母亲像母亲的样子,情人像情人的样子。”说这话时,金星的脸还没化上油彩,没有涂上娇媚,素面朝天,棱角分明的刚毅。
人生如戏,金星从不记得自己有过痛苦绝望到失声痛哭的时候,她总是有勇气去摈弃她认为是鸡肋的东西:20岁离开中国古典舞蹈,作为中国内地第一位获得美国艺术研究全额奖学金的中国艺术家赴美深造,学习现代舞;27岁放弃自己生来的性别,差点把自己的舞蹈生命断送在手术台上;33岁领养了一个弃婴,当起了单身妈妈,她要求媒体不要公布儿子的照片,却对男友非常坦率,两年前她和德国男友汉斯结了婚,并领养了三个孩子,但对这三个宝贝丝毫不手软,谁做错了事屁股就要挨打。
2007年9月28日金星的《中国制造:游园惊梦》在上海进行世界巡演的首演,之后她又将带着这个舞剧在世界巡回,一演就是四五个月。
现在的金星不再是年轻时一次旋转就是50圈,但那时她的舞蹈是缺乏意境的,舞者征服观众的是技术,但舞蹈最能打动人的是意境,而意境需要年龄。“一个人在40岁时说的豪言壮语或者‘我爱你’,跟18岁时说出的,从语气到意味,都有着天壤之别。”如今坐在台下,观众都被吸入了金星营造的强大的漩涡中,忘记去分辨真实和虚幻。
此时39岁的舞者在舞台上已经活了30年。那里有的是灯光和掌声,而没有性别和误解,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B= 外滩画报
J= 金星
杜丽娘的爱情很纯粹
B:当初怎么想到做《游园惊梦》的呢?是因为你平时也很喜欢昆曲、京剧、古典乐,还是觉得现代演出需要中国化的包装?

J:我在八九年前就想过做《游园惊梦》了,因为1999 年的时候,我帮上海昆剧院做过《牡丹亭》的舞蹈设计,通过那四个月,我认识了中国古典艺术。杜丽娘这个人物很吸引我,她的爱情都是在梦中完成的,这样的爱情很纯粹。在现在的社会中,已经很难找到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做《游园惊梦》还不是很成熟,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把中国古典艺术包装后推出,现在是比较热门的方式。但是对于《游园惊梦》来说,我并没有把这个中国经典的作品包装,我是从内在分析杜丽娘的感情。完成《游园惊梦》的创作,是我的一个情结。
B:皮娜·鲍什刚刚在北京公演了她的现代舞作品《穆勒咖啡屋》,但是从演出上看,这不太像一个现代舞作品,而是很像一个动作哑剧。你的现代舞剧会慢慢演变成这样吗?
J:《穆勒咖啡屋》是皮娜·鲍什舞蹈剧场的著名作品,每一个人对现代舞的理解不一样,每一个人在不同年龄对现代舞的理解也不一样。对我来说,我不会像皮娜·鲍什那样去降低舞蹈元素。我的作品中,舞蹈的量都是非常大的。
B: 舞蹈的历史中,涌现出了很多的传奇人物,比如“舞蹈之神”尼金斯基,前不久,邢亮还以尼金斯基创作了现代舞作品。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创作一个尼金斯基的作品呢?
J:我想过,但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没有彻底理解他的每一个方面,所以我要再过些时候,才能创作尼金斯基的作品。
B:尼金斯基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名满天下,但是现在似乎艺术家成名越来越晚,这是什么缘故呢?
J:年龄的增长会让阅历增加,也让自己对世界的领悟力更强。所以,现在的艺术家成名不会像以前那么早。尼金斯基那个年代不同,当时的社会多么动荡,而且那时候的物质生活也远远不如现在,他自身的经历也让他过早地了解了人生。这在现在也是无法做到的。
有勇气放弃鸡肋
B:现在中国舞蹈界的培养模式,限制住了很多舞蹈人才,你觉得中国舞者的出路在哪里?
J:中国优秀的舞者被限制在了一种模式里,以至于很难有所发展。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从自己的思想上,走出这种模式。跳出来看世界、看自己。如果不能这样的话,即便出国了,在国外拿了大奖,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在很多地方遇到一些纷纷投奔国外的中国舞者,他们的状态并不好,还是会为生活忧虑。中国人在本质上,都会想光宗耀祖,所以,他们不在国外做出点儿样子出来,是不肯回去的,这样一来,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很不如意。
我觉得有思想的优秀舞者一定要学会放弃,放弃现有的一些鸡肋,然后让自己用自由的状态,和各个优秀的舞团合作,千万不要把自己限制住,而是要把自己的路越走越开阔。当初,我去国外学习,我创办自己的舞团,没有人给我指路,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但是任何的选择就是需要勇气的,有勇气放弃,才能有所获得。
B:中国的古典舞该如何走上国际呢?
J:我觉得中国的古典舞缺失的是个性,所以一定要注重个性开发,否则古典舞就会变成模式。
B:林怀民的云门舞集是华语地区最出色的舞蹈团体之一,但现在有人认为,云门舞集的作品已经形成了自己固定的模式,这么一来,突破就变少了。你怎么看待“突破”呢?你认为自己有一天会陷入自己的模式中吗?
J:在没成名的时候,人都会努力地寻找突破,寻找既能表现自己,又能赢得公众认可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人要承受孤独和指责,所以当成功到达以后,人就开始偷懒,开始向公众妥协,开始保持这个成功的模板。因为谁都知道,再去突破,就又要承受孤独和指责,失去先前社会的认可。对于我来说,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模式是什么,所以也就谈不上陷入自己的模式中。
艺术家的最高境界是无性别
B:有人认为在艺术领域同性恋者才能用两种性别去看同一个事物,感知艺术。你认为是这样吗?
J:我觉得艺术家不一定是同性恋者,但是艺术家的心态会是中性的,这确实可以集中男性和女性双重的观点。我觉得,现在的世界也需要中性心态,要不然这世界太尖锐了。中性会让人都缓和。很多艺术家到达一定境界的时候,心态会是中性的,但他会不会是同性恋者取决于一个层面上,就是他遇到的、能够理解他的人是同性的,还是异性的,如果是同性的,那就是同性恋,如果遇到的是异性,那就是异性的。艺术家的最高境界是无性别。
B: 你认为一个好的舞蹈作品,是应该让欣赏者领悟编者、舞者的意思,还是让欣赏者从这个作品中寻找到他自己理解的、能感动他自己的地方呢?
J: 我觉得肯定应该是后者。我创作一个舞蹈作品的时候,当然是按照我的理解去创作每一个人物、环节和构架的。但是对于观看者来说,我提供的是一种思考的空间。观看的人认为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也是艺术的奇特魅力吧。
B:舞台对你来说,是最有魅力的?
J:舞台上跳舞的时候,我跳着跳着,突然觉得那个舞蹈角色不重要了,在舞台上,但我还是在跳着,舞台上才是真正的我。生活当中就是个角色,人生如戏,可能我把这个角色做得准确,母亲像母亲的样子,情人像情人的样子。
B: 你经历了很多,遇到过别人对你误解,那个时候你怎么办?
J:我觉得时间是解决一切问题的良药,在很多时候,在事情发生的那个时段内,你怎么解释,怎么去让对方理解,都没什么用。等过了那个时段,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解决了,至于那些始终不能够理解你的人,也没办法强求,这也是一种缘分。不过,我也确实是一个心理调节能力很好的人,这太重要了。
B:你有不可接受的事情吗?你怎么看待人的心理底线?
J: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心理底线,我当然也有我的心理底线,这个底线,即便是再亲密的人也不可能逾越。也或者说,生活中,生活在一些方面是需要自我封闭的,人与人之间不需要百分之百的透明,这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B:但艺术家太敏感了,也就会太容易感受到不快乐。
J:是这样,但是艺术家是有释放痛苦的方式的,比如作曲家会用作曲来发泄,舞蹈家用舞蹈来发泄,画家会用绘画来发泄。对我来说,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是幸福的,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即便在这个过程中,经历很多痛苦,我也觉得没关系。这是创作的来源和自身思考的过程。
当然,艺术家确实是非常敏感的,而这种敏感也会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后的结果是孤独。所以,我认为对于艺术家来说,痛苦不是一定的,但孤独是一定的。文/张嫣 郝晓楠 图/Dirk Bleicker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