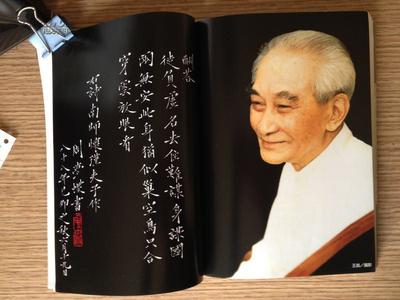采访44岁的广东省云浮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利平,潮州人直爽健谈的性格会打破你对官员“不苟言笑”的习惯认识。在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郑利平多次用“作为一名职业官员”为开头来展开自己的表达。郑利平说他做官既不为做老爷,也不为光宗耀祖,他将自己的官位形容为“只不过是份职业罢了,当然为官的责任有所不同。”
1996年,我在深圳市南山区任常务副区长。这一年,35岁的我突然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发展的平台期,有必要改变以往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而“欲穷千里目”,就得“更上一层楼”,于是出国学习的念头就有了。 幸运的是,那一年我正好赶上特区政府派50名副局级以上干部到海外接受培训,很多人担心出国会丢掉官职,所以包括我在内只有3个人报名。后来政府把门槛降低到副处级,报名人数增加到40多个,但经过严格考试最终成行的只有21个。 我是学机械制造出身的,但我一直对管理很感兴趣。我在中山大学读硕士时学的就是企业管理,我觉得技术就好比一条船上的动力轮机,而管理则是轮船的驾驶室。我先是到美国明尼苏大学做研究,并着手申请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公共政策及管理梅森硕士班。这个班是哈佛大学专门替发展中国家培养政治领导人的地方,曾荫权和李显龙等都是梅森班的毕业生。到我入学的那一届,梅森班已经培养了40届共1100位毕业生。
入学申请的时候,我将一篇探讨中国改革开放路径选择的文章作为申请材料的一部分,我比较了中国改革开放渐进式和突进式的不同路径选择,得出了中国需要走渐进式改革道路的结论。后来知道,不是文章结论,而是我理性、客观地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让这些哈佛教授们很感兴趣。因此,我如愿被寻取并在学习中获全额奖学金。 梅森班三个学期共12个月的学习生活让我受益良多。我所选的课程除了政治学和社会学外,更多的是对中国现实的分析和研究。一年的学习下来,我接受了哈佛“少一点价值判断,多一些实证分析”的研究态度。这种理性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让我回国后能够轻松驾驭繁杂的政治和经济工作。
1998年6月,在结束了梅森班的学习后,我有种尽快把所学知识实践出来的强烈愿望,于是在毕业典礼结束的第二天我就回到中国。有意思的是,正如出国之前很多人担忧的一样,回国后我发现自己的职位丢了。组织了解了我的情况以后,安排我担任深圳市外资局局长一职。后来云浮市换届,省委决定从发达地区派一名干部过去做市长。我有过海外学习的经历,就被调了过去。
在云浮期间,我把一些公共项目推向社会。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完成了95%以上,我们制定了全国第一个政府反垄断规章,设立扶贫基金对贫困户子女进行就业培训。这些想法无不受国外学习经历的启发。这几年我做了不少的改革,也遇到了不少的压力,比如我们推行农村居民健康医疗保险,但很多人认为这是给农民增加负担。在基层的经历让我开始重新思考改革路径的选择。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我认为渐进式改革的前提首先是要“改”。渐进的方向有很多,要完成一个改革有时甚至需要从数百个方面开展。这就需要把某些相互制约的方面打包成一个整体,并整块整块地解决掉。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研究哪些方面是应该打包做为一个板块来一次性考虑,更多的是只改一个方面,其他方面不动。这就造成改革难以操作进而造成反弹,反弹的结果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这种渐进方式不是我们要的,并不是我们走的渐进式道路不正确,而是缺乏好的操作方法。 西方管理技术层面的东西往往能够实证地告诉我们“如果做”的方法。海归需要克服的是“水土不服”的难题。有的人回国后觉得国内什么都不对他的胃口,什么都看不顺,觉得受到的限制太多。的确,中国这片土地上传统文化很深厚,我们往往被要求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这对已经习惯独立思考问题的海归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以我的经验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在保持一致的前提下,用足用活自己的“自选”动作,充分发挥地方上的自主权,大胆实践自己的想法,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去对现有体制做一些“补台”和“修正”。由于各种原因,我还有些想法不能够实施。但是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能够找到实践这些想法的地方。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职业官员,我的家人都在深圳,我与家人分居已达7年,我不会觉得有什么委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