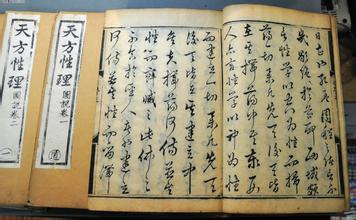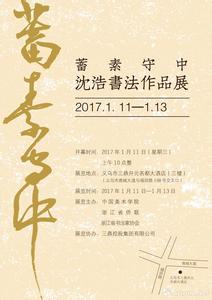系列专题:《中国十年之真问题:舒立观察》
-Q:我们常说新闻作品是"易碎品",现在让读者回过头去,重读这些文章,你认为价值何在?是否可以说,它提供了一种思想史,更具体地说是中国改革思想史意义上的史料? -A:说是"思想史"之史料,可能过誉了,但对读者或多或少还有些参考价值吧?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其一,新闻的易碎性,这确实是我们常讲的话题,也是客观存在。其二,正是知道了新闻易碎,我们才希望自己的作品不碎,至少不易碎。我在1994年出版的那本《改革没有浪漫曲》后记中写到,新闻本身是易碎的,但新闻记者对于永恒性的追求是始终不渝的。我是从日报的新闻记者做起的,这么多年,想的就是能写一点有生命力、以后看了不遗憾或少些遗憾的东西。后来,有机会做《财经》杂志,更是怀着这种心愿来做编辑、做记者的。

-Q:《财经》希望其作品"不碎",其标准是什么呢? -A:"不碎"当然也是相对的。我觉得,如果说有个标准,就应当这样衡量:作为时代的记录员,在每个时期写的作品,固然有那个时期的历史局限,但要寻求超越,从而能够经得起更长时期的历史考验。 -Q:这也许正是《财经》之所以为《财经》的原因,写"财经观察"时这种意识是不是更强烈? -A:我确实希望,这约1700字所表述的东西,能在比较长的时间站得住脚,回过头来看不感到脸红。1700字的容量非常有限,很难把每件事情都说得很周到,这就是为什么包括我在内的多位编辑不断地对其修改完善,甚至在大样上仍要看和推敲多遍的原因。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不能说每一篇都完美,但是,可以说,"硬伤"不是很多,这一点是令我欣慰的。 -Q:本书选入的140多篇文章,贯穿其中的思想就是为改革鼓与呼。我们不断地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时而加快,时而滞缓。这些文章也记录了这一过程。你如何评价改革的历程?是否偶尔也会感觉到有些无奈? -A:新闻评论这种体裁,与学术文章及一般的理论文章的写法是不同的,它追求快节奏的出版、语言和文章结构所带来的冲击力,因此,不应把新闻评论看做完整的学术阐述。以此为前提,"财经观察"确实倾注了对改革的急迫之情。尽管文章表达的向往,并不能都变为现实,只是折射了我们自己以及与我们心心相印的改革者们真切的心声,客观上对改革起到了"鼓与呼"的作用。回过头来看,有些文章不但是急切的,甚至是过于急切,这既是可以理解的,也还是有意义的。我们常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Q:《财经》的宗旨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三独"(独立、独家、独到),还有一种表述是"复杂的自由主义"。无疑,在《财经》的各类稿件中,"财经观察"是最直接地体现主张的。现在回过头来讲,你是否对实现的程度比较满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