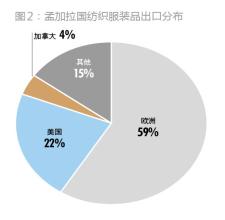商业社会
90年代末,郝舫开始赶上好生活。互联网来了,他成了第一代网民。“当时只有中科院和清华有网络。我那时开始写《灿烂涅槃》。yahoo,google都没有,在AltaVista上一敲,涅槃乐队有400多个网址。把我乐坏了。”
互联网特别适合他的工作习惯。在图书馆,他善于在文献引用中跟踪思想的脉络,在超链接中更是如鱼得水。
凭借无与伦比的音乐视野,郝舫成了MTV中国网站的艺术总监。“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互联网的工作经历是最有趣的。每天像吃了鸦片似的,生活在很夸张的气氛里。天天在聊天室里泡着就算工作,天下哪有这样好的事儿!后来我说Internet不垮,天理难容。每天花钱不挣钱,怎么可能?”
经济上的宽裕逐渐改变了他的写作态度。“现在写书是副业,文章也写得很少。我回到最初了,写作是享受。有话要说,想写才写。为了一顿饭东奔西跑的年纪,我已经过了。写作变成极其业余、很纯粹的事情。图个好玩,有快感就干。非要靠爱好赚钱,那真不舒服。”
尽管写作成了副业,但大学时养成的文化恶习依然未变。每到一个陌生城市,即便是拉斯维加斯,他也会查黄页、找书店和唱片店。他对生活的奢侈化要求也只限于一堆数字设备、高级音响,还有书和碟。房子的装修布局是老婆一手操办的,他所拥有的是三排大书架,一排书,一排CD,一排DVD、游戏软件和录影带。
最近几年,郝舫的作品包括《比零还少——探访欧美先锋音乐的异端禁地》,目的是让人知道摇滚乐原来如此多姿多彩,不光是泄愤的手段;《上车走人》译自亨利·罗林斯的传记《与“黑旗”在路上》,罗林斯是硬核朋克乐队“黑旗”的主唱。据说这本书是让不愿意吃苦的中国摇滚人看的。今年他与人合译了《请宰了我——一部叛逆文化的口述史》。
郝舫认为,这几十年来,最富创意的潮流,都是被商业消灭的,政治的迫害反而很少。90年代非主流音乐就是因为被商业过度开发,来得快去得快。“它们被富于野心的市场、资本主义、资本家征服了。在战斗过程中,为什么文化批评、学者、酷的创造者和拥护者拿不出一套办法来对付征服呢?你没有武器嘛。现在摇滚乐在中国不用像以前那么地下了,最大的敌人不是来自意识形态,而是市场化体制。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要学会怎么利用它,然后反抗它。”
但批评他今日文字的人也很多。有人写道,“你这两年的乐评呈现出一种极其病态的趣味,一味追求艰涩的文字,如果剥去一切的浮华和欲盖弥彰的无能,郝舫之于中国乐迷只是一个空享其名的卖字人。”
也有人为他辩护,“郝舫的方向注定在高处,虽不胜寒,但依旧沉浸于自己的乐趣之中,这是一般人所无法体会的,那种无法自拔的沉溺是用苦心孤诣和形影相吊等价交换而来的。”
末世情结

好多人以为郝舫就是一个对哲学、摇滚乐感兴趣的人,但他却说,“摇滚乐只是我感兴趣的很小的一部分。”现在他更喜欢的是——启示录文化。
“启示录其实是西方人对一类文化的统称:人类已经堕落到一个阶段,这个场景和《圣经》启示录描述的景象差不多了。从反面来讲,人类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很多人认为,恰恰是在这些最阴暗的地方,而不是前途一片光明。比如,很多侦探片有连环杀手,这不是犯罪现象,是文化现象。很多人从连环杀手看到人类未来可能发生的症状,在美国就有很多做学问的人在研究这个现象。每个时代总有一个特别的精神病。这个精神病是社会造成的,是下一步社会变动的集中表现。”“邪恶有时候就是有趣的代名词。文化取向上,我不太喜欢光明正大的东西。我喜欢研究因为受压抑变得很邪恶,或者本身就很邪恶的东西。”
郝舫自称绝对的科幻迷,具有cyberpunk小说的专家级水平。他还提到《黑客帝国》、《攻壳机动队》、《银翼杀手》以及其他我们闻所未闻的作品和作者。
“那些想象中的城市应该是阴森的,湿漉漉的,每一步不可预知,同时它又是物质极度辉煌的。人们就像在一座迷宫里一样彷徨着,颓废着;但又可以过自己需要的生活,他出于无奈去做着不想做的事情,而且做得很了不起……”
他手头同时在操作的有几本书。比如吉姆·莫里森的传记;比如《酷回忆》和《艳回忆》,从个人角度谈谈这个世界上最酷的人和最艳的女人。
谁也无法预料他的轨迹,没准什么时候他会写出一本让都市人共鸣的小说,因为他觉得能够反映中国城市荒谬感的书几乎空白。
“我喜欢看不同的说法,喜欢新鲜的东西。这个对我一辈子的审美倾向、观察倾向,有决定意义。”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