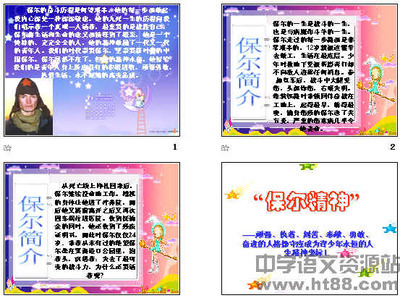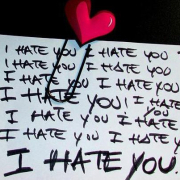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解决好人的问题,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让农业经营有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这是一串很诗意的表达,给人们一个非常鼓舞的愿景。但是,实现此美丽愿景,不但要帮助农民,尤其重要的是要给农民以平等公民的政治经济权利,权利平等既是体面的内容也是体面的前提,万万不可缺失。 理论上来说,中国历史上农民的地位从来不低。士农工商的划分,一直延续两千多年,在主要的四种职业中,农民地位仅次于读书的士人。在给农民以较高地位的同时,历代还把农业叫做本,商业叫做末,通过重农抑商政策以保护农业,扶持农民。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奖励耕战。勤恳耕田的农夫,如果给国家缴纳足够多的粮食丝帛,就会被免除服兵役的义务,从其他诸侯国亲来秦国耕田的农民,还可以免除三世的徭役。从事农业并向国家缴纳若干粮食丝帛的农民,还可以得到官爵,这就是所谓的“粟爵粟任”。除了奖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外,商鞅对非农产业和产品征收重税,“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汉朝建立以后,刘邦继续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征收很低的田租以奖励农夫,禁止商人衣丝乘车,禁止商人做官,向商人征收重税,以打击商业。这样的政策,后世多有实行。 但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农民的地位从来并不像统治者所标榜的那样崇高体面。汉朝建立不久,作为高官和思想家的晁错,就看出这个问题。他给皇帝上书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为什么国家尊农夫而农夫却贫贱了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粮食虽然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但以种粮而快速获得财富,却从来都是不现实的。司马迁深刻地指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司马迁在《史记》中还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可见,在汉朝那样的时候,追求富足生活就已经是人们不言而喻的追求,并且人们清楚地知道从事什么职业来钱更快。既然如此,人们当然会选择能够更加快速致富的职业而不愿守着土地受穷。 从事农业不能致富,无法体面生活,那么,离开土地而从事工商业就成为很正常的事情。这是一个市场选择的过程,通过市场的选择和配置,使农业和其他职业达到平衡。但农民的自由选择威胁到皇朝的粮食供应,因而,也是从商鞅开始,国家就实行了严厉的户籍制度,禁止农民迁徙,也禁止农民转行,作为农民,必须世世代代束缚在土地上为国家种田纳粮,成为给国家种粮的工具。这体现了国家对农业的极度重视,却决不能认为是国家对农民的极度重视或极度尊重。国家重视农业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条件为前提的。 农民不可能从耕田种粮中得到体面的生活和社会地位,这种状况,在近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可谓登峰造极。 上世纪新政权建立后,极为重视农业和粮食,“以粮为纲”长期是中国农业政策的核心。但对农业和粮食的重视恰恰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前提和代价的。严密苛刻的户籍制度下,农民不能转行,不能迁徙,农民必须永远在出生地为国家生产粮食;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使农民失去了对自己种植的粮食的任何支配权,种田的农民反而是大饥荒最惨烈的受难者;城乡二元壁垒下,城市人与农村人所实际拥有的权利有天壤之别,权利的缺失使得农民这个职业完全成为二等公民的代名词,千方百计逃离农村,告别农民,不遗余力“跳农门”“农转非”,成为农民们几十年中望断天涯路的梦想。农民职业,何谈体面! 今天,中国的粮食生产再次遇到挑战。户籍制的松弛使从事农业的人越来越少了。粮食问题随即摆在全社会面前。今天,不可能再用强迫手段“驱民归农”。中央农业会议描绘的通过帮助农民,扶持农民,使农民成为一种体面的职业以鼓励和引导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成为必须的选择。但是,根本上来说,仅此远远不够。农民职业要体面起来,最关键的是要落实农民的各项权利,使农民真正成为国家平等的公民。 目前,农民作为中国人数走大的职业群体,却没有自己的组织。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商会,农民却没有农会。人大中的农民代表也往往并非真的来自于农民。农民的利益与诉求没有表达和维护的渠道和机制。政治权利的缺失使农民处处成为弱者。作为公民应该一视同仁享有的教育、医疗、社保以及其他公共福利公共服务,农民大多享受不到;国家对粮食的干预使得农民连粮食市场议价权也不具备。这说明,农民身份的不体面,源于农民权利的不健全。把农民作为中国公民应该享有的平等权利给予农民,农民身份就会体面起来。如果农民的平等权利不能落实,那么,国家的扶持和帮助也并不能让农民体面起来,这一点,两千年前的晁错也已经清楚地看到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