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际遇十分奇妙。都是新亚毕业逾40年素未谋面的老校友,本来肯定是我有生之年也没机会相识的了。有历史系的,有英文系或其他系的。我是哲教系又是研究所毕业的,1967年在历史系重读学位。夏仁山学长是重读中文系学位的。自1961年起我与王兆麟兄同时在中文系任教大一国文的兼任讲师,不料在1968年遭遇被裁员的噩运。此后兆麟兄得到钱师母胡美琦女士的推荐去了圣保罗中学,我则在新亚附近的圣母院书院任教。每天下午四时放学,便匆忙赶到新亚上课,选修了全汉升、李定一、陈荆和、刘伟民等名师的课程。由于时间紧迫,根本没法与同学们倾谈。所以当时同读历史系的陆、黄诸兄,压根儿无法认识。直到41年后的2010年,意想不到的奇遇发生了。接到我曾担任文学审评员多年的艺术发展局邀请参加酒会,并允许可偕同一位亲友参加。仁山兄欣然同往。在酒会中他认识的新朋旧友极多,因此使我认识了历史系的黄浩潮学兄。次年艺发局又来函邀请,仁山兄亦有同往,因此又认识了叶永生和陆国燊学兄。黄、叶两兄多年前已从政府教育、司法机构高职退休,至今仍为香港社会作着贡献;陆兄则自中大出版社退任后,复受陈万雄先生礼聘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总经理。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在酒会中有仁山兄介绍相识,即使在酒会中与上述诸学兄擦身而过,还是不会相识的。这个世界上,老师中有良师,朋友中有益友,任何人必定在一生中可以遇到几位良师益友的。60年来,自我完成新亚哲学教育系学业以来,不包括中大、港大,我在新亚已遇到很多良师益友。良师中使我最钦佩最敬仰的其中一位,便是钱穆宾四师。当年(1953年)我与李杜、张乘风、颜锡恭、吴业昭等毕业于协同圣经学院后,为了要亲炙这位大师而来报考新亚的。同学也有多位益友,可惜多位已经作古,而仁山兄可说直到如今仍是我最相知的益友。新亚四年大专生活,他带我去涂公遂教授家中玩,一同称呼涂伯伯涂伯母,因他们的长女是我们学姊。涂伯母十分好客,假期常去涂府吃喝玩乐,使我这位独在异乡的异客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20世纪70年代,仁山兄把我这位连考两年中大教育学院的备取生变成正取入读(因有一正取生弃读让我补上)。近年,仁山兄又使我结识了多位老校友,我曾多次对仁山兄说:“你退休后还这么忙,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现在仁山兄又使我认识了多位鸿儒,当中包括丁新豹教授,真使我有高攀不起之感。说真的,我们这班老校友都很怀念艰苦创办新亚的钱穆老师,我们在多次茶聚中常常谈起这位终身为中华学术不懈钻研而卓有贡献的一代大儒。可惜在1962年时,在钱师担任院长兼所长及教授达12年后,他老人家竟突然宣布要辞职。后来幸得经济系主任张丕介师的坚决挽留作罢。但到翌年(1963年)时,他坚持辞职,而且不愿以退休名义离校。如果当时有校友们同学们群起挽留他老人家,可能会有转圜余地也说不定。(按:10月5日见到雷竞璇校友在《信报》专栏写的《钱穆在新亚》一文中说:“钱穆信函说‘在新亚真如一大噩梦’,此话极重,也极堪玩味,他说的噩梦是‘新亚’,不是中文大学。……人性中有共患难易共富贵难的弱点,钱穆辞职时,和他一起创立新亚以及共事多年的同人没有谁离去。未知是否反映内部不一致……”)宾四师辞职后,仍居港一段时间,我去拜访他几次,他从不向后辈诉说心事或闲谈他人。某次谈及我本身时,他才讲了几句。后来在台北,何佑森兄向我谈起过。宾四师的好友罗忼烈师在其《缅怀钱穆先生》一文中,也曾谈到一些。但不论如何,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名人学者,其生前的遭遇,多有不如意的。但他们对发扬中国学术文化的卓越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宾四师亦然。宾四师爱护新亚的心也是永恒不变的。宾四师辞职后,南洋各大学争相礼聘他,有聘他任教授或做校长的,他选了一间任教授的,可惜水土不服,最后于1967年赴台北定居。老友张晓峰先生请他担任文化大学研究所的教授,直至92岁退休,屈指一算,他在文化大学教了25年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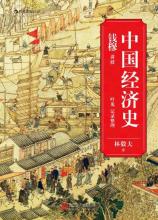
如果,钱师留在新亚教下去,一直教到92岁,那我们新亚数以千计的同学都可亲近这位不世出的大师,岂不是新亚校友之福?可能有人会说,钱师在新亚辞职那年已是69岁高龄了,怎么还可以教到92岁?普通一位教授当然年届60或65岁已是退休之年,但大师级的教授是在全世界都备受尊重的。例如我们新亚首届校友余英时教授年逾八旬,至今美国知名大学还仍争相聘请他为讲座教授;又如多间知名大学争着礼聘他担任客座荣誉教授的饶宗颐选堂师,今岁年届95高寿,杭州西泠印社还礼聘他为社长。名师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如果钱师80、90岁时还在新亚的话,也可以像台北文大般每周只请他讲学一次也做得到。这对我们新亚今后得以亲近名师的数以千计学弟学妹们,真是何等大的福气。钱师从来不为自己的名利着想,他曾亲口对我说:“两万港元与一万港元的月薪是没有分别的。”他也从来没有为自己置产,直到他病逝那年,现在仍在台北监狱服刑的陈水扁,当年要钱师迁出素书楼,钱师母为了争口气,在市区买下一间屋,房钱付不起,还是一位书商讲义气,多付出一笔版税才能成交。这是一位出版家告诉我的。钱师主持新亚校政的十几年里,先是住在九龙桂林街和嘉林边道的学校宿舍,后来租住钻石山的西南台和沙田的和风台,生活的清苦可想而知。即使他定居台北以后,文大与故宫博物院给他的研究费每个月都是一万元台币而已。可是钱师牵挂着新亚的心却是永远的。记得钱师自台北来新亚参加35周年校庆,筵席上林院长诚邀他40周年庆时再来。我有幸坐近钱师旁(只隔两个座位),只听钱师低声回应着:“那时我可能不能来了,如果人死后有灵魂的话,我是会回来的。”听了使人心感凄酸,但老师爱新亚之心溢于言表。现在老师已逝,一切希望和想法已成泡影。所幸老师还留下丰硕的宝贵著作,让我们后辈研读学习,老师的学术思想将永垂不朽。钱师在经、史、子、集各方面的宏言傥论和卓越见解,我们后辈当谨记勤习,使中华学术文化日益发扬光大。过去数月来,与上述诸学兄茶聚中,当我提起想把钱师的“讲学粹语”出版时,学兄们均表赞同。于是浩潮学兄要我把这些拟出版的资料尽快交给国燊学兄评阅。包括钱师的手札以及讲学粹语和多篇对钱师生平的报道,连我曾在《信报》刊载过的“历代人物经济故事”和钱师讲述的“中国经济史”两个专栏作品也一并送审,国燊学兄又请毛永波先生一起来研商何者可先出版。凭永波先生的卓识和锐利目光,认为多年前友人周淑屏小姐在壹出版刊印的《中国经济史》,已缺售十余年,但该社已不出版学术书籍。因此钱师《中国经济史》之得能重见天日,实在衷心感谢国燊学兄之重视及永波先生之识见。也要感谢编辑经验丰富的张宇程先生。他将钱师讲述的中国经济史,准确编排了朝代,订正了在报章作专栏刊出时的一些疏误,成为一册相当完美的学术与知识兼重的历史书籍。也感谢尚学中心的王龙生兄,为此书影印文稿付出了很多精力。最后,希望爱护本书的读者不吝提出宝贵的意见。叶龙于香港九龙2012年10月26日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