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文”一词,按其广义,可以指任何具有某一特定主题的文章。在此按圣教书会所定下的狭义,专指为了宣扬道德而进行宗教宣传的小册子或说教作品。它们的目的在于开启人们的心智,净化越来越广泛的人类生活。中国这一古老帝国的人民在许多项发明和各种社会实验上均领先于西方,所以他们先于西方编纂这样的说教作品,其实也在情理之中。跟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中国人把言谈记录下来的最早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圣贤教诲的影响力,使他们的名言可以传达到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圈子里,因为口头交流在空间上最多只局限于几英里以内,在时间上也只能流传几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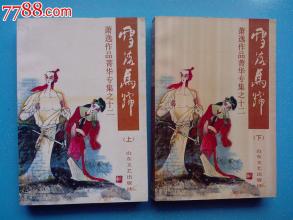
出于同样的理由,中国人使用比欧洲人早发明六百多年的印刷术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大量复制这些说教作品,而一千多年以来,他们所印刷的这类文本不计其数。即使是只挑最有影响力的那些说教作品,也可列出一长串的名单。而要对其逐一进行简单评论的话,则根本就不可能。然而,我们可以将其明确地划分为以下几类:劝人向善的作品;劝人行义的作品;劝人避恶的作品;宣扬特定宗教或神灵的作品。对于每一类作品,我们可举一两个例子就足以把此类文章的特点和规模阐述清楚。在第一类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孔子和孟子的语录,同时还包括其后众多哲学家的论文。正如我们习惯把圣经与说教作品区分开来,这类文章,或至少是孔、孟的书,可被视为中国的“圣经”。西方的许多说教作品几乎全部是从圣经中摘录出来并重新编排的段落。在中国的本土文学中,也有大量此类说教作品是以引用经典著作为主的。|www.aihuau.com|60例如《明心宝鉴》精选了中国圣贤们最经典的论述。它们就像精工雕刻的宝石那样闪烁真理的光芒。在其他说教作品中,这些语录出现的顺序和位置也许会有所不同,但无论置于何处,它们都放射出智慧和德行的光芒。有一本叫《名贤记》的书在北京很受欢迎。跟《明心宝鉴》不同,这本书所收录的主要是现代著作中的经典语句。它开篇即写道:“积德行善,勿问将来。”第一章的结尾处又这样鼓励人们说:“欲望可敛,天道可依。”书中的另一句话大体概括了全书的主要思想:“行善第一,诚信得福。”书中每一句话都是格言。跟希伯来谚语一样,其中一些格言劝告人们勤俭节约、指导人们如何为人处事,但也有不少的格言层次更高。遗憾的是,这本书中的宗教思想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一些苍白无力的描述,与希伯来谚语中无处不在的对一个活生生的上帝直接负责的概念形成了对比。这使得中国人的宗教信念成为最实用主义的。事实上,直接负责的概念在此类书中并非完全缺失,只是没有得到充分地强调。在包括此书的几乎所有同类说教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下面这样的警句:神灵注视邪恶的念头,清晰得如同犀利的闪电;从暗处向人们喃喃耳语,后者听来却如隆隆雷声。著名的《朱柏庐治家格言》①则为治家提出了一整套令人赞叹的规诫:教育儿女要严厉,对待下人要仁慈,贞洁和荣誉是家庭气氛中的最重要因素。《弟子规》的知名度虽不及前一本书,但其层次更高。这部基本上与我们属于同时代的作品所模仿的是声名远扬的《三字经》,但成就却更高。仅就文字而言,它让我们看到,当今之世圣贤之言也未完全销声匿迹。在题为“真与信”的第二章中,我们还找到了在中文书中很少见的下列训诫: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见未真,勿轻言;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还有这样一个简洁明了的定义: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作者接着补充道: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增一辜。《圣谕广训》收录的是康熙和雍正的圣诫,篇幅不长,也可归为与上面同类的说教作品。事实上,它的每一章都堪比一篇专题论说文。没有别的书能比它更好地体现了一国之君想要宣扬的道德准则,而这些道德准则跟基督教教义有许多相通之处。上述这些作品都宣扬了纯儒家学派思想。这些书不无宗教因素,因为书中到处都提到了一种模糊的主宰一切的力量,即“天”。它们还承认,无论这种力量是什么东西,它都能支配人们的行为举止。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