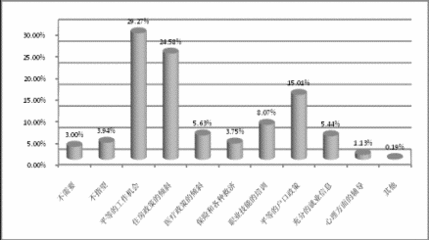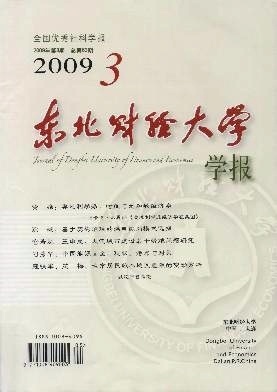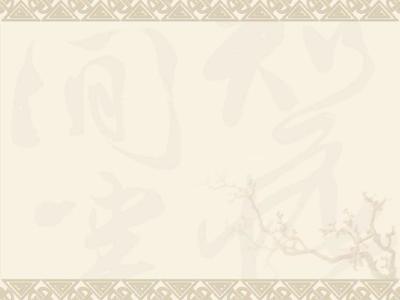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与社会中的个人息息相关。许多环境问题,归根结底都可以说是个人行为失调的结果。所以,能否合理地引导、影响和改变个人的行为,使之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是环保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正因如此,对个人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的研究,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是环境社会学领域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参见Dunlap/Catton 1979; Buttel 1987; Kuchartz 1998; Diekmann/Franzen 1995; 王民1999;洪大用1998, 2005)。
对环境意识的比较规范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始自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则基本上是从90年代才开始的(王民1999:116,127)。人们进行环境意识调查与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将环境意识作为社会价值体系的一个部分,通过包括环境意识在内的民意调查,可以了解社会价值的变迁情况,另一方面则是预期环境意识可以转化为实际的环境行为,因而寄望于通过环境意识来预测和引导人们的环境行为。国内外大量的经验研究的结果显示,从总体上讲,世界各国的民众都已经普遍具备了较高的环境意识。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会导致民众在环境行为方面也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可以直接体现在人们的主观信念转化为具体的日常行动上,也可能以间接的方式体现出来,即民众的环境意识会影响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决策者,以此为贯彻和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措施创造有利条件。
那么,对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分别应该如何测量?影响环境意识的社会因素有哪些?环境意识究竟是否会影响环境行为,或者说它在什么情况会影响环境行为?这些都是国内外环境意识研究的主要问题。本文的目的一是要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上述问题的研究现状,二是在此基础上找出研究缺陷,提出建议,并指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为此,文章对研究现状的整理将主要集中在环境意识的内涵及其测量(第一部分)、环境意识的影响因素(第二部分)和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关联(第三部分)等三个部分,文章的最后部分(第四部分)将着重分析环境意识现有研究存在的主要困境,并就如何克服这些困境进行初步探讨。
一、环境意识的内涵及测量维度
“环境意识”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中文的“环境意识”是对英文“Environmental Awareness”一词的翻译(徐嵩龄1997: 46)。但在英语世界里,人们讨论环境意识时,更多的是使用“环境素养”(Environmental Literacy)(参见王民1999: 1)、“新环境范式”(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简称NEP)(Dunlap/van Liere 1978)和尤其是“环境关心”(Environmental Concern)(R. Weigel/J. Weigel 1978)等词汇。这些词汇尽管在意义上彼此有些区别,但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即都是反映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看法。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学者们尽管从不同的角度对环境意识进行了研究和界定(参见王民1999: 12-14),但迄今为止,人们对环境意识的内涵并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也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但尽管如此,经过仔细分析后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在关于环境意识的内涵这个问题上,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意识应该包括环境知识、环境价值观、环境保护态度和环境保护行为等四个环节。这个观点的最典型的代表大约是洪大用先生的有关论述。他甚至认为,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一种“环环相扣,级级增值”的关系(洪大用1998:14)。这种观点的主要特征,是将环境行为视作环境意识的维度之一。依照这一特征,国内大多数学者都可以归入此类(例如杨朝飞1994,王民1999,吴祖强1997,吴上进等2004)。在欧美,早期的研究一般也将环境行为视作环境意识的组成要素,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另外一种观点逐步占据上风,并基本上形成共识。这种观点认为,应该将环境行为作为一个独立于环境意识的变量来看待,这是因为:环境意识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探讨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变为人们具体的环境行动,假如我们将从概念上将环境行为视作环境意识的组成部分之一,那就相当于我们事先已经预设了环境意识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力,这样就正好回避了我们自己的研究问题——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相关关系(Diekmann/Preisendrfer 2001: 101)。
与学术界对环境意识的定义及其操作化仍然存在广泛分歧相反,学者们比较共同的看法是,不断提出新的、却无法获取广泛认可的定义方式已经没有多大意义。随着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的不断深入,环境意识的各个组成部分被一步步地分离和“肢解”。这种将环境意识分解为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方式,一方面使得人们越来越注意研究哪些部分才真正是环境意识的核心因素,而哪些则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同上);另一方面,这种研究趋势也使人们越来越重视发展出测量环境意识的有效工具。
综观西方学者提出的测量环境意识的众多指标体系,影响最大的其实只有三个:Maloney/Ward(1973)的“生态态度和知识”(Ecological Attitudes and Knowledge)量表、Dunlap等人的新环境范式量表(Catton/Dunlap 1978)和德国学者Urban(1986)、Schahn(Schahn u.a. 1999)和Diekmann/Preisendrfer(1991)等人提出的环境意识量表。
Maloney/Ward量表源自心理学的态度研究,是迄今为止在美国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测量环境意识的量表。Maloney/Ward(1973)认为环境意识是人们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一种态度,而态度又包含情感、认知和冲动等三个部分。Maloney/Ward量表它最初包含130个项目,可以细分为四个分量表:情感分量表(34项)、知识分量表(24项)、行为意愿(verbal commitment)分量表(36项)和行为(actual commitment)分量表(36项)。其中,情感分量表要测量的是态度的情感部分,即在环境遭受破坏时,一个人从情感上受到影响的程度(害怕、愤怒、忧虑、无助等)。情感分量表可以说反映了英文Environmental Concern所表达的环境关心的核心内容。知识分量表的目的是反映态度的认知部分,它主要要调查的不是人们对于生态破坏的一般认识程度,而是人们对于环境保护领域里具体事实和关联的知晓程度。行为意愿分量表反映的是态度的冲动因素,它既指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环境行为,又包括个人对环保公共事务的参与,还包括个人要求采取政治措施的行为。最后的行为分量表包含被调查者对自身行为的自我陈述,它严格说来不是环境意识的真正组成部分。Maloney/Ward将行为分量表主要用来对问卷进行效度检验。在后来的研究中,Maloney等人(Maloney et al. 1975)将量表简化成了结构相同的45个项目。总的说来,Maloney/Ward量表的特点是从多个层面测量多个环境话题,角度非常全面,但也正因如此,它也显得过于复杂。此外,有学者认为该量表只注重了表面效度和内容效度,而没有深入检验建构效度(Dunlap/Jones 2002)。但尽管如此,该量表、尤其是经过简化后的量表,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在美欧许多学者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了使用。
Maloney/Ward量表相比,Dunlap和Catton等人提出的新环境范式量表(NEP量表)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二位学者是美国环境社会学的主要创始人。他们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末,不管是在现实里还是在社会学的学术研究中,国际社会都存在着一种与西方工业国家主流的社会范式相区别的新型的生态范式。他们称之为“新环境范式”(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简称NEP),以区别于传统的“人类例外范式”(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简称HEP)(Catton/Dunlap 1978; Dunlap/Catton 1979)。1978年,Dunlap和van Liere(Dunlap/van Liere 1978)设计了一个包含12个项目的“新环境范式”量表,以便检验民众对这一“新的世界观”的接受程度。他们通过经验调查对量表进行了严格的效度和信度审查,并证实了民众中确实存在着“新环境范式”的思潮。除此之外,该研究也对这12个项目的建构效度进行了检验,得出了量表只存在一个整体综合性因子的结论(参见王民1999:121)。随后展开的一些研究(Albrecht et al. 1982; Geller/Lasley 1985; Kuhn/Jackson 1989)则主要对该量表的单一维度性提出了质疑,都得出了“新环境范式”量表本身包含多个因子的结论(参见王民1999:121-125)。不过,对拓展“新环境范式”量表帮助最大仍是Dunlap和van Liere于198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Dunlap/van Liere 1984)。在该文中,他们设计出了一套量表,以便将“新环境范式”与“主流社会范式”(Dominant Social Paradigm,简称DSP)进行对比。该量表包括八个因子,总共37个项目。在随后的相关研究(Steger/Witt 1989; Sheppard 1995)中,人们一般倾向于将NEP项目与DSP项目整合起来,以便测量人们的生态价值。
德语国家的学者们在借鉴上述两大研究传统的基础之上,进行了颇具特色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的主要焦点是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来探讨“环境意识”(Umweltbewutsein)究竟应该包含哪几个组成部分。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Dieter Urban的相关研究工作。Urban(1986)反对将环境行为和环境知识纳入“环境意识”的范畴,而是认为环境意识应该包含三个彼此相对独立的维度:环境价值观、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的意愿。其中,环境价值观是指人们与环境及环境保护相关的价值观,它比环境态度更为抽象,是环境意识的价值基础。环境态度主要是指人们对于在环境遭受破坏时,情感受到震动的程度。环境行为的意愿则是指人们将环境价值观和环境态度转化为环境行为的愿意,它之所以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是因为如果存在着某些特殊的障碍的话,环境行为的愿意就会迅速降低。在这三个维度中,Urban认为环境态度是环境意识的核心部分。Urban虽然没能对这三个概念进行严格的操作化定义,但他的这种三分法在德语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例如,Diekmann/Preisendrfer就设计了一套环境意识量表,并以此在德国和瑞士展开了多次环境意识的问卷调查。他们也赞成将环境态度视作环境意识最核心的部分,并将环境态度区分为情感、认知和冲动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又包含三个叙述(Diekmann/Preisendrfer 2001: 103f.)。
从上述回顾我们可以看出,环境意识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由于选择的维度以及对每个维度的操作化定义各不相同,学者们设计出的环境意识量表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尽管如此,从在美欧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三个量表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如下几点基本共识,这些共识有助于我们确定测量环境意识的基本角度(Preisendrfer/Franzen 1996: 225f.)。
首先,环境态度、特别是环境态度中的情感因素和认知因素应该成为环境意识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它们是环境意识的“最小模块”(同上:225)。而在情感因素和认知因素当中,前者可以说更为重要。其中,情感因素是指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情感牵挂程度,而认知因素是指对环境破坏的认识状况,主要目的是要了解被调查者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能够环境问题视做和认可为一个问题。这种认识无需丰富的知识背景,因而也无须针对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进行全面的知识检验。
其次,根据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不同,可以将环境价值观和/或环境行为的意愿作为环境意识的第二模块。与环境态度中的情感因素和认知因素相比,环境价值观更为抽象,而环境行为的意愿则较为具体。其中,环境价值观一般包含如下三个方面:对科技的信任,增长的极限,以及人类中心主义。而对环境行为的意愿主要也可以从下述三个角度来界定:日常生活中环境行为的意愿,环保领域中公众参与的意愿,以及支持和服从环保措施的意愿。
最后,也可以将环境知识和(真实的)环境行为作为构成环境意识的第三模块。其中,环境知识既包括环境事实方面的知识,也包括环境关联方面的知识,还包括对个人及大众行动可能性的知识。但是,许多实证研究(Maloney/Ward 1973; Maloney et al. 1975; Schahn/Holzer 1990; Diekmann/Preisendrfer 1991)表明,环境事实方面的知识和环境关联方面的知识是相对独立的,与环境行为关系不大。此外,环境行为虽然不是环境意识的组成部分,但从有利于对问卷进行效度检验的目的出发,在调查环境意识时也调查人们实际的环境行为,也常常是十分必要的。

二、环境行为的内涵及测量维度
环境行为是环境保护行为的简称,指的是个人或团体发生的对自然环境有影响或者参与环境保护的行为,亦称“环境友好行为”、“环境负责行为”或者“环境适宜行为”等。与“环境意识”相比,对“环境行为”的界定和测量难度更大,争议也更多。这主要是因为在界定和测量环境行为时,人们原则上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要确定哪些领域的行为与环境相关,第二步还要确定每一领域的行为中,哪种行为方式才是符合环保要求的方式(Diekmann/Preisendrfer 2001: 105)。而在这两个方面,选择的空间都非常巨大。
武春友/孙岩(2006:62)通过分析后认为,西方学者对于环境行为的测量指标,其实可以分成“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和“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两大类。在国外关于环境行为的经验研究中,德国学者Schahn设计的指标体系比较具有代表性。他选择以下七个领域来测量环境行为:垃圾分类与回收;购物与消费;家庭节能;汽车与交通;节水与净水;运动与休闲和环保公众参与(Schahn et al. 1999)。在这七个领域中,前面六个领域基本上属于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而环保公众参与可以视做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综合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上述行为领域中的最前面的四个领域可以被视作测量环境行为的“最小目录”(Diekmann/Preisendrfer 2001: 106)。
与环境意识相比,我国学者在环境行为的界定和测量指标方面的研究更显不足。不少学者或者团体在进行相关研究时,使用的词汇通常是“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或者“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活动”等词汇,而不是“环境行为”或者“环境保护行为”。例如,具有比较浓厚的官方色彩的《中国环境保护行政二十年》编委会(1994:308)建议,我国应从如下几个方面支持、鼓励和引导“公众参与”:积极参加净化、绿化、美化环境工作;在本职工作中为环境保护尽职尽责;参与对污染环境的行为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的监督;参与对环境执行部门的监督;参与环境文化建设。任莉颖(2002:94)认为,这几方面的“公众参与行为”可以划分为从易到难的三个层面:公众对环境宣传教育的参与;公众自身的环境友好行为;公众发挥民主监督作用,监督环境污染行为和环境执法。
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在1998年进行的“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中,设计了一组关于“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活动”的问题(参见同上:110)。在这个基础上,任莉颖(同上:95)将环保领域里的公众参与行为总结为从易到难的四个变量:
——与他人谈论环境保护问题;
——参与环境宣传,增进环境了解,充实环保知识;
——参加有关环境保护的公益劳动或活动;
——为解决日常环境问题进行投诉、上访。
综上所述,在国外学者看来,“环境行为”既包括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环保行为,也包括个人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行为。其中,前者更为重要。而国内学者的注意力基本上只局限在个人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行为上面,而没有关注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环保行为。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本人认为,从个人的日常环保行为和个人的环保公众参与行为两个角度对“环境行为”进行界定,是比较妥当的。其中,对个人的日常环保行为的测量可以借鉴西方学者的观点,主要包括垃圾分类与回收、购物与消费、家庭节能、汽车与交通、节水与净水、运动与休闲等六个方面,而对环保公众参与则可以借鉴国内学者的意见,主要包括谈论环保问题、参与环境宣传、参加环保公益活动和进行环境投诉与上访等四个方面。
注释:
1、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多地使用“环境保护意识”(环保意识)和“环境保护行为”(环保行为)等术语,但学术界则惯于使用“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等概念,并将它们作为连续变量看待,一般不将它们与“逆(反)环境意识”和“环境破坏行为”分开(但也有少数学者明确区分了“逆环境意识”,参见王民1999:64-67)。
2、1992年,Dunlap和Mertig在一项名为“星球的健康”(Health of the Planet;简称HOP)的调查项目中,对全球24个国家的民众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发现,民众对环境质量的忧虑程度与所在国家的富裕程度更多地是呈反比,而不是呈正比。作者认为这从经验上否认了Inglehart的后物质主义的论点,并断言存在着“世界范围的环境意识”(Dunlap/Mertig 1996)。
3、根据王民的统计,国内公开发表的书刊上有关环境意识的定义就多达三十余个(王民1999:3)。邓拉普/琼斯更指出,国外关于环境关心的操作性定义大概有数百种(Dunlap/Jones 2002)。
4、从这个角度讲,将Environmental Concern翻译成“环境忧虑”也许更为贴切。
5、Dunlap和Jones(2002)将(单个/多个)环境话题和(单层面/多层面)关心两个角度进行交叉,得出了四种主要的测量“环境关心”的类型(参见洪大用2006)。
6、这12个项目分别是:1)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是很脆弱的,很容易被打乱; 2)人类对大自然的干扰常常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3)为了生存,人类必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4)人类已经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环境;5)目前的人口总量正在接近地球能够承受的极限;6)地球就象宇宙飞船,只有很有限的空间和资源;7)工业社会的增长是有极限的;8)为了维持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控制工业增长的速度;9)人是最重要的,可以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改变自然环境;10)人类生来就是主人,有权去统治自然界;11)动植物的存在是为了供人类使用;12)人类不用去适应大自然,因为我们有能力改变自然环境,使它们适合我们的生存(参见王民1999:121)。
7、2000年,Dunlap等人(Dunlap et al. 2000)又将该量表拓展为15个项目,修改后的量表也成为我国学者洪大用最近相关研究(洪大用2005,2006)的基础。
8、例如,Albrecht等人和Geller/Lasley都提取了三个因子:自然界的平衡,增长的极限,人类控制自然,而Kuhn/Jackson的研究结果则包括如下四个因子:科技与增长的负面结果,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生活质量,生态圈的限制(参见王民1999:122-124)。
9、这些因子的名称分别是:1)相信科技,2)支持经济增长,3)相信物质富裕,4)相信未来会成功,5)支持个人权利,6)支持私有财产权,7)支持维持现状,8)支持放任主义政府(Preisendrfer/Franzen 1996: 224)。
10、这三个部分、9个叙述具体是:情感部分:1)如果想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生活在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我就会感到不安;2)如果我们的行为一如既往,就会导致环境灾难;3)当我看到报纸上或电视上关于环境破坏事件的报道时,我常常感到很生气。认知部分:4)经济增长是有极限的,而且我们已经或者即将达到这一极限;5)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人的日常行为仍然不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6)在我看来,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被人为地夸大了。冲动部分:7)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仍然太少;8)为了保护环境,我们大家都应该限制自己对生活水平的追求;9)即使会降低本地的就业水平,我们也应该贯彻环境保护措施(Diekmann/Preisendrfer 2001: 103f.)。
11、事实上,西方学者所说的“公众参与”,一般是指公众通过各种方式对决策过程的参与,而不是泛指一切发生在某一领域里的个人行为。
12、当然,这六个日常生活领域非常具有西方社会的特点,不一定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因此,有必要研究并确定更符合中国国情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日常生活领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