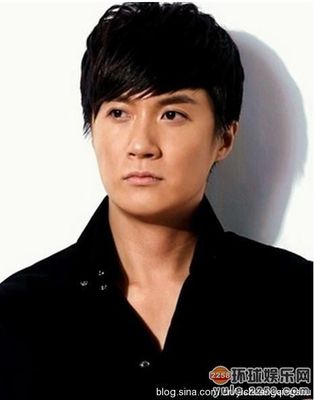正如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所阐明的,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危机,并非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是“一种文明的没落”。而与此相伴生并绵延至今的,是中国人的“文明的焦虑”,或者进一步说是“文明的不自信”。由此也开启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大门。今日之中国的各种“哈”症候群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百年而下,“哈日”,“哈美”,“哈俄”,直至今日令人啼笑皆非的“哈德”。 从根本上来说,“哈什么”却不是由对象“是什么”决定的,而是由学习者“需什么”所决定的。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的学习历程,不是由学习对象的价值和逻辑所决定的,而是由中国自身的境遇和需求所决定的。用孔飞力的术语来说是由学习者自身的“根本性议程”决定的。那么,什么是“根本性议程”呢?比如说,一个人饿了三天,“吃饭问题”就是“根本性议程”,而晚清以来被西方列强拖进“弱肉强食”的全球化丛林的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就是根本性议程。 而这个“根本性议程”的内容,也绝非是一次性而是逐渐地呈现出来的。从魏源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体现了这个内容的逐步延展与具体化。总起来说,中国向西方学习一开始并不是“全方位的”,而是“发现缺什么,就补什么”。以此为主轴,我们或可洞悉在“西学东渐”中渐次形成的“以欧为师”、“以日为师”、“以美为师”以及“以俄为师”等景观的内在机理。 既然清王朝的危机首先是从军事上开始的,那么,首先向西方学习军事也是自然的。中国最早“师夷之长技”实际上是铸炮术。1876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派卞长胜等七人,前往德国学习军事技术和兵法,是为赴欧留学之始。 1894年,甲午海战后,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昔日步趋中国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模仿西洋而一跃成为强国,必有可资镜鉴之处,一时间,举国上下掀起了赴日留学的高潮。官费之外,自费尤多,而所学者,“皆日本人自西洋贩来之西学”。留美潮的兴起则缘自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1911年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设立,至1924年官费留美学生已达689人,私费人亦随之大增,“回国后在社会上势力颇大”。 然而,到20世纪10年代末,中国开始掀起“哈俄”浪潮,从孙中山“联俄、联共”到共产党壮大并夺取政权,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最终在“以俄为师”的指导下得以建立。 如果我们认同法国组织社会学学者米歇尔·克罗齐在《行动者与系统:集体行动的政治学》一书中所指出的,“所有重大变革,比如西方的工业革命、阿拉伯世界8-9世纪的奇迹、15-16世纪的西班牙、16-17世纪的瑞典等等,实际起作用的是组织性的集体能力的建立”,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中国在“根本性议程”的政治叙事中,为什么会最终走上了“以俄为师”的道路。 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军事上的四分五裂,在这种背景下,要造成国家统一,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不具备军事能力的欧美式政党是无能为力的,惟有建立自己军队的俄式政党才是不二之选,所以孙中山转向“以俄为师”建立自己的军队体系,后起的中国共产党亦是如此。要依靠俄式政党的组织技术和军事力量,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起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非“中央集权”无可为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