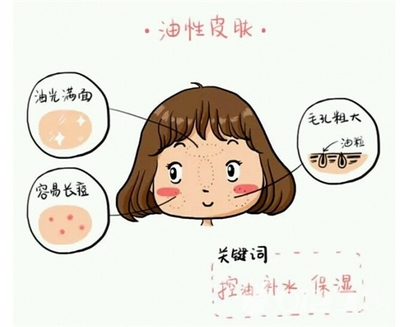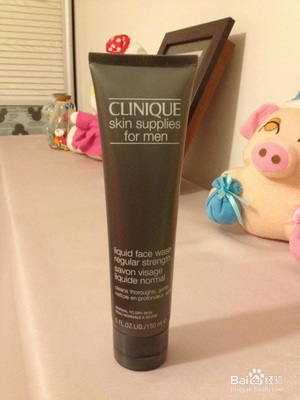藏戏和内地的京剧及傩戏一样,都有传统戏剧兼具的夸张而鲜艳的面具和脸谱。但藏戏与其他几种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他的传统戏剧都与如今的现实生活差异巨大,但藏戏却有一点跟如今的藏族人仍然特别相似,那就是性格和情绪都“写”在脸上的率真。

戏剧舞台总是要有更多更夸张的肢体语言,很多剧种都要给演员脸上涂上醒目的色彩或者直接戴上比头顶着大大的名字更显眼的符号和标签化的面具,只有这样,才能被音响效果不佳,场面又很大的剧场或者露天的观众一眼看出舞台上的人是谁,他在做什么。 回溯到古希腊,那时候的喜剧演员都戴着微笑的面具,悲剧演员都带着撇嘴悲伤的面具。后来的罗马人发明了“亚提拉闹剧”,专门讽刺四种人:愚蠢的丑角马克,既贪吃又多话的布孔,又吝啬又好色的老人帕普,不学无术的驼背骗子道森。这四种人用四个不同的面具做区分,人们一看面具就知道这个人物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后人意大利人在两千多年后发展出了类似的即兴喜剧,展演至今。 从这个角度来说,藏戏、京剧以及傩戏这样的戏剧之所以有夸张的面部色彩,道理应该跟那些外国古老的戏剧形式是一样的。有趣的是,就连藏戏面具和京剧脸谱本身,由于基于不同的文化色彩理解,同样的颜色,代表的人物性格却差得相当远。 京剧里大白脸一出现,人们便知道那是一个像曹操一样奸诈多疑的狂徒;但藏戏里的白脸却是基于对白色的崇拜而象征的纯洁、善良、温和而无害的人物形象。京剧里的黄脸是典韦为代表的性格刚烈的战士,但藏戏里却是高僧大德甚至仙界渊博、功力深厚的高人。差得更远的是绿色和黑色,很多人都知道藏传佛教有绿度母,所以在藏戏面具里绿色面具都是代表女人,而且都是貌美端庄的贵妇形象,甚至神佛化身;可是京剧里的绿脸都是勇猛莽撞的好汉!京剧里的黑色脸谱以包公为代表,是一种公正而威严的表现,但在藏戏里黑色却是凶恶的忿怒相。藏戏里还有一种半白半黑的面具,正如颜色所标示的,这个矛盾的结合体成为口蜜腹剑挑拨离间的小人。 如今,表演的细腻和仿真已经登峰造极,却有戏剧理论家打着“陌生化”的旗号在呼吁回到面具表演,有电影已经在试着把曾经努力还原和逼真的场景故意处理成明显的舞台布景效果,有电视会调皮地用台词把观众从剧情沉浸的氛围中偶尔“穿越”打断。总有一些人在纷繁复杂的现实残忍中开始怀念童年时候对戏剧的简单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此时的面具和脸谱,已经不仅仅是努力体恤远处的观众自报家门的浓重“名片”,更是后现代活在复杂如戏剧的你我回到前现代童年的“门票”:善、恶、智、愚,都明明白白“写”在脸上。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