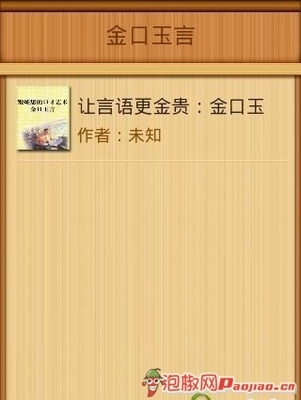金庸谈香港回归10周年
记者:那您觉得回归以来有没有什么变化?
金庸:正因为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之下,我觉得回归之后并没有什么变化,1997年6月30日我睡好觉,7月1日起床,发现香港什么都没有变化,当时很多香港人都不相信。
到现在为止,香港继续沿用之前的“普通法”,和“大陆法系”的《基本法》并行,这样使香港的社会环境和英国、美国都比较接近。当初让我们去起草《基本法》的时候,说到立法的原则,我们都说,让香港人“宁可怕老婆不要怕政府”。因为在法治社会里,老婆不讲法,政府是讲法的。(笑)
记者:那回归以后,香港人是不是可以继续“怕老婆不怕政府”?
金庸:还是啊,政府如果侵犯人民权益,人民可以和政府打官司,政府会输掉,要赔钱。
记者:之前我们也听说,回归以后,香港市民的参政意识更高了。
金庸:英国统治的时候完全没有民主,市民想参政都不行。立法局议员都是港督任命的,谈不上参政的问题。回归之后,立法局由民选,有些人有兴趣就去参选,参政的兴趣比以前要多一些。
记者:香港人对国家的认可程度有没有在增加?
金庸:在内心深处,香港人对一些事件可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对国家的认可程度确实在增加,尤其是我们的爱国心,应该是一直没变的。
金庸其人
金庸应该是最会赚钱的文人侠客了!他已经年迈,但你丝毫看不出这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冬日下午的阳光,带些慵懒地照在位于香港北角的这间偌大的办公室里。窗外,维多利亚湾湛蓝的海水一如数十年前,一个叫查良镛的年轻人初来香港的日子。
那时候他25岁。身无分文。后来他改名金庸,成了著名报人,成了一代武侠小说的宗师,成了“千古以来以文致富的第一人”。

他见证过香港文化从起步到繁盛的各个阶段并参与其中,培育和积蓄了大量人才。他是一个报人,也是著名影评人,甚至还是导演,到最后,还提出了香港回归后基本法起草的“主流方案”,确立了目前香港政体的基本框架。
他总是在创造新闻和被新闻追逐。与内地高官过往甚密,屡次受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去年的浙大博导资格事件,刚刚平息,他又宣布以八十高龄,去剑桥大学读历史,做一个老学生;在全世界疯狂改编他的著作搬上电视荧屏的时候,他也不甘寂寞,一直在修改自己笔下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人物形象的命运。
他命运多舛,婚姻坎坷。先后有三次婚姻,几个孩子,似乎都在他光辉的阴影下生活。他也曾失去过一个成年的孩子,至今,仍然没有人敢问他这个问题。他不甘寂寞的晚年生活,缺少了儿女陪伴,在香港、澳洲和英国剑桥,几近寂寞地度过。
他的作品已经印刷过上亿册,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必有金庸流传。
但我丝毫不能把想象中那个有无数传奇的近乎英雄的人物和面前这个老人联系起来。他应该不像乔峰也像郭靖,至少该像段誉。当他从办公室的一角走过来欢迎我们的时候,我显然是失望着并好奇着,这个笑起来像孩子一样的老人,说话平淡,简单,究竟有什么样的能量能够影响到这世界上近乎一半的华人?
像传说中那样,他是一个温和而细致的人,仪容整洁,带着金丝边眼镜,风度和蔼。拍照时,他微微有些羞涩和紧张。手里拿着一张从杂志上取下来的塑料封套,卷成细长的棍,不停的玩弄。我的镜头一直在躲避那闪烁的光点,看到他略带腼腆的笑容和不知所措的举止,在这数百平米环绕书架和海景的大办公室内,格外显得孤单。
他的门口,那幅对联依旧: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他的背后,满满三个通壁书架里,摆满了各式版本的他的书。他似乎不能对应到其中任何一个人物,但这些人物无一不是出自他的笔下——金庸,到底是一个侠客,还是他自己所称的庸人?
我对唐代有新的见解
记者:您在剑桥的生活如何,现在主要是在攻读学位吗?
金庸:在剑桥,每天读书4到5个钟头。现在不用工作了,读书是很大的享受。以前办报很辛苦,每天要写一篇社评,写一篇小说,要看新闻,还要给记者布置任务,教记者如何去采访,怎么做新闻。
现在我在剑桥念历史。一星期念两次,我去学校一次,老师来我家一次,一次2个钟头。外国大学跟中国不大一样,单独一个人教学。每次五六个硕士和博士一起读,老师找了很复杂的古书来读。除了读书外,我在牛津大学还有一个工作,那里有一个汉学研究所,我是高级研究员。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进的剑桥,是通过考试进去的吗?
金庸:不是。2004年,他们给我一个荣誉文学博士。我没有大学和硕士学位,进入牛津、剑桥很难,即便英国人也很不容易进去。我大学没有毕业,曾经在上海念书,但没有拿到学位就离开了。当时上海快解放了,一打仗什么毕业考试都没有了。我没有大学文凭和硕士学位,他们要我重新念硕士学位,再念博士学位。
者:您读的博士具体研究什么?金庸:是关于唐朝的,但现在我不能宣布,内容也不能讲。一讲出去,别人拿去发表了,我就糟糕了;学位也拿不到,念书也评不上去了。
记者:以前您的小说中较多涉及宋、明、清的历史,现在做研究为什么选择唐朝?
金庸:因为我有新的见解,别人没有写过,我可以写。我写宋朝和大理,看了很多书,也容易写,但有人说那个课题别人研究过了,就不能写。研究宋朝的人,没有新的见解就不能写。
他有一种健康的游戏心态,并没有自我作古
◎鄢烈山(评论家)
作为一个“新武侠小说”的局外人,我觉得他改编不改编都无所谓。我很少读他的小说,以前偶尔翻了下,没有读完过。我觉得,作为一个有名声有地位、智商颇高的人,他三次改编自己的小说,不仅是他的权利,也必有他要改的理由:或者想改得更贴近时代潮流,比如让韦小宝的老婆少一些,乃至让他厌倦了俗世的追逐而出家;也可能是出于对读书市场的考虑;更可能是为了让自己的东西更“经典”。
我觉得他怎么改都有利于他健脑健身呀,表明他有一种健康的游戏心态,并没有自我作古,把自己的东西看成不能易一字的圣经。倒是那些“金迷”把金庸小说比金庸本人还看得神圣!好笑。我相信他没有老糊涂,倒是很理性,比如80多岁了还要去英国剑桥读书,都是有自信的理性的表现。
他还是想当一个历史学家
◎董健(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去年“浙大事件”,我们这些学者批评他,主要是指他不想当武侠小说家或文学学科博导,而硬要当历史学博士生导师,这是“错位”。谁也没有说他是一位不好的武侠小说家,也没有批评他的小说哪些地方有违历史事实。
我觉得他现在改写自己的小说,想使其中一些情节尽量符合历史事实,可能是他想当历史学家心情的表现。前年我见到他时,他不希望别人称呼他为一个小说家,而是要别人称他为历史学者,他强调自己学者的身份。他80多岁跑到英国去拿历史学博士,也很好玩,这些可能都是他的心态反映。在浙江大学,他当历史学博士生导师,遭到学者的非议,历史系事实上也不接受他,这些可能对他都有影响。还有,他自己说要写第一本白话中国通史,其实范文澜、郭沫若早就写过了。他要写出新意也不容易,这与写小说的路子是不同的。
他的武侠小说其中的细节无论怎么改也无关大局。影响已经客观存在,学术界对他的小说已有定评,无论怎么改,也改变不了已经形成的影响。
我主张不必改,一些破绽可以修补
◎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金学专家)
谈到一些情节的补充,如黄药师爱上梅超风,其实在以前的小说中就有一些铺垫了,只是没有充分展开。至于袁承志继承父亲的大业,也是他对人物的理解在变化,身上“武”的东西少了,“侠”更多一些了。我也听到一些朋友讲述他的《鹿鼎记》结局,韦小宝最后被7个太太都抛弃了。我主张不必改,一些破绽可以修补。比如人物年龄有些错误啊,他人是认真了一点。
韦小宝是他14部小说中最深刻的人物
◎万润龙(《金庸茶馆》主编)
金庸先生改编小说,可能是他3次修订小说中最强劲的。1998年,新闻出版署就有统计,全球有3亿金庸迷。金先生每天都收到很多金庸迷的信。很多读者来信指出哪些不好,哪些地方有错。一些读者甚至要求他不允许他再修改以前的作品。前年,查先生来杭州请《金庸茶馆》的编辑吃饭,我们一个年轻编辑指出新修版《碧血剑》大概有100到200处和原来不同,他和查先生进行理论,查先生听了很开心。
查先生自己很重视读者意见,在改编过程中,也很难以割舍。他事前还专门请教过很多专家,如严家炎、孔庆东、陈墨等等。在改编中,他自己认知也有很大变化。我曾经跟他讨论过,他自己也说过,韦小宝是他14部小说中最深刻的人物、《鹿鼎记》是他小说中最出色的。在我看来,韦小宝是一个可以跟鲁迅的阿 Q媲美的人物,他具有中国国民的双重性,是他所有小说中唯一具有社会意义、历史意义的人物。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