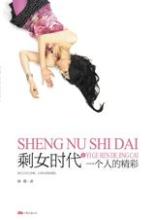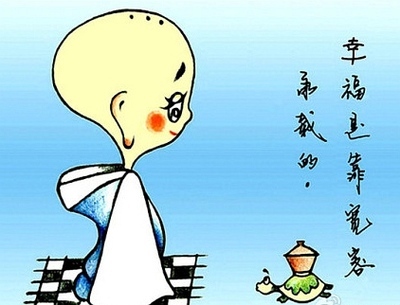2011年,田耳花四百多块钱买了一副天文望远镜,架在自家三层楼的房顶,调了几晚上。找不到星星,只能看最亮的几颗,镜头外是凤凰这座南方小城清冽湿冷的夜雾。2013年秋天,田耳在《收获》杂志发表长篇小说《天体悬浮》,小说里也有一个喜欢在山顶夜观星空、把爱情跟星空联系起来的主人公符启明。 田耳从1999年开始写小说,曾获第十八届、第二十届“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此后,又陆续出版过长篇小说《风蚀地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和《夏天糖》(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版)。一些文学评论家开始注意到田耳,李敬泽称其小说中“有一种复杂、含混的态度”,有一种“隐蔽的个性”。 田耳今年37岁,但“青春”仍是他在采访中提到的高频词。如同他小说中那些为生活琐屑营役、敏感得不合时宜的主人公们一样,田耳所描述的青春或者说他自己拥有过的青春,深深渗入在一地鸡毛似的生活里。 读王朔,看守鸡场 就像无法想象腼腆到有些木纳的沈从文,如何站在北门码头淡定地给悬在城楼上的人头数数那样,南方边陲小城凤凰正是以这种近乎蛮荒崇拜的滋养,使田耳完成了边城少年的“野蛮生长”。跟贾樟柯《小武》里所呈现出的县城景象一样,南方小城的天多是灰扑扑的,偏远闭塞,生活乏善可呈。放学后,田耳总喜欢绕到城郊寻找各式奇形怪状的石头,找到就去问自然老师是不是化石,“他老说不是,我就问他到底懂不懂。小学时很讨班主任喜欢,后面就爱惹事,一直跟班主任处不好关系。” 池塘柳树,桑榆雏鸭,少年如飞蓬般成长。在田耳的小学毕业纪念册上,同学们纷纷留言祝他做生意发大财,一个同学甚至写下了“你不要把心思放在赚钱上,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学习”这样语重心长的话。他们断然想不到,这个一心贩卖邮票赚同学零用钱的家伙,日后会成为一个作家。 1996年,复读一年的田耳,高考英语考了35分,只能读最末一批招生的湘西电大,念汉语言文学专业。现实如帛,青春草莽,荷尔蒙总趁着黑夜吹响号角,恣肆无疆。课时松散,他也懒得上,窝在校外租住的农民房,没日没夜地看小说。翻到王朔的《动物凶猛》,吓了一跳,相对于小说中马小军的勇敢和张扬,想起高中暗恋的姑娘,田耳觉得“自己的青春简直白活了”。像遭受了一场洗礼,那年整个夏天,田耳都沉浸在王朔小说的情绪中,每天看一遍,陷入一种忧郁却暗带兴奋的心境里,“相当美好”,“想写点什么”。 1999年电大毕业后,田耳帮亲戚看守一个养鸡场,这是他干过的最喜欢的一份工作。他每天给鸡喂食,清理鸡舍。因为过分清闲,田耳开始写小说。 留在凤凰,享受观察乐趣 田耳的小说,底层气息浓郁:派出所里没有编制的协警、理发店的老板娘,个个都像是拎着小卖铺打来的酒壶、随时准备盘腿在树墩下开个牌局似的。田耳的写作跟生活没有嫌隙。继看守鸡场的工作后,他又卖过四年空调。旺季忙着走货,淡季上门收账。账不好收,也没别的辙,就去对方店里静坐,脑子里构思自己的小说。一坐就是整天,靠这笨办法多少收回一些欠款,小说也接二连三地写了出来。 田耳的写作是田野调查式的,毫无虚晃招式,是生活现场的第一证人。《天体悬浮》写派出所与地方三教九流共舞的小江湖,只不过这个江湖,相较于田耳在派出所待过的还是温和许多,“在基层派出所可以看见地狱景象。粉哥粉妹、快到天命之年还去隆胸的妓女、三块钱盒饭都舍不得吃也要博一把的赌棍……在我们之外,总有些人这么活着。” 常年生活在凤凰,田耳没有想过“逃离”。相反,去上海作家研究生班就读的经历让他觉得有些水土不服:“江浙那边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太有秩序了。”“我也长期考虑过要不要离开,但后来觉得这不是问题的根本,重要的是一个人需要什么。”田耳说。 如今,凤凰是广告中那个“为了你这个城已等了千年”的天下凤凰,虹桥桥头的那家粉馆也打出了网友推荐的招牌,田耳仍旧住在沱江一侧坡头上自家修的房子里,在乎的还是那些东西:买书,看书,写作,反复听高中时就热爱的达明一派的歌,观察生活琐屑的迷人之处。“我喜欢观察,这让我在哪里都不会枯燥”。

表达灵魂渴欲,哪怕肉身相距遥远 爱写警察,因为爱看推理小说 时代周报:从构思到写作完成,《天体悬浮》用了多少时间? 田耳:2005年,我到一个派出所待了两个月,和辅警接触较多,那时候就想写个有关辅警的东西,最初想写成中篇,名字叫《左道封闭》。辅警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转个正式编制,但对于底层,“名正言顺”往往是一件需要付出巨大心力才能达到的事情。在一个单位上班,你的职位最低,甚至像二奶一样无名无分,才能感受到这种给自己“正名”的渴望。但这个想法纠缠了我,如果丁一腾(《天体悬浮》主人公之一)和符启明就为一个编制闹得风生水起,格局太小,人的命运感也难以在如此狭侷的空间内展开。某天突然想到,这两个人都可以将编制扔开,都可以离开派出所,展开一段新的人生……这一刹,我意识到这应该是个长篇,但一直写不出来。 我一直写不好长篇,死在电脑里的长篇开头有十几个,找不出原因。后来偶然帮朋友干了几个月编剧的活,回家以后思路突然打开了,知道自己写不了长篇的症结所在:我把长篇混同于中短篇,要想好开头结尾才下笔,所以整个写作过程是封闭的,气息羸弱;长篇写作的过程,应该是开放的。于是我在开篇着力建立好两个人物的形象,然后顺着他们的品性习气慢慢地往下走,我将自己等同于他们,他们的明天就是我的明天……犹如编剧,今天编好这集,不管下一集的事。怎么走,全凭经验把握。如果进入状态,会有一种命运感牵引走向。这时我再将原先未写好的《左道封闭》写成长篇,很顺,从2011年9月写到2012年6月,初稿43万字,发表在《收获》上删至20万字。现在正在修改出版稿,估计得有30万字。 对于这个长篇,我现在也不去想满意或不满意,它自有命运,别人说会更准确。写完《天体悬浮》我最大的感悟是:我能写长篇小说。 时代周报:《天体悬浮》中的符启明和丁一腾这两个主人公,有些像一个人的两面。 田耳:没错,我经常感到符启明和丁一腾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都和我本人关系甚微。生活中我羡慕稳重、低调、平静、善良的人,我也想得来这样的沉稳,其实我善于给自己添乱,没事找事,经常让一些朋友感到头疼。丁一腾是我的一种理想状态,符启明身上有我想扔扔不掉的躁动。但写到后头,符启明失控了,他脱离了我,成为小说中的那个人。丁一腾这人,读者不难理解;而符启明,他心存理想,又熟谙各种现实法则,这样一个人在当下社会,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轨迹,会有怎样的心路历程?一位网友将符启明总结得非常到位:在不断自嘲与戏谑的文字下,透露出一个人最内在的灵魂渴欲,不管这肉身距离灵魂多远。 时代周报:《夏天糖》、《风蚀地带》、《一个人张灯结彩》,还有《天体悬浮》,都和警察有关,这跟你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吗? 田耳:没关系。我和警察的交道无非是去体验了一阵生活,时间也不长。我爱写警察,因为我是个推理控,喜欢读推理小说。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我从一本叫《知识》的杂志里看到一个短篇小说,叫《投影》。那是我看的第一个推理小说,作者松本清张,是说一帮人怎样设计、改变路上原有的灯光,诱惑一个醉鬼开摩托扎进海里。当时读到这样的故事,很震撼,试图给朋友们说,朋友们也耐心地听,但太复杂,讲得别人一头雾水。 写短篇更有快感 时代周报:刊登在《花城》杂志的短篇小说《割礼》是今年你的另一个作品,背景是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能否谈谈这个小说的创作?相较于长篇写作,你是否更青睐短篇? 田耳:这个小说是听来的一个故事。某工作队下乡强化计生工作,因信息不通,差点把一对夫妻同时扎了,幸好有人及时发觉。讲故事的是某县文化馆的创作员,钟情于写作,觉得这故事可以写,但他写不出来,就问我愿不愿意写。我对这故事有兴趣,对他作为一个老文青的经历也感兴趣,他写了大半辈子,老婆是他唯一的粉丝。我把两者融合起来,写出了《割礼》。写好拿给他看,他点了头我再拿出去发表。 短篇创作当然给人更多快感,时间周期短,在有限的篇幅内更易于发力。但长期写作,我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题材,都吸引我,有的确实只能用长篇表现。对我来说,篇幅是次要的问题,我只想写出好小说。 时代周报:在你的早期写作时,似乎有过一段较长的静默期。 田耳:当时也不知道是静默期。能不能成为作家、自己写得到底怎么样,说不清的,只能摸石头过河。一开始那几年,没人知道我在写,可能是我最舒服的日子,有一种说不出的安静,虽然不赚钱,但也不花钱,平时就宅在家里,有朋友打电话就去喝喝夜酒。当时我的同学都在恋爱,听听他们的故事,出出馊主意,日子很好过。现在想想,可能是年龄的问题,二十多岁,有钱没钱,都是一辈子最好的时光。 我的写作没有规律,一点规律也没有,任何时候可以开始,可能有感觉了一写半个月,接下来一停也是半个月。 没有母亲,不可能成为作家 时代周报:听说家人对你的写作很支持,尤其是你的母亲。 田耳:没有母亲,我可能不会成为作家—不是指她生我这事。我母亲是我遇见过的心理素质最好的一个人,她以前在县烟草公司,工作就是背着一个大包到全国各烟厂讨要卖原烟的款项,一去几个月。她的耐心使她成为单位里的追款能手。我电大毕业后,她不要我接她的班,说是怕我学坏。写作的事也是母亲力排众议,因为在小县城,一个人要坐在家里写小说直到变成作家,简直是异想天开,但母亲认为我干的不是坏事。她也相信(也就她相信),我能当上作家。亲戚们都劝我找事干,走上街也不乏熟人热嘲冷讽,如果年过三十发表小说还不顺遂,那我基本就是小城里的一个笑柄了。所以,母亲的支持对我相当重要。其实母亲的支持也不足以使我成为作家,我还得感谢意外地获了一次鲁迅文学奖,获奖让无聊的人闭嘴,让自己一直写到今天。 时代周报:听说你有一个多年的习惯,每年正月初三都会去沈从文先生墓前烧纸?沈从文对你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田耳:2000年春节我给沈老烧纸,因为那是年初三,朋友们都去给祖宗烧纸,我家在凤凰县城没有祖坟,闲着无聊,想着去给沈从文烧。结果次日也就是年初四,邮递员送来一份邮件,我半年前投出去的一篇短篇在《花溪》发表了。初次发表给人的鼓舞,现在发到哪里都不能比。我知道和沈老没关系,但宁愿当是托他的福。从此每年初三都去,坚持十来年了。要说创作,沈老对我影响不大。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者,大都是受王朔、余华那拨以及外国作家的影响。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