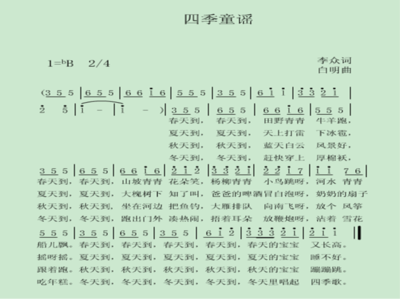1978~1983
摸着石头的变革
创业史定位: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的确立,给久被政治折腾的中国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个体经济开始疯狂地涌现,面对突变的格局和民间力量的暗涌,摸着石头的变革因此充满惊险又一波三折。
时代描述:
1978年到1983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转折年代。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宣告下,刚刚复出的老一辈领导人邓小平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推进中国的命运变革。
政策的鼓励,舆论的支持,社会环境的好转,商业形态开始在一种懵懂的姿态中萌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等利好消息的刺激下,久被压抑的创富愿望开始被催化,一些早起的先觉者主动或被动地走上了个体工商户的道路。他们踩着还有些生涩的创业节拍,迷茫地积攒着原始资本,虽然大多人都不知道这条路究竟会驶向何方。
所有的人都彷佛听到了时代火车转换轨道的尖利声响,这种激励在民间随后就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在浙江南部的温州、福建潮汕、广东珠三角一带,越来越多的乡土工厂展现出他们超乎寻常的活力。当“笼子外的野鸟”个体经济肆无忌惮地冲击了旧有僵化体制后,左右为难的高层而后又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地力保那些尚在旧体制下低效率运行的国企的利益。
不可逆转的是,计划经济的闸门开始被逐渐撬开,民间的创业力量如涌出地面的小涓流般四处漫游,与之而来的各地小商品市场、流通领域开始兴盛。致富的渴望开始萌芽,日渐成为全民共同的理想。
创业史记:
复苏的萌动
1978年,鲁冠球的工厂已经有了400号人,年产值300余万元,这一年的秋天,他在5个人的见证下,“高调”地又挂上了“宁围万向节厂”的厂牌。
之前的10年,鲁冠球一直在偷偷摸摸中办厂。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统统属于“非法”。工厂没有地方买原材料,他踩着一辆破自行车每天过江到杭州城里,走街串巷地收废旧钢材。生产也是有上顿没下顿,一开始做了一千把犁刀,跑去向农机公司推销,一进门就被赶了出来,因为他没有“经销指标”。他东钻西闯了几年,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来的缝,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厂提供配套生产,如饲料机上的榔头、打板,拖拉机上的尾轮叉,柴油机上的油嘴,要什么就做什么。
1978年的到来,这位只有初一文化、但嗅觉异常灵敏的农民嗅到了一丝有别于以往的清新空气,他觉得自己可以不再偷偷摸摸地干活了。
这年不只是企业家们“隐姓埋名”后浮出水面的开端,同样也有改革的模板,江阴市华西村(8.00,0.30,3.90%)的吴仁宝就被推到了前台。这位集中全村人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村支部书记因当年带领全村创造了296.35万元的产值,而成为举国学习的发展经济的榜样。
这年,恢复高考,那些充满抱负而又报国无门的青年们开始跨进大学的殿堂,这奠定了他们日后高起点创业的重要基础。

在辽宁,沈阳铁路局工人马蔚华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1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15.51,0.73,4.94%)总行行长;杭州出生的张征宇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后来他做出了第一代PDA掌上电脑“商务通”;北京176中学的青年老师段永基考上北京航空学院的研究生,后来他创办四通公司,成为中关村的风云人物。而在广州的华南工学院,在无线电班第一批学生中,年近40的陈伟荣和两个年龄均只有18岁的黄宏生、李东生成为了同学,这三个人,日后分别创办了康佳、创维和TCL.
黄鸣和顾雏军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前者考上中国石油(13.17,0.47,3.70%)大学,第一节课教授就告诉他:世界石油只够用50年,中国的时间更短。以后这位“中国太阳能产业教父”选择了新能源领域创业;18岁的顾雏军则考入江苏工学院动力工程系,老师对他的评价是:聪明好学,踏实上进。但20多年后他却以商业诈骗罪锒铛入狱。
一些没有机会和能力改变命运的青年则有些被动而愤懑地选择创业。因为父亲被打成右派且进了监狱,李如成和精神崩溃的母亲以及四个兄妹根本无法返回上海。他用返城补助款,开了一家乡镇企业:青春服装厂;1978年9月,为了推销低压电器,胡成中在长沙郊区85个村子的抽水站间连续跑了十几天。当时他还不到20岁,身份是农民。
官方助推力
复苏的萌动风起云涌,被压抑的创富愿望在政策的指引和诱导下,开始延伸向各个角落。
1979年4月,在广州,一个名叫容志仁的人领取了个体营业执照,他以100元本钱开饮食店做学生餐,如今早已为人们淡忘的容志仁确是当年的街边“创业第一人”;这年国庆节时,在顺德容桂镇,街道办副主任出身的梁庆德创办的“桂洲羽葵工艺厂”挂牌投产,产品是鸡毛掸子、羽毛扇、皮革制品。而后十数年后,完成了原始积累的梁庆德华丽转身,创办了格兰仕集团。
一些聪明的早起者都意识到,这个国家开始对他们敞开创富的大门。1979年初,周正毅拿出所有积蓄在杨浦区开了一家馄饨店。在混沌多于秩序的年代,精明的周正毅不甘偏于馄饨店这“钱途”黯淡的一隅。他浑水摸鱼,踏上了去往日本的飞机,美其名曰“留学”,实则暗渡陈仓,走私商品去日本销售,“带的货物很多,记不清楚,好像是101生发水”;这年,许荣茂来到香港。无钱无背景,他什么行业都做,只要不违法的钱就赚。
这一年的秋天,张果喜第二次来到上海。他舍不得住旅馆,蜷缩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的屋檐下过了一夜。第二天,他找到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软磨硬泡签下了20套雕花樟木箱的出口合同。
国家落实政策,对贵州的罗忠福无疑也是个天大的喜讯。他父辈、祖父辈遗留的几十万元财产连同罗家的“天府别墅”被一起归还,他回城后准备结婚。苦于在遵义买不到养眼的沙发,于是他参考国外电影上的沙发式样,开始试做。没想到一炮走红,订货者蜂拥而至,名声传遍川黔。之后,有想法的他在遵义搞了一个家具展销会,又出人意料地跑到电视台花钱打了一个广告,广告片中的模特儿由他妻子客串。一经播出,家具展销会获得巨大成功,他的第一个十万元就这样信手拈来。
在官方,中国的决策者们也尝试着在南方设立一个有别于过去任何经济形态的“经济特区”。首吃螃蟹的执行者,则是官拜司局级的干部、军人出身的袁庚。
袁庚的所有筹码只有三个,一个允许特区内华侨、港澳商人、某些外国厂商直接投资办厂的政策、国家拿出的3000万元贷款以及一大片杂草丛生、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的土地。
区区3000万元的贷款——这点钱几乎还不够搞2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无奈之下,开发者们唯有一计可施,那就是出租土地,用地金来换现金。这个在当时可谓“大逆不道”的想法得到了强烈的反对。顶着压力的蛇口开发区官员们不得不翻遍马列原著找根据,而后他们终于在厚厚的《列宁全集》中查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而后这段话深圳干部人人会背,有考察和质问者远道前来,他们就将之作为“尚方宝剑”。
通过出租土地收租的方式,深圳用收进的数亿元钱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从1980年至1985年的五年里,深圳累计完成基建投资76.3亿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9个工业区,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特区之风自此一路北上,开放之势再不可挡。
大风起兮
1980年,仿佛一夜之间,中国从事个体经济的人数突然猛增到86万人,比1979年翻了一倍多。
1981年,年广九决定雇佣几个人开始炒瓜子。
年广久是个文盲,7岁开始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他不知从哪里偷学了一门炒瓜子的手艺,他自小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
1981年,只会写5个字的年广久在澡堂里泡澡时,听到一群人唧唧喳喳的议论后,他敏感地觉得,党中央是要鼓励私营个体经济的发展了。这年7月,他在芜湖的十九道门摆起了一个卖瓜子的固定摊位。此前,瓜子一直是国家供销社统购统销的二类商品,他摆了一段时间,居然无人过问。
在经营中,这个浑身透着狡黠的商贩很是懂得迎合紧缺年代人们的消费心理,“别人买一斤瓜子,我还要抓一把送给他。”他的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买瓜子的队伍最长的时候排过100米。
年广久开始被作为个私经济的典型人物被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生意太好,年广久不得不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人一个个多起来,到秋天,一统计,傻子瓜子已经有了12个雇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虽然对个体经济的政策有了一定的松动,但在政治意识领域,长期习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层决策者们对个体经济依旧保持着观望的警惕。年广久的雇工居然有了12个,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过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于是,“年广久是不是资本家?”、“年广久是不是剥削分子”的流言开始流转全国各地,争论、辩护、讨伐,一场带有浓烈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
这场大辩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以至于邓小平不得不出来讲话了。他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一动就人心不安,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争论最终尘埃落定。
在民间,这场争议并未引起太大的注意。1980年,郑秀康终于向单位正式提出了辞职,创办红象皮鞋作坊。“我决定做消费品,要么做沙发要么制鞋,最终选择制鞋,是因为家里的住房太小,连个沙发都放不下。”如今,他的康奈集团已成为中国的“鞋王”之一。
这年,成绩出众的蒋锡培高考意外名落孙山。他跑去太湖边坐了一夜,而后决定跟随二哥去杭州学修钟表,他的目标是一辈子赚够5万元,“回家造两间房子,剩余的放在银行里面存定期”。
整肃与暗生
年广久因为邓公的“特殊眷顾”而幸运地“躲过一劫”。但1982年后,因为个体经济发展过于迅猛,主政者也开始对这个有些狂放的群体进行调整和治理。
因为个体从业者不按章法的出牌冲击了国有企业的利益,抢占着基础并不坚实的国企资源,一些挖人、挖技术等手段对国企构成了直接威胁,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犯了众怒”。1982年,国务院两次下发严厉文件,对那些严重破坏经济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整肃和清理。
在温州,柳市镇的8个工商户随后得到了判刑、拘禁等严重处理,并通告全国,轰动一时,史称温州“八大王事件”。到这一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个体经济遭受重创。已经出狱三年多的牟其中又被抓进了监狱,这次他犯的罪是“投机倒把罪”。因为他发现一种由上海工厂生产的“555”牌座钟在市场上很好销,他找到重庆一家半停产的军工企业,请他们以每个25元仿制1万个,然后他再以32元的价格卖给上海的一家贸易公司。
被“错杀”的小私营业主中还有个叫严介和的人。之前利用闲暇时间,中学语文教师的他边骑着自行车到周边窑厂联系销售业务,边组织同村的青年收购芦苇编织草帘子,一个月轻松能赚几十块。做大一些后,他又陆续组织一些人编草帘子,自己收购,再卖到窑厂。三四年间,他成了淮安有名的有钱人、万元户。在村民的举报下,严介和又变成了当地“资本主义”的典型,有关部门取缔了他的家庭作坊。
但持续两年的整肃并不能改变被激发的个体工商业者在巨大诱惑面前的蠢蠢欲动,一场民间自发的创业浪潮开始席卷各地。
1983年初,刚过春节,四川新津县农业局刚刚分配进来的大学生陈育新突然提出辞职,日后成为中国首富的刘氏四兄弟办起了平生第一个实业:育新良种场。
在1983年前后,中国的第一批“倒爷”出现在北京和深圳。曾为铁路工人的王石,倒起了玉米,一年下来,他净赚了300万元。与此同时,义乌的公路边自发地聚起了一个小商品的交易基地,日后这里诞生了全球最大的商品采购中心;在温州,一些农民开始制造小五金商品,并摆在自家门口叫卖,此为最早的“前店后厂”雏形。这一年最火的榜样是敢在厂里搞奖金制度、提出“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虽然这个脾气暴烈、小错不断的厂长后来被证明有“被神化”和“树典型”的嫌疑,但在当时,改革已经逐渐开始成为官方和民间不争的共识。
34岁的宗庆后还处于找感觉的阶段,他回杭州城两年,刚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学校的校办工厂当推销员,此后10年间,他一直不温不火地呆在这个位置上。同样在找感觉的还有马云,1983年,在受到女排精神的激励后,第三次参加高考的他终于考上了杭州师专。
这是一个官方与民间都紧张而摸着石头探索的年代,这又是一个创业激情被唤起、民间力量开始喷薄的年代。
备忘录
●1978年底,中国 *** 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年底,可口可乐开始在北京设立临时办事机构;宝钢公司在上海北郊的一片海滩上打下了第一块基石。
●1979年1月,香港商人霍英东谋划在广州盖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
●1980年,一无所有的乔金岭筹建长葛县第二化工厂,生产石棉瓦和硫酸铜。
7月,深圳、珠海和汕头等地创办特区的思路渐渐明确下来,后被明确定义为“经济特区”。
10月,北京,已经是五个孩子母亲的刘桂仙,在自家31平方米的堂屋中,开起了北京第一家私人经营的“悦宾饭馆”。
年底,知识分子出身的陈春先在中关村的一个仓库办起了国内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中国的硅谷”中关村开始萌芽。
●1981年,作为1977年第一批返城的知青,李晓华开始在北戴河海滨卖冷饮。
作为上海市委重点培养的青年团干部王正华,决定选择成本较低的旅游业,解决街道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
李东生与创业伙伴在还只有一条街道的深圳,创办了TTK磁带公司。
●1982年初,温州八大王事件爆发。这年,国务院两次下令,严查破坏经济秩序的罪犯,个体经济遭受重创。
出生广东梅州的梁亮胜带着太太,和所在工厂的其他40多名工人前往香港,住进了只有四五平方米的“贫民窟”。
多次倒腾生意均告失败的左宗申把岳母家一间临街住房空出来,用牛毛毡搭起了一个遮雨小棚,开始修摩托。
●1983年,倒玉米的王石用净赚的300万元,成立了以主营进口专业视频器材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
24岁的王文京辞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司的工作,到中关村注册了个体形式的“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
11月,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开始被塑造为改革的典型人物。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