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专题:《买单:我们到底消费的是什么》
最后,研究人员用这个实验的变式再次进行了实验。这一次他们调整了广告和广告的评价问题,其中增加了兔巴哥,谁都知道这不是迪士尼的动画形象。约16%的受试者随后声称,童年时他们在迪士尼主题公园与兔巴哥握过手。随后的研究发现,反复呈现假冒广告导致更高的虚假记忆的出现率——一项研究为25%,另一项为36%。在其中一个研究中,那些表示自己有过和兔巴哥见面的受试者被直截了当地问到,对于这个童年经历,到底他们能够回忆起的具体细节是什么;其中有62%表示能记得和它握过手,超过1/4的受试者能记得它对他们说:“嗨,最近怎么样?” 最近,神经学家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机拍摄大脑某一部分的神经元放电的图片表明,大脑回忆“真”和“假”的记忆活动十分相似。显然,当翻译器帮助我们确保“自己”的故事正确,是和大脑的记忆活动相同的。 创造模式 现在,对所有的这些研究,我们必须提醒读者注意下面这几点。这些虚假记忆发生的概率远远低于百分之百。仅仅看到广告显然不会让你重写整个人生。虽然这种“源记忆”并不总是可靠的,但是它们只有在情景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情况下,才容易误导我们。例如,不管看到什么样的广告,很少有人会有这样的虚假记忆:记得在迪士尼乐园见到过总统或猫王,或从克拉里昂星球来的外星人。至于耶鲁大学研究的“启动”效应,在现实世界中,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产品,要复制研究的实验条件是非常困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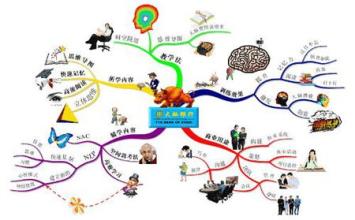
这些警告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你才不会在稍微了解了翻译器的功能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哇,人都是白痴。当然我们想要说明的并不是这个。行为科学研究者(特别要包括加扎尼加)会告诉你,这种结论离事实很远。虽然研究人员曾将非意识思维和抑制等作用联系在一起,但是最新的观点是,这仅仅是效率问题。弗吉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蒂莫?D?威尔逊,在他的精心构思、令人印象深刻的《我们是自己的陌生人》(Strangers to Ourselves)一书中写道,在“任何时候,我们的5种感官都在接收超过1 100万条信息”。这显然远远超过意识可以处理的数量。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威尔逊认为,依靠非意识思维“对我们的生存非常重要”。加扎尼加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并指出,大脑的工作相当惊人。他写到,大多数时候,“我们的翻译器运转得很好,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 其实讨论上述研究和结论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而自己还不能直接地意识到这些因素;这并不是过激的观点,而是很多认知研究的中心论点。翻译器可能会出现错误,这应该是它正面临着“超多的数据或毫无意义的信号”,加扎尼加解释说:“当变量很多,或者我们坚持用逻辑的思维来思考毫无疑义的信号时,我们就能够自欺欺人地找到实际不存在的联系。”虽然我们的大脑善于处理大量的信息,但它并非十全十美。正如威尔逊所言:“事实上,我们往往不自觉地‘强迫’新的信息适应我们已经形成的观念。”当发生这种情况时,理性思维就被基本思维所取代。基本思维通常在我们不太明白的情况下,揭开需求密码。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