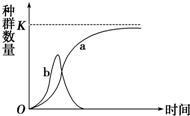我对这个世界知道什么呢
当人们提起我的名字—理查德·布兰森,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维珍涉足的音乐产业。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传统。当我回首过去,我发现那段早期从事新闻业的生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虽然它是那么的短暂,而又幸运,但却为我未来的商旅生涯开启了一盏明灯。
要说让一个年轻人发现人生的意义价值,有什么能比做记者更加合适的呢?恐怕我永远不会成为一名一流记者,但是,我善于倾听,我总能让我的受访者侃侃而谈。我喜欢问那些“事后诸葛亮”的问题,即便它们“很傻很天真”。这两项技能即便是我下海经商后也让我受益良多。事实上,倾听和好问是常被商界精英们所低估的两项基本素养。
我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总体来说,那是一个有着关怀和同情的时代,很多年轻人变得关注社会,开始意识到世界是怎样对待少数族裔的,他们应享的权利是什么,以及更加公平的措施会如何改变状况。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我怀着好奇心跟踪着美国黑人反抗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经济不平等的斗争。
1968年3月我有幸参与了前往格罗夫纳广场美国驻伦敦使馆的游行,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我与左翼领袖塔里克·阿里和演员瓦妮莎·雷德格瑞夫并肩前行。当时我也曾畏惧过马背上挥舞着警棍的警察,和投来的催泪瓦斯。我也被这样的想法所激发,就是年轻人在做某种直接的和良性的事情。透过《学生》杂志,我—一名幸运的英国私立学校学生—有生第一次听说了关于非洲的恐怖消息。我对那里的压制、疾病和饥荒有了点了解。《学生》杂志组织过抗议发生在尼日利亚巴亚弗兰战争的集会。我们展示了《星期日泰晤士报》著名摄影家唐·麦库林在越南和柬埔寨拍摄的那些令人心碎的照片,唤起公众对于这些在内战中数百万饱受饥饿的儿童们的关注。
1968年秋季刊的《学生》杂志充斥着愤怒:在美国的贫民窟,黑人们发起暴力示威;在巴黎的街头,学生们用鹅卵石冲击警察;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人用坦克镇压布拉格之春运动;越南在弹雨中枯萎。要报道的太多了。我记得,我们让盖雷斯·布兰德斯写美国,报道越南的是当时年仅17岁的朱利安·马岘,现在是独立电视台资深海外记者,当时他采访了一名北越的医生关于越共士兵死于痢疾的情况。但是真正让我感到心灵震撼的,是我对美国著名激进派作家詹姆斯·鲍德温的采访。要是你依然怀疑“提傻问题”的好处,请你看一看以下这段访谈,看一看詹姆斯·鲍德温是如何回答我那些“傻”问题的,假如我有哪怕一丝委婉,我都不会引起这样的火焰。
詹姆斯·鲍德温,你受过什么样的教育?
在学校,我在《圣经》的技术中受训,而我所受的教育来自街头巷尾。
在美国有好的学校吗?
怎么可能有?那都是白人建立、白人管理的学校,他们绝不让我们黑人靠近半步。
你认为白人最终会给你们自由,还是需要靠你们的抗争来争取自由?
白人甚至都无法给予他们自己自由。你们的履历并不让人非常振奋,我绝不奢望你们能给我任何东西。我将去拿我所需要的——不必从你们那里,这是你们的谎言,我会过我的生活。我对白人做什么没有兴趣。白人没有那么重要。人去抗争的不是针对白人,而是要打破横亘在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权力。就这么简单。这根本不是种族之间的战争,这是贫穷与特权的斗争,是自由与压迫的斗争。
我被鲍德温对于生活的不公表达出的尖刻而又不是克制的怒火感到深深的震撼。
在1963年撰写的《下一次的火》中,他预言在10年内,白人特权将被取消。我问他是否依然坚持这个观点,
鲍德温回答:“我并不是这么说的,我只是说我有这样一个预言,预言家可能是对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西方的社会体制正在陷入困境,而且,显然在崩溃。”
“是来自黑人的压力吗?”
“是因为他们白人自己编制的谎言再也纸包不住火了。”
他的谈话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年轻的白人编辑而言是那么铿锵有力。那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愤怒,因为我没有任何可以拿来与之参照的。我想帮助改变世界,可我对这个世界知道什么呢?

不久之后,我听说了关于黑人社会活动家史蒂夫·比克的事情,随后遇上了纳尔逊·曼德拉这个名字。他的父母给他取这个名,是因为“纳尔逊”听起来像一个白人的名字。他们希望他能够在这个白人当道的世界里过得更好。他被一些英国人视为危险的极端主义者。但是我逐渐了解了这个非凡人物的真实内心。
曼德拉在非洲广受爱戴,而我第一次见他却心存畏惧,但是见面之后,他的微笑,他的热情和孩子般的幽默深深地打动了我。“理查德,很荣幸见到你。”我后来才知道,他总以这样的开场白和陌生人打招呼。这是一个因他的肤色和信仰而饱受沧桑的人。他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受害者,曾被判入狱监禁46年。他的囚衣号码是466/64,那是因为他是第466号囚犯,并且于1964年发配到恐怖的罗本岛监狱服刑。他的囚房只有6英尺见方,确有2英尺厚的墙,整个牢房仅仅刚够他躺下。他在服刑的最初岁月里是和政治犯们一起度过的,每天用4磅重的榔头把岩石敲成碎砾。这绝对是一件折磨人的苦活。我曾经去探访过他的牢房,那简直是人间地狱。
在他的自传《漫漫自由路》中,他说到,罗本岛绝对是南非铁血政治中,残忍暴虐的典型代表,即便是监狱的工作者,都不堪忍受其苦。白人典狱长高高在上,说着南非语,要我们像奴隶一样伺候他。他命令我们喊他主子,但遭到我们的拒绝!罗本岛真可谓“黑白分明”,所有的狱卒都是白人,而所有的囚犯都是黑人。
但是,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一星半点的愤怒。
他在当选南非总统后不久,出席史蒂夫·比克的雕塑揭幕仪式上发表的演讲最能表达他的心声:“当史蒂夫支持并投身于‘黑人自豪运动’中时,他从没有把‘黑人’神化……接受我们是黑人这一事实,是一切的起点,也是我们投身于黑奴解放斗争的基础。而今天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停止战争,摆脱贫穷,破除愚昧,战胜疾病,是我们重建和发展的基础。”
在这寥寥数语之间,流露出的是他伟大的领袖风范。这里有对人性的关怀,和大智慧。这一席话既展现了曼德拉的风度,又并非高高在上,夸夸其谈。他给了所有听众一个清晰而又明确的努力方向。
有一项优点是曼德拉在演讲中无法展现的,却也是大多数杰出领袖所共有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出色的推销员。曼德拉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推销员,无论什么场合,曼德拉都不会放弃任何机会,为他的国家争取援助。一次在伦敦,他和我、乔恩、霍利、萨姆以及几个亲近的朋友一起吃饭。饭后我在我的笔记本上写道:“在任何一顿宴席上,曼德拉都不忘为他的穷人们争取援助。他和他的新婚妻子格拉萨·马谢尔,还有他的女儿来我家,开口第一句话便是:‘这真是一顿美妙的午餐,但是你知道吗,上周我去见比尔·盖茨,他可出了价值五千万英镑的美元。’全场喷饭!”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