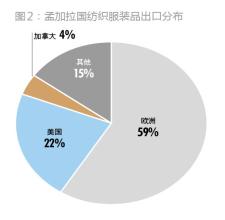第四,高估资产价值的行为应该更容易出现在投资的初期阶段。在Cumming教授的数据中,处于起步阶段的56个未实现的投资样本平均内部报酬率为126%,而对应的34个已经实现的投资样本的内部报酬率仅仅为48%,两者相差了78%。在早期阶段的投资中,数据也显示出了相似的结果。而私募股权基金在扩张期企业的投资样本中,未实现投资收益与实际已实现投资收益的差距仅为8%,明显地比那些更早期的投资要少。
私募股权基金所投资的企业在报告期内的估值水平可能显著地高于私募股权基金在退出该企业时所实现的实际回报水平,这种风险投资计量价值的减少可能是由于市场环境的恶化所导致,也可能是某种特殊的影响因素导致了私募股权基金经理未能在报告期意识到这种潜在价值的变化。由于投资初期阶段距离私募股权基金退出被投资公司的期限仍很长,在较长的投资期间内很难区分究竟是私募股权基金有意地高估资产价值还是在报告期至退出期内资产的实际价值发生了不利的变化,从而造成声誉损失的可能性和损失程度也会较小。
第五,私募股权基金全部退出被投资公司的情况下,相比部分退出而言,未实现投资回报总体上有着更高的估值水平。也就是说,私募股权基金的部分退出,可能有助于更加现实合理的估值。私募股权基金部分退出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减轻退出时作为出售方的风险资本和购买方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风险资本不选择全部退出而是选择保留原来投资企业的部分股份,是表示风险企业质量较高的一个积极的信号,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私募股权基金对该企业未来前景的看好和对当前估值水平合理程度的认可。
由于私募 股权基金相对投资者在信息方面的不对等地位,决定了私募股权基金在操纵信息上的主动权,降低了资本市场上资源配置的效率。如何纠正这种不对等地位,从而迫使私募股权基金“说真话”呢?
为了使得私募股权基金“说真话”,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消除信息不对称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手段,尽可能准确地反映私募股权基金投资运作的情况,避免信息失真的现象发生。

然而,在私募股权投资项目中,私募股权基金与被投资企业往往通过一些非常复杂的合同关系来约定投资人和创业者之间的利益、风险以及激励机制等等,而且被投资企业出于维护自身在市场中利益的考虑也有着一些经营项目保密的需求,所以完全敞开地向众多投资者披露基金运作的详细信息是不现实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应当通过何种方式准确地反映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情况。
为了准确地反映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情况,首先需要考虑的应当是建立并完善私募股权基金信息披露的会计标准。更加严格的会计标准使得私募股权基金的信息披露建立在透明且可比较的基础之上。私募股权基金按照相同的会计标准对其投资的资产回报进行估计,能够使得投资回报之间具有可比性。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由于个别私募股权基金高估其投资回报而导致的资本在不同私募股权基金之间的不合理分配。
其次,行业的自律监管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模式是适用于私募股权基金监管的手段。私募股权基金的信息披露离不开政府的监管,因为严重缺乏透明性的私募股权基金在缺乏政府管制的市场环境下,很容易形成行业的混乱,当其行为失控时甚至可能引起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然而,由于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专业性,仅依靠政府的监管是显然不够的。政府并不一定具备足够的私募股权基金的行业知识和经验,而且政府的过度的行政干预也可能会抑制整个私募股权基金行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在政府的适度管制之外还需要借助整个私募股权基金行业的自律性监管来增加其透明性。也就是说,在政府监管的基础之上,通过私募股权基金行业的专业人士之间构成的自律组织的配合,实现私募股权基金之间的相互制衡来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诱使私募股权基金尽量“说真话”。
此外,信息获取之后也可以通过外部的独立组织进行公开的客观的评估。这种独立组织通过收集、加工私募股权基金披露的信息,聘请专业人士利用其专业知识和行业经验对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运营情况进行评价,并将这种经过加工的信息进行出售,有助于减少由于投资人专业知识的匮乏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