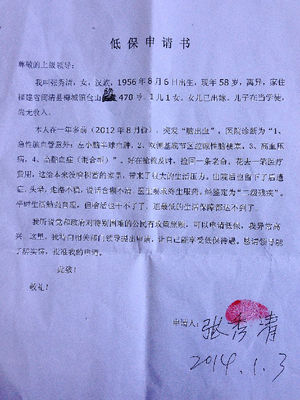上周听大学同学说:我们一位老师彭教授去世了,提起彭老我就想起认识他的那些往事来。
上世纪80年代初,某周一早上我在去学校的公交车上与一位工人模样的老头闲聊起来,说着说着就说起我是某某学校的大一学生,那人就问得更多了,譬如:你们学校怎么不住校啊,学校食堂饭菜质量好不好啊,等等。我把学校说得跟地狱差不多,老头还不时地笑笑。可是后来等我下车时老头也下车了,等我进校门时老头也进校门了,不过,我心里还在想这老头最多也就是我们学校的工人而已。可是,等进了校门以后人家给老头的礼貌礼节告诉我,老头绝对不是普通工人,再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我们系的教授彭老。因为有了公交车上“老工人”的不好印象,听彭教授上课我就是提不起精神来,心理感觉他就是一“老工人”而已。大三的时候学校组织一个代表团去德国慕尼黑大学交流,我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彭教授是代表团团长。才短短的一个多月,近距离地接触以后,改变了我三年来对他的看法和成见。彭教授当年就是德国慕尼黑大学留学的,对他的学术、他的为人以及他的德语的了解,都在我们近距离接触中有了不同的认识,此后,我一直很敬仰彭老教授。
就在那一个月亲密接触中,我也很坦诚地说了我对彭教授的最初认识,彭教授没有更多的训导,记得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故事也是说人不可貌相的。
有一对衣着简陋的夫妇到哈佛大学,他们胆怯地走进了校长接待室想见校长,可是校长的秘书说:“校长,他整天都很忙。”穿着褪色方格棉布衣的妻子微笑着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等他。”几个小时过去了,秘书没再搭理他们。秘书不明白这对乡下夫妇和哈佛大学会有什么关系,她希望他们会自个儿离开。可看来他们没有丝毫想走的意思,尽管不太情愿,秘书决定还是去打扰校长。“可能,他们只需见您几分钟。”她对校长说。
校长的确很忙,他显然不会花费太多时间,在那些他看来无关紧要的人身上。校长还是点头同意会见了这对夫妇。女士告诉校长:“我们的儿子进入哈佛大学一年了,他爱哈佛。他在这里很快乐。”“夫人,谢谢你的儿子爱哈佛,你知道,哈佛的学生都会爱哈佛。”“一年前,他意外地死了。”“噢,夫人!”“我丈夫和我想在学校的某个地方为他竖立一个纪念物。”校长被这个想法震动了。“非常遗憾,”他提高了声音,“夫人,你知道,我们不可能为每一个进入哈佛大学后死去的人,竖立纪念物。如果这样做,这哈佛大学不就成公墓了吗?”
“噢,对不起,先生!”女士赶紧解释,“我们并不想要竖立一尊雕像,我们只是想说我们愿意给哈佛建座楼。”校长的目光落在这对夫妇粗糙简陋的着装上,惊叫道:“一栋楼!你们知道事实上,造一栋楼要花费多少钱吗?和你这样说吧,仅在哈佛的自然植物,价值就超过七百五十万美元!”校长为这远道而来的夫妇悲哀,觉得他们太幼稚了。
女士沉默了,她转过身静静地对她的丈夫说:“这笔耗费不是可以另开一所大学吗?亲爱的,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建一所自己的学校呢?”面对校长的一脸疑惑,她丈夫坦然地点了点头。斯坦福夫妇离开了哈佛,他们去了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他们建立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大学——斯坦福大学。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说起来我们都很明白,可事实上我们未必能在实际生活中记得住。我们看人总喜欢以貌取人,长相、言谈举止以及穿着打扮等等,而且一旦有了这以貌取人的第一印象以后就很难改变对这个人的看法,除非再有其他特别反差的印象。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