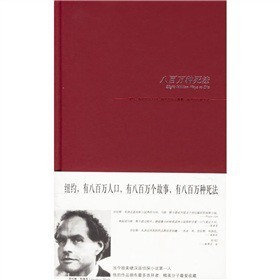帕金森定律和彼得原理,以及与其类似的墨菲法则,在管理领域名闻遐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这些人称为另类管理学家。他们以其特有的幽默、调侃和讽喻,对现实中的管理弊端进行了无情地揭示。帕金森对官僚机构的各种病症提出了一系列解释,尤其是关于机构膨胀、人员增加、效率低下、公司瘫痪等问题形成了完整的独特看法。彼得对组织中的晋升问题进行了眼光独到的分析,从造成 不胜任的根源中寻找改善管理的答案,并以此为据展望了人类的未来。墨菲对细节带来的灾难进行了归纳,试图探讨管理中的低概率事件和不完全控制问题。这些表面诙谐而实质严肃的论述,直指学院派管理学科的不足。他们的贡献,是把来自生活的智慧运用于管理活动,对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法则给出另类回答,从而针砭主流管理学科的理论缺陷,促使管理学科向贴近现实方向发展。他们的睿智和机敏,令象牙塔式的研究失色,给管理学界吹来了一缕清风。在管理大师的行列里,他们就像扑克牌中的Joker 那样,具有与电影界的卓别林相当的地位。
脍炙人口的帕金森定律
如果不是因为杂文调侃式的《帕金森定律》,恐怕这位英国人也就只能在一个小圈子里摆摆绅士派头,调侃揶揄人情世故,过着“贫嘴帕金森的幸福生活”。但是,一篇杂文,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使帕金森成为管理界的世界级名人。
诺斯科特·帕金森(Cyril Northcote Parkinson,1909-1993),是一个很难定位学科领域的名人,他的出名,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深刻的学术造诣,而是因为他是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作家。他的本业是历史学,阴差阳错,却因为管理方面的杂文名震天下。
1929年,帕金森进入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学习历史,1932年毕业。可能同英国重视海军的传统有关,帕金森对海军历史非常感兴趣,1934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海军的。1935年,帕金森在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海军、空军、陆军和军事培训部门担任过一系列职务,位居少校。在政府以及军方的工作经历,使他对官僚体制有了切身感受,后来他对官僚主义的批评,有许多素材就来源于这段经历。战后,帕金森一直从事教学与写作,曾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和位于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执教。后来,在美国哈佛大学、伊利诺伊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当过访问学者。他的著述颇丰,据说写了60本左右的书。这些书包括系列海军历史小说,还有《政治思想的演变》、《法律与收益》等学术性著作。但是真正使他扬名世界的,是同管理紧密相关的讽刺官僚主义的小册子《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这本书带来的巨额版税,使他悠哉乐哉地辞去马来亚大学的教职,定居于英国海峡群岛(the Channel islands),后来又移居马恩岛(Isle of Man)。
《帕金森定律》一文,首次在1955年11月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上发表。其后,他不仅在《经济学人》上继续发表类似文章,还在《哈泼杂志》(Harper’s Magazine)、《报道者》(The Reporter)上发表相关文章。这些系列杂文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于是,帕金森把这些半调侃半正经的杂文汇集成册,于1957年先后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取得相当不错的销售成绩,长期踞于畅销书排行榜之首。值得一提的是,帕金森在1968年出版了另一本有意思的书,书名为《帕金森夫人定律》(Mrs. Parkinson’s Law)。不过,这本书与官僚组织无关,作者把目光从办公室转移到了家庭,讲述的是家庭主妇如何为人处世。不变的是作者敏锐的观察、辛辣的讽刺和幽默的风格。
《帕金森定律》一书,据说有十几种文字的译本。中国市面上能看到的汉译本,有1981年台北中华企业管理发展中心出版的潘焕昆、崔宝瑛译本,译名为《帕金森定律——组织病态之研究》;有1982年三联书店出版的陈休征译本,译名为《官场病:帕金森定律》;有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四元、叶凯译本,译名为《帕金森法则》;有2004年中国商业出版社的编译本《不可不知的管理定律》;有2004年甘肃文化出版社的编译本《帕金森定律》;有2004年地震出版社的编译本《世界上最伟大的管理法则》等等。除了《帕金森定律》这本书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出版过帕金森谈退休后调适的《人生不言老:生活的重新定位》;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曾经出版过一套《帕金森通俗管理丛书》,是帕金森同拉斯托姆吉(M. K. Rustomji)合著的小册子,包括《待人接物》、《心中有数》、《精打细算》、《管理诀窍》、《知人善任》等。
所谓帕金森定律,其实质是用另一种眼光看管理,对现实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提出与学院派管理学家截然不同的新解释。具体有以下内容:
机构和人员是怎么增加的?
这是帕金森定律中最有名的一条,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雇员的数量和实际工作量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联系。”机构和人员的增加,不是来自于现实工作的需要,而是有它自身的法则。在这里,帕金森向人们的常识提出了挑战。按一般的逻辑来判断,工作量的增加才会导致雇员的增加。如果工作量不增加,那么,雇员的增加必定会引起工作时间的减少,工作人员就会更加闲散。帕金森则给出了相反的观点。他强调,管理机构只要能增加人就增加人,关键在于管理活动能够自己给自己制造工作。管理者总会忙不过来。效率低下的人不一定显得无所事事,工作量少的人也不一定显得散漫悠然,相反,有可能这种人反而比谁都忙。帕金森举了一个例子:假如有一位清闲的老太太为了给侄子寄张明信片,她可能需要忙一整天,而一个真正有效率的人则可以在三分钟内完成。
关于人员增加的论证,帕金森是拿政府机关开刀的。在他的书中假设了一种状况:一个公务员A,在工作中感到力不从心,疲惫不堪。在他自己看来,工作任务太重了,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然而,这很有可能是他人过中年后精力衰退的自我感觉。A面对这种情境,有三种方式可以解决所谓“工作过度”的问题。第一,他申请辞职;第二,他申请让公务员B来分担自己的工作;第三,他可以要求增加两个助手公务员C和D。从人之常情来判断,A只会选择第三个方案。因为他若辞职,以前就白干了,养老金就泡汤了。如果用B来分担他的工作,两人就平起平坐了,上司退休时,A就给自己增加了一个竞争对手。所以,A会坚持增加C和D当自己的助手(如果只有一个助手,就同用B来分担工作效果一样),两个或者更多助手之间会相互牵制,而控制权则牢牢掌握在A手里。终有一日,C也会抱怨工作太累,A给他指派两个助手E和F。同时,为了摆平关系,还会给D也委派两名助手G和H。在此,帕金森点出了机构膨胀的第一个动力:官员想要给自己增加助手,而不是对手。
到此,原来一个人的工作现在由七个人来承担。而实际上,A比以前更加累了。一份文件要在每个人的手上转一圈,E接到后认为这事归F管,F便写一个草案给C,C修改一番后向D征询意见,D见G在休假,就叫H处理,H添了几句话后,经D签字,又回到C手里,C据H的意见改动几处后上交给A。而A正思虑重重,有很多烦心事。明年他将要接替W的职位,所以他得在C和D之间物色一个接班人。尽管G不太符合休假条件,但他不得不同意G的休假请求。他有点担心H,应该让H去休假,因为H身体不太好,还有如F的增加工资问题,E的内部调动问题,D的办公室婚外恋问题,G和F的人际关系冲突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总在A的心头萦绕。那份文件传到他的手里,他向来是一丝不苟的,所以尽管忙也得仔细修改文稿。他删除了C和H的废话,修改了几处语法错误,抱怨了一通年轻人办事的不细致,总算完成了文件。等到A下班,已经暮色苍茫。工作的过分辛苦,使他增添了缕缕白发。机关中的人员,总是互相给对方添事,人一多,做同样工作所需的时间比以前更长了,没有人闲着,都忙得不可开交。由此,帕金森提出了机构膨胀的第二个动力:官员们相互之间制造工作。
帕金森结合英国政府的实际情况,对自己的定律做了说明。从1914年到1928年,英国海军官员人数,从2000人增加到3569人,以每年5.6%速度递增。而在此期间,由于《华盛顿海军协定》的限制,海军规模在减小,1928年的海军士兵人数是1914年的三分之二,军舰数是1914年的三分之一。从1935年到1954年,这种状况还在发展。这一期间,英国海军部的人员从8118人上升到33788人,而此段时间英国海军的地位在不断下降。殖民部从372人增加到1661人,而这正是大英帝国殖民地迅速减少的夕阳残照时期。据此,帕金森认为,无论政府工作量是增是减,甚至是消失,雇员数量都受帕金森定律的支配而增长。
帕金森通过多年的资料对比,在撇开一些细节的情况下,仅仅计算行政人员的增长数量,得到的年增长率为5.75%。他甚至总结出一个数学公式来表示帕金森定律,算出的年增长率大致在5.17%和6.56%之间。

帕金森定律虽然是以公共部门的人员膨胀为例,然而,企业中这种情况同样存在。现成的例子,莫过于金融风暴打击下的美国三大汽车巨头。福特、通用、克莱斯勒,被媒体称为汽车工业的“dinosaur”,即恐龙。而三大恐龙的形成正同机构和人员膨胀有关。没有三大巨头就没有底特律,这座汽车城的汽车员工达三十多万。底特律的汽车产销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迅速增长,巨额利润带来的是员工的迅速增加和工资福利的快速上涨。撇开车型、质量等因素,单纯从人均产量看,当今日本的汽车企业每人每年生产汽车67辆,而美国的通用公司每人每年生产汽车只有21辆。迫于工会的压力,通用的工人工资和各项福利达到每人每小时78.21美元,而日本丰田的工人每人每小时是48美元。再加上通用的医保开支是丰田的10倍。这种状况,恐怕斯隆再世也难有回天之力。所以,帕金森定律不仅仅是揭示了政府的膨胀问题,同样也可以警示企业的膨胀问题。尤其是经营效益好的企业,稍有不慎,经营效益就会被恐龙化的机构和人员吞噬。
帕金森不是管理学家,所以,他的书中没有管理学家擅长的数据模型和逻辑推导。他强调,植物学家只是告诉我们杂草长得有多快,而不去考虑如何除草。帕金森提出的挑战,在一定意义上直指管理学的软肋。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