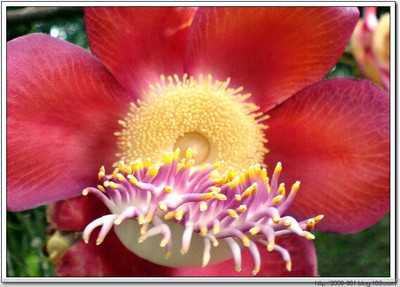给小平同志的两个要求
《21世纪》:小平同志的南巡,给矛盾中的大家很大的支持吧?
邹尔均:1984年,刚过春节,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就到了厦门。小平同志是倡导改革的,是支持我们特区工作的。所以我们就想,要跟他老人家讲讲,诉诉我们心中的郁闷和表达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想法。
但是,中央传下话来了,小平同志在南巡中要“三不”。不听汇报,不讲话,不要陪吃饭。我们强烈要求,无论如何要听汇报。这个要求传上去了。小平同志到了厦门之后,陪同小平同志的中办同志传话说,可以给老人汇报厦门的情况,但是只给五分钟的时间。
我一方面很激动,但是另一方面又比较为难,因为我要讲的很多,5分钟实在装不下。
《21世纪》:那后来这五分钟怎么利用的?
邹尔均:汇报厦门的概况,提两个要求。
这两个要求是在小平来之前,我们市委市政府讨论过并报省委都同意了的,大家都一致认为有两个要求最重要,值得提。
一个要求是特区太小了,我请小平同志到楼顶上去看特区的时候,我就直接跟小平说,“您看,太小了,一眼就望穿了,就是这2.5平方公里”。他看了以后就笑了,但他不回答你的问题。第二个要求是,是不是让特区更开放一点?我们厦门能不能办个类似香港的自由贸易港那样的特区呢?我们很想让小平同志讲讲,他还是什么都没说。
我汇报完,一看时间,超过了2分钟,汇报了7分钟。
《21世纪》:小平同志一直一言不发?
邹尔均:他后来一路上问了我很多自由港的问题。我们当时才刚刚搞经济特区,对于自由港的知识也是有限。我尽我所知讲给老人听,他还是不满足,继续提问。我最后只好如实报告,我们知道的不多,还要边实践边学习,边干边学。还需要继续学习。
要离开厦门,临上车的时候,他开口回答我们的问题了。他对我说,你提的两个问题我带回去,让第一线的领导来做决定。他微笑,他点头,他还是不多说话。但是我当时就觉得,他是接受我们的建议了。我预感到厦门经济特区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将要来临了。
《21世纪》:小平同志这次南巡之后,一下子开放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形成了一个沿海开放带。你的扩大厦门特区的建议看起来在全国都发挥了作用。
邹尔均:后来中央有领导给我转述,小平同志在北京说,厦门的两条,一个是2.5平方公里太小,要扩大到全岛,我看是可以的。
他们要搞一个自由港,让他们试一试吧,这么一个城市,失败了也不要紧,何况不会失败。后来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到厦门的时候,就加了两个字“某些”。可以给厦门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这样,我们两个要求一下子就兑现了。
《21世纪》:特区建设少不了来自北京的支持,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当时是怎么传达到特区的呢?
邹尔均:不仅小平同志支持我们的特区建设,谷牧同志在中央分管改革开放,也分管我们经济特区。他一直坚持“三个一”,一年调研一次,他每年要走一趟沿海和经济特区,问问我们在改革中有什么问题,如果现场能解决的就立刻解决,解决不了的就反映给中央。
一年开一次经济特区的会议,经过讨论,中央发一个会议纪要。那个时候,我们遇到了制度性难题,新组织调查研究,拿出建议和办法放到中央的会议上去讨论,发一个纪要,我们下边就执行。
年年如此。我们每年都希望谷牧同志过来,我们跟他讲的是心里话,没有官腔没有套话。当时的这个渠道很通畅。国务院还有一个特区办,这也是我们诉求问题的地方。经过他们协调,帮助特区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是谷牧同志带着我们去闯。
动了刀子的“改革”

《21世纪》:比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更难的改革,是体制改革。厦门特区的体制改革,是怎么起步的?
邹尔均:从具体领域开始。我们最大的改革就是直接动刀子,砍掉政府部门自己的机构。1987年,我把8个工业系统的专业局一下子都取消掉了。放权给企业自己,给企业以自主权。
原来,外商来厦门这里投资谈判的,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比较多。找副厂长,副厂长解决不了问题找厂长,然后是书记,然后是分管局副局长、局长、局书记,然后反映到市里的经委,然后是分管的副市长,人家说,你婆婆太多了,我都搞不清楚,而且意见不一致,效率也低。所以我取消了这些局,就没这些环节了。
这一刀很厉害呢,砍下去后哇哇叫。我对这些部门说,给你们吃两年的“皇粮”,原定的财政预算拨款不变,你们自己去搞公司。如果两年你都养活不了自己,那就是你没本事。时间一到我们就断奶了停止拨款。实际上他们很快就上路,就融到市场紧经济里去了,成为商品进入市场的推动者。
这样一来,环节少了,效率提高了。把你们过去行政管理的职能市场化去经营。你们不再是企业的主管部门去管他们,你们是市场的交易关系了。
《21世纪》:涉及到具体的利益,改革遇到的阻力就大。你在厦门推行的“放水养鱼”,减免企业的红利,很有名。
邹尔均:当时搞“放水养鱼”,是想企业除了交税以外,我们基本上不要红利了,留给企业自己,或者至少留给企业60%,一块钱企业自己留6毛。让企业得大头,利用这个资金,让企业自己去发展生产。
厦门港务局就是个好例子。他们弄了两个集装箱桥吊,一个吊一年就3.5万个标箱,可是香港同样的吊每年就能完成12万个,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水平运输能力不够,其他的流程环节不配套。
港务局维持着微利或者微亏的状态,我说我不要你的利润了,你赚来的钱一分钱财政也不要。把利润留给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条,赚了钱首要的是完善设施,其次才是可以提高大家的福利、奖金。尽管当时有反对的声音,但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不过分。
第一年赚了2000多万;最多的一年盈利1亿多。我说厦门财政不眼红,说好了不要就是不要,后来,我到省里去工作的时候,他们已经积累了7亿多资金。
厦门的任务
《21世纪》:厦门特区毗邻台湾,这是厦门的优势还是劣势呢?
邹尔均:特区为什么划给厦门,1980年调查的时候,就有过分歧的。反对意见说,这里距离台湾很近。谷老和很多人认为距离台湾近,就必需放在厦门。中央批准了提议。
我跟梁湘开过玩笑,我说,深圳靠近香港是得其利,厦门靠近台湾是得其害。当时两岸的关系紧张,刚到厦门的时候,傍晚5点,海滩上就要戒严。
《21世纪》:这给厦门特区的发展带来很大不方面?因为你总要去吸引台资过来,否则厦门的特区的优势就不明显了。
邹尔均:台商想过来还是很困难,我们就只好去香港、新加坡等第三个地方跟台商见面,请台商过来。
后来1987年底,蒋经国允许台湾同胞回乡探亲访友,两岸的关系有所松动。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抓紧这个时机,我向正在厦门视察的杨尚昆同志(时任国家主席、对台工作小组组长)提了个要求,我们可以专门办一个台商投资区。杨老表示可以考虑。
1988年下半年,他派了丁关根(时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来这里调研,初步的结论是可以的。转年,召开全国人大期间。我去汇报。我带了两个方案去汇报,一个方案是海沧60个平方公里,当时到会的人听到这个,都很震惊,“你搞这么大的一块地!”
我就只好说,我还有小的呢,杏林10个平方公里。这一下争议声音小了,但还是有人说,厦门刚开始的时候才2.5平方公里呢,现在一下子搞几十个平方还是太大了。
最后,田纪云在会上总结的时候,一句话“两个都可以”。他说,“不要划界限,需要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收效一片”,这四个一片就这里来的。在政策上,田纪云给厦门台商投资区的是“享受现行特区政策”。
《21世纪》:加上厦门、海沧、杏林,都实行原来特区的政策,这就意味着特区的面积一下子扩大了。
邹尔均:说到这,我就有点内疚啊,我对中央对台工作的要求理解不深刻,我还谨慎的要一个有界限的,中央支持的是一个没界限的。要一个给三个。后来台塑要搞一个“海沧计划”100平方公里,借这个机会我再跟中央申请,补一个集美。这样加起来实行特区政策的范围就有了500平方公里。
今天,厦门还是要加强、加倍对台经济合作的进度。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对台的经济合作有更好的政策支持。
改革要放一定的权
《21世纪》:今天回顾20多年来的改革风雨,您认为改革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邹尔均:厦门的经验是,争取到了两个权。
我们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当时中央领导人来的时候,我就这样要求。他们问,你特区了还要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我说,“特区权没有省大,把特区的政策和相应的权结合在一起,我相信能办得更快”。赵紫阳回去之后就批准了。我觉得,适当的放权,对于发展地方经济很重要。
另外一个是,厦门享受较大的特区立法权,深圳就有这个权。就这两个地方有,改革的手段就比较多了。
《21世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你多次提到改革开放特区建设给了我们经验也给了我们教训,这都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邹尔均:改革遇到过很大阻力,阻力来自于意识形态。计划经济曾经对刚成立的新中国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后来,有人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区别看成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界线,到意识形态领域这个高的原则上去看,就错了,把手段当作性质,就错了。
改革之初,很多阻力不是来自下面,而是来自上面。回首改革这么多年,就是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但是计划经济那一套,已经有完善的法规制度了,有章可循;我们所做的那一套市场经济,都是与这相矛盾的甚至是抵触的。你不去闯,要你特区干什么?不去闯,那就是你的失职。不仅是失职,甚至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败者。我不愿意当失败者。
特区的使命这样看——特区因改革而生,改革是特区的魂,我们的使命就是改革。闯的失败了,就这么一个“点”。成功了,就能为全国提供经验。想到这里,我们的两个老人,小平同志是总设计师,谷牧是总工程师,我们老一批特区人,也就是项目经理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