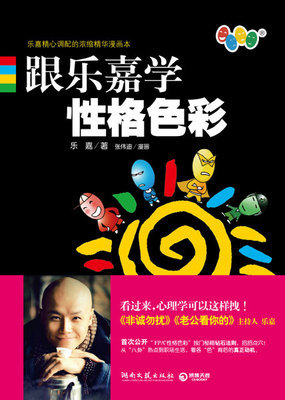我为什么成了一个这样的作家,而没有成为像海明威、福克纳那样的作家,我想这与我独特的童年经历有关。 小说家无论如何千方百计挖空心思搞创新,不管他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确实还应该有一个生活的底子,万丈高楼还是要从平地上建起来,无论多么大的大树,还是要把根扎到泥土里。无论什么样的天才诗人,他的想象力有多么发达丰富,也不可能脱离现实。 ——莫言 莫言曾经在一次演讲中提过:“每个作家都有他成为作家的理由,我自然也不能例外,但我为什么成了一个这样的作家,而没有成为像海明威、福克纳那样的作家,我想这与我独特的童年经历有关。我认为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在今后的岁月里还可以继续从事写作这个职业的理由。” 所谓经历,大致是指一个人在某段时间内、在某个环境里干了一件什么事,并与某些人发生了这样那样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莫言有着自己写作的富矿:高密东北乡。故乡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都是他写作的素材和灵感,而他成长道路上的那些经历、那些故事,更是写作时帮助他腾飞的羽翼。当作家就是为了一天三顿吃饺子 莫言的童年时期,感受最深的大概就是饥饿了。那个时候,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古怪而狂热的时期。一方面是物质极度贫乏,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几乎可以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一方面是人们辛勤的劳作,一方面却是一年到头吃不饱、穿不暖。 “那时,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孩子,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里,基本上是赤身裸体的,只是到了严寒的冬季,才胡乱地穿上一件衣服。那些衣服的破烂程度是今天的中国孩子想象不到的。我相信我奶奶经常教导我的一句话,她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但是没有受不了的罪。我也相信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学说,人在险恶的环境里,也许会焕发出惊人的生命力。不能适应的都死掉了,能够活过来的,都是优良的品种。所以,我大概也是一个优良的品种。那时候我们都有惊人的抗寒能力,连浑身羽毛的小鸟都冻得唧唧乱叫时,我们光着屁股,也没有感到冷得受不了。”(《莫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那时候这些孩子的思想非常单纯,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他们就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中的大街小巷里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许多在今天看来根本不能入口的东西,在当时却成了美味。吃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吃光后,就吃树皮,树皮吃光后,就啃树干。 提起自己的童年经历,莫言说留给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今天看来很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件事: “1961年的春天,我们村子里的小学校里拉来一车亮晶晶的煤块,我们孤陋寡闻,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一个聪明的孩子拿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吃起来,看他吃得香甜的样子,味道肯定很好,于是我们一拥而上,每人抢了一块煤,咯嘣咯嘣吃起来。我感到那煤块愈嚼愈香,味道的确是好极了。看到我们吃得香甜,村子里的大人们也扑上来吃,学校里的校长出来阻止,于是人们就开始哄抢。”(《莫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莫言说,至于煤块吃到肚子里的感觉,已经忘记了,但吃煤时口腔里的感觉和煤的味道,至今还牢记在心。 由于饥饿,莫言还差一点被父亲打死。那还是莫言辍学后的12岁那年,他在一个桥梁工地上当小工,后来给铁匠拉风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铁匠们和石匠们躺在桥洞里休息,因为腹中饥饿难捱,莫言溜到生产队的萝卜地里,拔了一颗红萝卜,正要吃时,被一个贫下中农抓住了。他揍了莫言一顿,拖着他往桥梁工地送。莫言赖着不走,他就十分机智地把莫言脚上那双半新的鞋子剥走,送到工地领导那里。挨到天黑,因为怕丢了鞋子回家挨揍,只有去找领导要鞋。然后,这位领导就发动好几百人,对他进行了批斗,莫言在毛主席像面前,认了错。领导把鞋子还给了莫言,他忐忑不安地回了家,回家后就挨了一顿毒打。后来,这段经历被莫言写进了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 莫言的作家梦想是很早就萌生了的,那时候,他的邻居是一个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下放回家的中学教师。莫言与他在一个生产队,经常一起劳动,在劳动的间隙里,人们饥肠辘辘,胃里泛着酸水,最大的乐趣就是聚集在一起谈论食物。大家把自己曾经吃过的或者是听说过的美食讲出来让大家享受,这是真正的精神会餐。说者津津有味,听者直咽口水。 中学教师说他认识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得了成千上万的稿费。他每天吃三顿饺子,而且还是肥肉馅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那时的人们不相信竟然有富贵到每天都可以吃三顿饺子的人,但大学生用蔑视的口吻说:“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 于是,小时候的莫言从此就知道了,只要当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顿饺子,而且是肥肉馅的。每天吃三顿肥肉馅饺子,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过如此了。从那时起,莫言就下定了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作家。远离故乡,投身军营,续写文学梦 莫言小时候是聪明调皮好动的孩子,因为能说,经常惹出是非。有一次,莫言在课后说,学校是监狱,老师是奴隶主,学生是奴隶。这句话被有心的同学告到了校长那里,学校给了莫言一个警告处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莫言和几个小伙伴成立了“蒺藜战斗队”,并且写出了战斗宣言。后来革命队伍里出了叛徒,老师最后追查下来,查出了小莫言这个幕后黑手,就这样,11岁正读五年级的小莫言辍学回家。辍学后的莫言先是当了一名放牛娃,每天孤独地在田野里游荡,后来割过麦子,当过工地上的小工,挖过河,修过滞洪闸。 1973年,莫言通过在县城棉花加工厂当会计的五叔的关系走后门在厂里当上了季节工。一天能挣1元3角5分钱。这笔工资在当时是“巨款”。莫言的工资要交给生产队一部分,还能在生长队里记工分,什么都不耽误,一个月能剩20多元。在20世纪70年代,20元能买很多东西。 对于这钱的珍惜,莫言在他的中篇小说《白棉花》当中说得很真实: “紧紧地攥住钱,我走出办公室。初次拿到这么多钱,心中充满幸福感。即使是交队里一半,也有五十三元归我所有。我想我应该去买一件蓝咔叽布军便服上衣,买一条灰布裤子,再买双紧口白底青年鞋,最好再配上一双花格尼龙袜子。应该买包香烟,高级一点,‘金叶’或‘玉叶’,每盒两毛九,不要‘勤俭’和‘葵花’,每盒九分钱。还应该买柄牙刷,买管‘白玉’或‘分外香’牙膏,我也要刷牙,像李志高大哥那样,嘴里插着一把牙刷,满嘴吐着白沫,说话呜呜噜噜,显得那么有派头,有文化,有地位,有身份。买了牙膏牙刷,还应该买个红塑料香皂盒,买一块高级的‘罗锅’牌香皂,再配一条花毛巾,洗脸时,一定要用毛巾擦,像电影里那些干部。” 莫言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决心好好干。就这样在棉花加工厂干了三年半,一直没回到村里干活。而这段亲身经历,在莫言的中篇小说《白棉花》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我们欣赏着白色的皮棉像瀑布一样,像连绵不断的白云一样从两只皮辊间倾泻出来,落在皮辊机前的储棉箱里。收皮棉的姑娘推着皮棉车在两排轧花机中间来回奔跑。皮棉车其实是个四四方方的竹编大篓子,篓下安装着四个轴承,跑起来咯咙咙脆响。车间的尽头有一个起重装置。皮棉车推上支架,推皮棉车的姑娘按一下电铃,楼上打包车间的临时工按住刹把,把皮棉车吊上去,皮棉倒在打包箱里,再把空车吊下来。棉花的绒毛是种讨厌的东西,它那么喜欢沾人,往我们的衣服上沾,往我们头发上沾,往我们眉毛睫毛上沾,往我们鼻孔喉咙里钻。它撕不掉,扯不掉,只有用刷子往下刷,用海绵往下擦。走在大街上,它向人们证明我们的身份。” 如果没有这段经历,要想写出这么细腻真切的文字来,几乎不可能。 棉花加工厂的工作经历给了莫言日后创作的灵感,更让他目睹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产生了逃离那片土地的渴望,他再也不愿意回到村里了,他对在地里干活产生了深刻的恐惧和巨大的抵触。在棉花加工厂工作的那段时间,莫言想离开农村的这种愿望越发强烈,他觉得自己一定再不能回到那个村里去了,不能再跟那一帮人混到一起,那里毫无前途,一回去前途就断送了,只能想办法离开那个村,才可能有出路。 莫言的目光,又一次回到了参军这个唯一的出路上。其实这条路,早就堵死了,他从18岁开始,每年都报名参军,每年都被刷下来。在那个年代,参军是乡村青年想得到的最好的出路之一。然而,莫言通过参军而逃离土地的梦想,仍然受制于他的富裕中农身份。 他几乎无路可走了。 要是换成了别人,也许早就放弃了。莫言没有,他要逃离土地的愿望是如此强烈。 1976年,机会来了。征兵时节,恰逢上级发动全县的力量去战天斗地,到昌邑县去挖胶莱河。征兵开始时,为了不影响水利工程进度,上级发文说适龄青年可在工地参加体检,那时莫言在棉花加工厂当临时工,不用去挖河,根据上级精神,可以就地参加体检。就这样,莫言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入伍通知书。莫言用这样的语言描述当时离家入伍的感受: “当我爬上1976年2月16日装运新兵的卡车时,当那些与我同车的小伙子流着眼泪与送行者告别时,我连头也没回。我感到我如一只飞出了牢笼的鸟。我觉得那儿已经没有任何值得我留恋的东西了。我希望汽车开得越快、开得越远越好,最好能开到海角天涯。”(莫言《超越故乡》,见《莫言散文》,第231页)。 当汽车停在一个离高密东北乡只有300华里的军营,带兵的人说到了目的地时,莫言感到了深深的失望。虽说未能实现“天涯海角”的愿望,但毕竟在部队里能吃饱了。新兵莫言也有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在部队好好表现,争取入党提干,不再转业复员回到那片绝望的土地。也就是在部队里,莫言拿起了创作的笔,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真正的作家少不了用亲身经历来编织故事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们自由地运用各自的风格开拓出一片翩翩翱翔的天空,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也是随性自在的。各种各样的创作,绚烂多彩的风格,追根溯源都和作家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密不可分,尤其是童年体验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这种深深烙印在心里的快乐或是痛苦的体会,自然就情不自禁地流露在作家的表达上。 莫言曾说,任何一个作家——真正的作家,都必然地要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编织故事,而情感的经历比身体的经历更为重要。 少年失学、回乡当农民、棉花加工厂当小工、当兵、在部队当文化宣传干事、在报社当记者等,这些漫长而又丰富的生活经历,成为莫言创作的不竭源泉。 莫言《枯河》里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 哥哥拖着他往家走。他的脚后跟划着坚硬的地面。走了很久,还没有走出白杨树的影子。鸦鹊飞掠而过的阴影像绒毛一样扫着他的脸。 哥哥把他扔在院子里,对准他的屁股用力踢了一脚,喊道:“起来!你专门给家里闯祸!”他躺在地上不肯动,哥哥很有力地连续踢着他的屁股,说:“滚起来!你作了孽还有了功啦是不?” 他奇迹般地站了起来,一步步倒退到墙角下去,站定后,惊恐地看着瘦长的哥哥。 哥哥愤怒地对母亲说:“砸死他算了,留着也是个祸害。本来我今年还有希望去当个兵,这下子全完了。” 他悲哀地看着母亲,母亲从来没有打过他。母亲流着泪走过来,他委屈地叫了一声娘,眼泪鼻涕一齐流了出来。 母亲却凶狠地骂:“鳖蛋!你还哭?还挺冤?打死你也不解恨!”母亲戴着铜顶针的手狠狠地抽到他的耳门子上。他干嚎了一声。不像人能发出的声音使母亲愣了一下,她弯腰从草垛上抽出一根干棉花柴,对着他没鼻子没眼地抽着,棉花柴哗啷哗啷地响着,吓得墙头上的麻雀像子弹一样射进暮色里去。他把身体使劲倚在墙下,看着棉花柴在眼前划出的红色弧线…… 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细腻、真切、精彩的场面和感觉描述,还源于上文提到的“莫言上小学时,由于说学校是监狱,老师是奴隶主,最后挨了一个警告处分”的经历。挨处分后,莫言怕家里人知道,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看到父亲的一个眼神不对,就猜疑,是不是知道了?看到老师和父亲在路上打招呼就害怕,看到姐姐们一起到学校玩耍就紧张,看到堂姐跟奶奶、爷爷多说话就怀疑。 村里一个姓薛的滑稽的老光棍经常到学校南墙晒太阳,知道了学校发生的大小事情。他对莫言的父亲说,你儿子了不得,在学校造反,还得了一“特等奖励”。父亲回来质问,把绳子浸到咸菜缸里要打,莫言说再打就去跳河。如果没有这段经历,莫言绝对不会把《枯河》写得有声有色,感人至深。莫言的小说多取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 创作理论强调:创作的源泉来自生活,也就是说生活是作文的源泉。而莫言生活道路上丰富的经历,成了他独到的文学富矿,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他的童年经验、乡村经验、左邻右舍、父母兄弟,乃至村东头的一个池塘,村头的一棵大树,田野里所有的动物、植物全都变成了莫言笔下写作的素材。提笔写作时,这些素材就变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源泉。

莫言最早的几部小说像《大风》《石磨》《透明的红萝卜》都是调动了他的童年记忆,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也获得了文坛的肯定。以后的作品像《四十一炮》《生死疲劳》里面都有一个“莫言”在不断说话。这些作品里的儿童形象,既是莫言童年的写照,也是一种文学创作。 莫言在短篇小说《大风》里提到了爷爷,和生活中的爷爷近似。爷爷排行老二,很有性格,有远见,也很清高。他性格沉稳、仗义疏财、乐善好施,是当地有名的老把式,农活样样出色,尤其是割麦子在高密东北乡方圆几十里地鼎鼎大名,是个高手。爷爷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木匠。后来莫言在《大风》中写到了爷爷割麦子的潇洒姿态,就是源于真实的生活经历。 在获得茅盾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蛙》中,有一段妻子流产的故事,也取自莫言的亲身经历。莫言大哥家两个儿子,二哥家一男一女,莫言姐姐连续生了三个女儿,第四胎生了一男一女双胞胎,莫言妻子杜勤兰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户口还在农村,按政策讲,他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间隔几年后可以再要一个。当莫言刚刚调到北京时,妻子怀孕了。 那时的莫言刚刚提干入党,文学道路一帆风顺,领导也很器重他,在单位领导出马劝说后,后来莫言只有答应不要孩子。他回到山东老家做老婆的工作,跟老婆举例说:“我同学在当地县里工作,无论是工人、教师,还是局长、处长,大家都是一个孩子,很多人只有女儿。”妻子杜勤兰想要这个孩子,但迫于形势最终流产了。 就是这段经历,让莫言常常反思,莫言说自己的写作立场一直是写人,而写人必然要敢于面对自己,解剖自己灵魂深处的东西,带着对生命的尊重和赎罪意识,莫言把这段经历写进了《蛙》。 旧时的大家庭中,母亲大概是最没有地位的人了,上有公婆,下有子女,除了忍饥挨饿,还要频繁承受生育之苦。莫言的母亲总共生育了六胎七个子女,但活下来的却只有四个。母亲曾经告诉莫言,自己怀过一对双胞胎,那时候肚子大得自己都望不到自己的脚,但还要顶着烈日下地干活。到生产那天,中午还在麦场打麦子,直到羊水浸湿了脚才被允许回家,下午生产,晚上赶上暴雨,又要挣扎着去麦场抢收麦子。双胞胎没活几天就死了,母亲落下了一辈子的妇科疾病。就是这段听来的间接经历,莫言把他写进了50万字的《丰乳肥臀》。 莫言曾自述:“我的长处就是对大自然和动植物的敏感,对生命丰富的感受,比如我能嗅到别人嗅不到的气味,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发现比人家更加丰富的色彩。”或许这得益于他童年孤寂而又艰苦的生活历练。 评论家赵园曾这样评价莫言:一旦感觉与表达相契,那支笔就触处生新,使得成熟的事物亦如被闪电照亮般神异起来。这种特异功能也使得他的作品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恣意遨游在幻真幻假的世界里。这样的特异功能,其实都来自莫言非凡的人生经历。莫言的创作经历也告诉我们,有丰富的生活经历不一定能成为作家,但成为优秀作家一定要有丰富的生活经历。 作家是生活中的人,作家融合自己所思、所感、所知、所见、所写,参与到创作活动中,作家的经历则是丰富生命本身的过程,并且不断地为作家的创作添枝加叶,成为源源不断的泉源。更加可贵的是,这种记忆深处的感触,这种存在心灵和脑海深处的记忆,会随着作家的成长而越来越丰富,随着作家一次次的回忆重温而更新。如果我们想拥有一支生花妙笔,整日躲在书房中闭门造车是行不通的,唯有走出家门,走入社会,走进大自然,多给自己增加一些生活的经历和体验,才能写出富有生活气息的文章。 美文点击 “打死你也不解恨!杂种。真是无冤无仇不结父子。”父亲悲哀地说着。说话时手也不停,打薄了的鞋底子与他黏糊糊的脊背接触着,发出越来越响亮的声音。他愤怒得不可忍受,心脏像铁砣子一样僵硬。他产生了一种说话的欲望,这欲望随着父亲的敲击,变得愈加强烈,他听到自己声嘶力竭地喊道:“狗屎!” 父亲怔住了,鞋子无声地落在地上。他看到父亲满眼都是绿色的眼泪,脖子上的血管像绿虫子一样蠕动着。他咬牙切齿地对着父亲又喊叫:“臭狗屎!”父亲低沉地呜噜了一声,从房檐下摘下一根僵硬的麻绳子,放进咸菜缸里的盐水里泡了泡,小心翼翼地提出来,胳膊撑开去,绳子淅淅沥沥地滴着浊水。 “把他的裤子剥下来!”父亲对着哥哥说。哥哥浑身颤抖着,从一大道苍黄的阳光中游了过来。在他面前,哥哥站定,不敢看他的眼睛却看着父亲的眼睛,喃喃地说:“爹,还是不剥吧……”父亲果断地一挥手,说:“剥,别打破裤子。”哥哥的目光迅速地掠过他凝固了的脸和鱼刺般的胸脯,直直地盯着他那条裤头。哥哥弯下腰。他觉得大腿间一阵冰冷,裤头像云朵样落下去,垫在了脚底下。哥哥捏住他的左脚脖子,把裤头的一半扯出来,又捏住他的右脚脖子,把整个裤头扯走。他感到自己的一层皮被剥走了,望着哥哥畏畏缩缩地倒退着的影子,他又一次高喊:“臭狗屎!” 父亲挥起绳子。绳子在空中弯弯曲曲地飞舞着,接近他屁股时,则猛然绷直,同时发出清脆的响声。他哼了一声,那句骂惯了的话又从牙缝里挤出来。父亲连续抽了他四十绳子,他连叫四十句。最后一下,绳子落在他的屁股上时,没有绷直,弯弯曲曲,有气无力;他的叫声也弯弯曲曲,有气无力,很像痛苦的呻吟。父亲把变了色的绳子扔在地上,气喘吁吁地进了屋。母亲和哥哥也进了屋。 ——《枯河》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