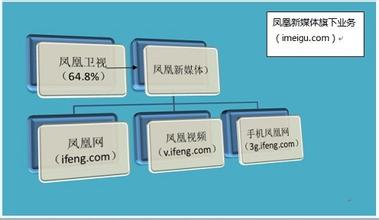刘长乐何许人也?
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以其传媒人和商人的双重智慧,在华人社会构建了一个东西方文化兼济的媒体特区,在将华语电视推向世界的破冰之旅中,成功打造出覆盖亚太、欧美九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传媒品牌,在政策与市场的平衡木上长袖善舞,调和两岸三地华语电视精英,以华人的视点关照世界的变幻。
这是注释刘长乐的一个标准答案。
当然,有标准的,就有不够标准的,那些流传于民间的关于刘长乐的称呼,比如“传媒智者”、“企业领袖”、“佛商”、“和商”、“憨商”等等,无不透露出人们对这位浑身散发着内敛、神秘气质的“大佛”的浓厚兴趣和关注。
1995年春夏之交,北京颐和园就要闭园的时候,一艘可容纳200人的巨型龙船悄然驶出,停泊在昆明湖的中央。船上只有不足十人,刘长乐、戴格里(默多克的谋臣,时任星空卫视行政总裁)、洛克里·默多克(默多克长子)、崔强(现任凤凰卫视常务副行政总裁)、王纪言(现任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兼中文台台长)、余统浩(时任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现任亚洲电视营运总裁)等催生凤凰卫视的关键人物徜徉在优美的湖光山色之中。可是,长乐之意不在山水,乃在凤凰也。
微风拂面,船上的人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剑拔弩张的氛围,但所有的人心知肚明:此次谈判涉及的股权分配问题直指合作要害。刘长乐意气风发,整个过程他说话最多,仔细一听,却发现他是在为戴格里讲解颐和园的历史和掌故。古人说,胸中自有百万兵,又说,学富五车。这是极言人的胸怀之大,肚子里的东西多得车载斗量,这些故事让戴格里听得眉飞色舞,无形中为双方最后的签约加上了一颗含金量十足的砝码。
不知何时,月牙悬空,凤凰卫视呼之欲出。
1996年3月31日,一个将载入史册的日子——凤凰卫视开播。开台酒会就在演播大厅举行,高脚杯里斟满了酒,大家怀着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紧盯着同一个方向——荧屏,等待着凤凰台标的出现。
刘长乐说,当时有两个感觉,一个是如释重负,另一个是百感交集。

有诗为证:不忘那一年,天上布满星,凤凰卫视开大会,我们开播了。忆昔八年前,相互不认识,偷偷看两眼,各自想心思。
耳闻刘长乐:背景复杂,交际广泛;当兵出身,做过记者;下海掘金,身价上亿;面相慈善,笃信佛教,人称“刘老板”。
眼前刘长乐:一身红装,身材健硕,大大眼镜,眯眯细眼,印堂发亮,耳垂面方,嗓音浑厚,彬彬有礼,好一个“刘老板”。
2004年7月中旬,北京的天气酷热难耐,刘长乐特意从香港飞来北京,为“海若工作室”的成立加油助阵。在逗留北京的两天内,他接受了《人物》杂志的独家专访。走进刘长乐的“凤巢”——位于北京东城的紫金宾馆,庄重、静谧、幽雅之气扑面而来,上世纪30年代的老楼在庭院深深中诉说着历史的沧桑,高阔屋穹的欧式阁楼在中国传统的红木家具与雕花镂空的饰品的点缀下别有一番韵味。
彼此寒暄落座,一身红装、脚蹬布鞋的他在众人当中格外抢眼,我正惊讶于他的休闲品味,刘长乐仿佛看透我的意念,“我刚从昌平打球回来”,随后补充了一句,“堵车呀,车在环岛那儿一动不动。”我知道他是在为我们长时间的等待而表示歉意,其实他在我们一进门时就道歉了。
从1996年至2004年,凤凰卫视剑走偏锋、锐意创新。
八年辛苦不寻常。这个只有 “县级规模”(余秋雨语,言指其办公条件的简陋和人员的精练)的电视台,八年来以“向世界发出华人媒体的声音”、“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构建两岸三地桥梁”为目标,在没有路的地方杀出一条血路,取得了成功。在海外,1999年,凤凰欧洲台进入欧洲主流卫星电视SKY DIGITAL以及英、法、德、荷四国有线电视网;2001年,凤凰美洲台开播,通过美国两大直播卫星网平台DIRECT TV和ECHOSTAR,将节目传送给北美观众;在亚洲,凤凰已进入新加坡有线电视网和马来西亚最大收费电视公司,用户已由开播时的25万增至目前的50万。《洛杉矶时报》2003年9月1日报道说,不少北京人买新房时都会问:“你们这里能看凤凰卫视吗?”
刘长乐,这个一手缔造凤凰神话的幕后传奇人物。伴随着凤凰卫视“拉近全球华人之间距离”的使命的传播,刘长乐在全球华人圈内声名鹊起。然而,关于刘长乐本人角色的准确定位,却一直颇有争议。
如果不做凤凰卫视,刘长乐的资产也绝对令人咋舌——据说个人总资产有数十亿人民币(刘老板没有承认这个数字)。上个世纪顶礼膜拜财富,于是善于创造和积累财富的人们当仁不让地成为社会追捧和学习的楷模。这个世纪注定是一个文化传播的强势时代,于是一批在媒体资本的大潮中耍弄刀枪的领袖借助传媒开始诠释声望的定义。刘长乐在世纪交接之际完成了从财富积累到声望传播的过渡,现在他的精力“99.9%都放在凤凰卫视上”(凤凰卫视公关总监王多多语)。
对许多人而言,凤凰成功的原因以及神秘老板刘长乐好像一个个巨大的谜团,人们啧啧慨叹,“凤凰的秘密在哪里?”
解密凤凰之一:传媒人的乐趣
我是有点儿“癖”——对凤凰的追求和爱好。心力的付出这方面是心甘情愿的,自讨苦吃,而且还苦中作乐。——刘长乐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节目中,净空法师问大家,“现在的世界什么东西对人的影响最大?”会众一片静默,净空法师说,有两种人对人的影响最大,一种是政治家,另外一种就是传媒人。
后来不知从哪家媒体开始流传,说这句话是刘长乐语录。他告诉《人物》杂志,“这绝对不是我说的,是净空法师说的。”
53岁的刘长乐10年从戎、10年握笔、10年“下海”,先后在中国内地、新加坡、香港、美国等地投资房地产及石油贸易等项目,干一行成一行,是商界有名的“智多星”。
刘长乐自言名字后面挂了一大堆董事长的头衔。然而,在送给记者的名片上,名字下方却只写着“凤凰卫视主席及行政总裁”, 名字后面的称呼则是“太平绅士”。
生意的成功让刘长乐成为一个财富人物,他过人的机智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对时局的把握和商业手段的运用上;作为一个老媒体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0年的记者经历,使他深谙媒介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将要释放的能力和威力,特别是在华语电视媒体领域,刘长乐敏锐地看到了商机。他几乎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在英语一统天下的媒体事业中打造出一个华语的天空,我多年的积累正是为了实现这样一个运作。”在市场需求、时代需求和受众需求的背景下,“华语电视媒体不应该是个空白,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仅仅是叹息!”
这时的刘长乐已经渐渐从其他企业的日常行政管理中淡出,而把大部分精力放到了他喜欢的凤凰卫视上。“我很喜欢在凤凰卫视这样的媒体里出力”,他说。凤凰管理层至今还在谈论老板当年的那一段“痴人说梦”:“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所谓梦一定不能是现实的翻版,它一定是天马行空,但绝不是空浮缥缈。梦,不光是鸟语花香,也会有刀光剑影,……我作为老传媒人,就是给一切有识之士提供一个做梦的舞台,给你一个发挥造梦潜能的空间——这,就是凤凰卫视。”
就是这番梦话,把几十个三四十岁的壮年人说得痒痒之极,毅然远离在大陆的妻子儿女到香港创业,过着不是单身的单身生活。而刘长乐也和所有的单身汉一样,他曾利用周末,身挂两部相机,亲自驾车拉大家到郊外去放松。据说这位公司的最高首脑喜摄影、会乐器、爱唱歌,和同伴一起出去玩时,俨然就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郎。
对凤凰,刘长乐撒下了激情,种下了智慧,也播下了技巧。1999年的凤凰卫视正在摆脱初期城市青年台的定位,准备迈向全新的资讯类方向。那时的刘长乐在焦急地观望:新闻是他的理想,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新闻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以及对于凤凰卫视中文台未来的重要性。
凤凰卫视由娱乐走向新闻,表面上更像是迫于“形势”。他们最早接触新闻是1997年,那一年,有两件大事改变了世界与中国的格局: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凤凰卫视此前于1月份在亚太地区首播了一部12集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2月19日,邓小平去世,此时若播放娱乐节目显然不合适,中国人需要更多地了解邓小平去世后海外对于中国的看法与立场。刘长乐抓住了这个机会,从当天始至2月26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连续7天用直播方式报道了内地及香港人士悼念邓小平的情况,其正面的评价与客观真实的立场,成为凤凰卫视转型的一个开始。
考虑到7月份的香港回归,刘长乐觉得有越来越多的资讯性的内容需要一个栏目进行包容,于是,《时事直通车》应运而生,这是刘长乐起的名字。在整个6、7月份,凤凰卫视在香港回归的报道中出尽风头,尤其是在“七一回归”的交接仪式高潮中。他们利用公共信号资源进行“现场文摘”,分阶段利用电视超越时空的力量,以香港交接仪式为主画面,北京天安门广场群众在倒计时牌前的情景和凤凰台主持人为分割画面,让观众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有了更多的关联感受。这三个信号渠道,只有主持人一方是凤凰卫视自己现场拍摄的,其他则全部借助他人的“公共信号”。
这是刘长乐一贯强调的“借船出海”、“乘风行船”理念的绝佳体现。
此后,“中国可以说不”专题、“‘9·11’美国遇袭”专题、“台湾‘大选’”专题、“伊拉克战争”专题等,愈来愈彰显出凤凰的大台气象和风范。有评论曰:“凤凰卫视在华语世界中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资讯传播与评论带,这个评论带显然正改变着中国的新闻格局。”
历史,就这样走来,走过了创业之初边缘媒体的尴尬,上升至华语电视媒体的主流,个中滋味,刘长乐体会最多:“我觉得一个媒体做到了对社会的发展、进步及人们的生活有相当的影响,这种影响你能体察到、感受到,这是一种乐趣。如果你做媒体,别人反对你,没有注意到你,落地无声,那你肯定很痛苦。”
还有什么生意能像传媒这样在民众中间产生层层涟漪?还有什么生意能像传媒这样打造出一个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品牌人物?
刘长乐回答问题非常工巧、机敏,他一会儿把凤凰卫视的大动作喻为“掷地有声”,一会儿又用“一石激起千层浪”来形容。无论是“掷地”还是“激浪”,刘长乐渴望的都是回音,是来自受众的关注。“拥有这种喜悦时,任何疲劳、任何打击、任何压力你都会觉得它无所谓了。”
比如“锵锵三人行”,刘长乐说凤凰管理层多次讨论过该节目要不要“下课”的问题,因为这个节目已经做了七年,是凤凰台最老的节目,几乎赶上“老友记”了。可是很多观众写信,说没有这个节目就活不下去,这个节目成了观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乐趣。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