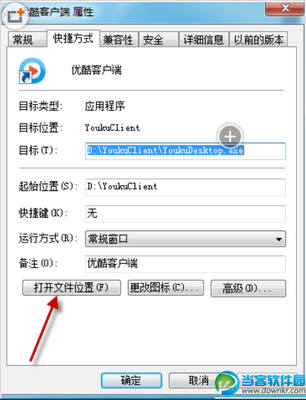江苏太仓。李伟龙一坐下来窗外就变了天,瓢泼大雨像是刻意要困得谁无路可觅。好在我们有话要谈。这时距离他回国还不满7个月,他34岁,此前的10年让别人称自己作William Li。在那条从纽约曼哈顿区南部百老汇路延伸到东河的、百年来引领世界金融业起落的华尔街上,他是30万名肤色各异、神情却一致漠然的金融从业者中的一员,每天出入于冰凉的银行旋转门,为搅动全球金融运势贡献自己微薄的光和热。
但他现在表情生动,说话时还辅以手势。2009年2月,他已辞掉摩根大通高级经理的职位打道回国,变回常熟人李伟龙,在当初离开的土地上重构自己的未来。“回到起点。”李说,语速快且确定,听不出迷惘。 他是个归客,上一站华尔街。也是在过去30年近140万中国留学生里,进入工程和金融领域的绝大部分中的一个。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华尔街对人才的吞吐能力极大降低,而中国却发出难以抗拒的召唤热情。一时间过江名士多于鲫,金融大江的彼岸是欧美,此岸是中国。 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与金融机构们已经把对华尔街人才的抄底付诸行动。去年12月,上海政府带队的一个金融招聘团从欧美运回来的简历重达300多斤。招聘团前往纽约、芝加哥和伦敦,海通证券、东方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和申银万国证券都位列其中,意在招揽首席经济学家、风险管理专家、合规管理专家、股权投资总监等岗位的人才,其中最高年薪开到了120万元人民币。同在2008年底,中国中央政府层面还出台了大规模引进境外高端人才的“千人计划”。 但在回国的半年多里,李伟龙们已经发现了水土不服的尴尬:中国本土的金融业虽然前景光明,但目前仍处于原生品主导阶段,他们所掌握的更超前的金融衍生品经验全无发挥空间,外语技能也不太有应用余地。在与我们碰面前两个星期,李伟龙从工作了不到半年的南京一家本土私募股权基金里再次辞职,准备另觅工作。 严格来说,李伟龙算不上被中资金融机构们青睐有加的幸运儿。中资机构希望趁这轮美国金融颓势,挖到的精英是在华尔街有10年以上工作经历、拿超过30万美元年薪的华人高管,他们的脑子里装满了成熟发达的金融业知识与技能,又深谙中国市场文化,外可应对QDII、国际业务,内可协助提升管理经验。 确实有这群人。“在华尔街,在像高盛、雷曼、JP摩根这类大公司里的董事、总经理级别的华人高管有二三百人。中国人进入华尔街是15年前,这15年间,中国留学生留美有几十万人,真正进入美国金融系统,在跟美国人竞争当中留下来的大概有300多人,这等于也是中国的人才库。”华尔街人协会的组织者、梅隆银行投资组合经理(portfolio manager)陈讯勇告诉《中国企业家》,“他们的专长几乎涵盖了华尔街金融的各个领域:对冲、风险、新兴市场、外币、不良资产处理、研究、固定资产、股票、股权……这些也是中国以后要发展的。”陈讯勇所说的二三百人就在华尔街人协会里。这个协会相当于一个俱乐部性质的华人人脉圈,建立5年以来,已经聚合了华尔街金融机构里的254位华人总经理、董事级别的高管。危机发生以来,去年11月,陈讯勇曾经带着这200多位会员的简历回国走访了政府部门、监管机构、银行、股权交易所、产权交易所,开始未雨绸缪地为华人金融家们做前期铺垫。 “中端人才回来比较多,高端人才回来比较困难。”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告诉记者。陈讯勇所描述的这一群的精英们并不愁工作难觅,另外考虑到家庭等各种因素,他们真正有回国行动的非常少。李伟龙不在此列。更不巧的是,他还正是华尔街自顾不暇时最容易被放弃的一群:资历尚浅,又是外籍。“美国人之间容易沟通,中国人和老美搞关系难搞些。很明显的事。想像一下你是小组的头。”李说。

1998年从南京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李伟龙前往密歇根理工大学读计算机硕士。他在硅谷只工作了两年就赶上互联网泡沫(所以,这是一个接连撞上两次大危机的人呢),决定改行,于是2003年去卡耐基梅隆大学读MBA。抛除实习经历,李的正式华尔街生涯始于2005年9月,德意志银行的衍生品风险管理部门。作为一个在中台分析和管理产品风险的新人,他在德银的收入底薪约在10万美元左右,并在年底另获得相当于底薪60%-70%的分红。 他羡慕前台经纪人的丰厚收入。“他们的底薪跟我们差不多,”李说,“有一两年工作经验的,本科生底薪六七万,MBA一般8万到15万之间。前台的分红肯定大于底薪,年景好的话,最多拿几十倍底薪都有。” 2007年6月,李伟龙发现当年升职无望,意气之下从德意志银行跳槽到了贝尔斯登,在这家有80多年历史的投行老店里任固定收益衍生品发行和交易部门副总裁(Vice Precident),负责产品的设计和风险评估。贝尔斯登向他保证,他的收入将至少是德银时期的2倍。 “(华尔街)这个文化决定了大多数人都是想往前台走,我当时去贝尔斯登就是往前台转。刚进去也是相当于高级经理,后来成为VP。如果干满八年十年,底薪可能在20多万,分红绝对是更多。贝尔斯登当时15000个人,其中顶尖的1000个平均每人能拿到250万美元。”李说这话时望向窗外,但眼里已经没有憧憬。 没有八年十年可以磨了,谁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李伟龙刚进去没几天,贝尔斯登旗下两只投资次级债产品的基金倒闭,总共损失逾15亿美元。置身于贝尔斯登内部,李所能触及到的真实财务状况也极为有限。他跟同事们一样看新闻,一样聊基金经理人的个人冒进,偶尔在公司大会里听到CEO底气不足的宽慰并信以为真,一样为2007年底的贝尔斯登与中信证券互换股权的计划兴奋,直到最后一刻。 在为期两个月的吸并过程里,摩根大通将1.5万名贝尔斯登员工裁掉了6000人。由于李所在的固定收益衍生品发行和交易部门的技术与经验都胜过摩根大通的自有部门,李的职位得以保全,但是也被从VP降职成高级经理。 贝尔斯登许诺的2倍收入没戏了。不但如此,分红看起来也要泡汤。“我们没降薪,但分红是没有了。只拿一个底薪,跟出租车司机一年也差不多。”李说,纽约出租车司机一年也能挣八九万美元。同时他发现,成为金融风暴的导火索后,自己所擅长的衍生品市场在整个美国也正高速衰竭。“这件事一发生这个领域(衍生品)就完了,再回来至少得5年。” 沮丧心情下,从3月宣布被接管到5月底完成合并,闲得无聊的李伟龙和同事们在办公室打了两个月的游戏,期间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与中国的猎头联系,投递简历。随后,也逐渐接触一些来自中国国内的招聘团。 另一边,美国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接下来的一年里,整个华尔街裁掉了十多万人。美国的失业率从2008年初的4.9%激升,到2009年7月已经达到9.4%——激进的观点甚至称,如果把放弃求职以及临时工人计算在内,这个数字应该是16.3%,失业人口总计1450万人。 2008年10月,李伟龙在全美华人金融协会(TCFA)年会遇到自己在香港与深圳工作的大学同学。“我本想在华尔街多干两年,累积些经验。但他们告诉我没必要在这儿留着。”看到几个同学的状态都还不错,李伟龙坚定了回国决心。 但在与国内金融机构的接触过程中,李发现了落差所在:到华尔街来的华夏、嘉实、南方等共同基金,都是希望挖到做股票的人才,但在华尔街做股票的人非常少,更多的是股票之外的金融衍生品人才。“这是矛盾所在,擅长和需求不同。” 综合权衡后,虽然尚未确定工作,今年2月,李伟龙辞职回国。几经面试,进入海融投资做投资总监。 “应该没有什么(不能适应的),其他人能干的我也能干。”李伟龙说。但他错了。进入海融投资后,他所擅长的固定收益具体债券化产品学识和英文都派不上用场。他的职责变成更基本的尽职调查、撰写报告以及陪着合伙人去走访公司。去拜访一些本地企业时,他需要乘坐公交车前往。如果下班忘记关灯,还会受到老板责备。“在华尔街,灯都是智能的。”李承认,中式的管理方式让他感到不适。只在海融投资呆了5个月,李选择了离开。 这会是华尔街归客们的普遍尴尬吗?科锐国际金融行业资深猎头顾问宫宇告诉记者,金融危机发生后,科锐随即在《华尔街日报》登了广告,随后收到两三百份简历。但引荐回来的人,大多因为薪酬、待遇、管理方式乃至人际交往上的不适应,又回了美国。至今为止,科锐为中国引进的华尔街人才成功案例只有一两个,还是在国内也已经起步的财富管理领域。 “很多东西在中国还是个起步阶段,适应起来不能说很容易,回来有个适应期是很正常,公司在适应期也可以看看这个人怎么样,再给予一个适合的位置。”陈讯勇认为,即便是专长与需求匹配,华尔街归客们的适应期也需要半年到一年,但不能因此否定他们的优秀。“既然你从国内最好的大学出来,在美国也是最好的大学,又能自己在华尔街找份工作,从全球最好的金融公司,从助理变成董事、副总裁、董事总经理,背后的能力不是可以数量化衡量的。在华尔街,不但是跟美国人拼,也是和世界在拼。华尔街总共就业人口30万,你是在和30万国际上比较优秀的人竞争下来的结果。” 李伟龙的新目标地是上海。在他看来,上海离自己家近,金融环境在国内已经算是完备。他希望新的工作可以让自己发挥在固定收益上的专长,另外,年薪在三四十万元。但他自己也知道,“现在问题是国内做固定收益的工作不多”。 “假如上海没有合适的,可能也会考虑香港,远的地方也不会再去了。”无论如何,李伟龙不想再回美国。 不过,华尔街似乎正在缓过劲来。今年上半年,高盛从上半年营收里拿出114亿美元支付员工薪资,瑞银集团则将银行家薪酬提高一半,就连上半年业绩锐减40%的摩根士丹利,也不惜拿出营收的72%来支付员工薪酬。 “那都是赚钱的部门,衍生品部门不会再有分红了。”李伟龙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强化决心。“衍生品部门不会。”也许他是对的。在吸并了贝尔斯登的摩根大通里,得到平均37%加薪的员工来自投资银行部。 那么接下来,中国市场能给他多少,他又能给中国市场多少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