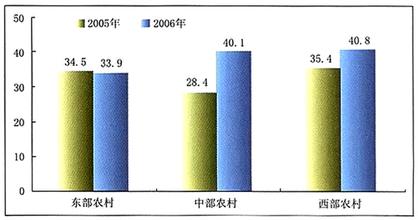“改革开放后,第一个10年,是香港人到广东搞投资;第二个10年,是台湾人到上海投资;第三个10年,是五百强企业到中国投资;第四个10年,则是全球资本到中国投资,卖奢侈品。我们已经站到第四个10年的门口,现在的图景只是预演。全球的资本管理人都要把旗子插到中国来,不到中国募集资金管理资金,你就与未来的成长无缘。这是我总结的,未来10年制高点就在中国,很快中国资本市场的交易量就排第一了。” 天敌与食物 40岁的朱平刚刚经历了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日子。坐在广发基金33层的大会议室里,他穿着考究的西装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像位大学老师。窗外是浩荡南去的珠江。 朱平1996年进入广发证券,现任广发基金副总经理,主管投资;他曾担任易方达科汇基金经理,广发基金投资总监。2007年广发基金公司获得明星基金公司、基金客户明星、3年期持续回报明星、平衡型明星基金、大基金明星等5大奖项。 在不到两年里,广发基金完成了一次过山车般的波动,管理的资产总额在2007年最高超过1400亿元,然后下降到2008年底的700亿元,现在重新回到了1000亿元。这也是公募基金的普遍状况。 “‘突然’是投资的外在表现,就像昨天的大跌一样,谁会料到跌得那么深,但是想想也合理,总这么涨也不对。”朱平告诉本刊记者,“世界的真相就是‘突然’,只不过,反映在投资市场上要比生活中剧烈得多。”朱平引用了索罗斯的名言,“投资者就像丛林里的动物,你不知道下一步会碰见天敌还是猎物,你要时刻保持警惕”。 “去年是最难受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投资的机会。我们曾认为经济不会变得很差,虽然实际上现在也是这样,但当时市场并不这么看。去年是熬过来的,投资者亏钱,我们的心里肯定不好受。”朱平说。 指数重上3000点,是朱平年初时不曾想到的情况,“年初的时候,我们认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经济要复苏了。但复苏的路径并不知道,程度不也不能肯定”。2008年,银行信贷的大量出笼推动了股市的第一波上涨,这种涨势在春节后继续加速。当指数上涨到2400~2500点时,朱平意识到形势变了,“复苏的速度比大家想象的快很多,市场开始预期,去年的金融危机实际并不严重,全球经济都会反转。4月份之前,没有人敢说出这个判断”。 朱平认为,如果全球V形反转的预期成立,那么反转的核心一定是中国,这又是一次全面性的机会。于是,周期性的股票开始进入基金经理的选股名单,投资就是一场战争,要赶在市场反应之前占领阵地。 两个月前,朱平给一家上市钢铁公司打电话,询问产量是否打满。对方很疑惑地说,产量虽然满负荷,但公司盈亏刚刚打平。朱平开始大量买入钢铁股,“我们预期钢铁一定会提价”。到6月底,钢铁企业开始赚钱,7月份赚了更多的钱,股票也应声而涨。与此同时,基金公司开始介入煤炭股,研究员们把每一家煤炭企业的产品、产能、成本情况的报告送到基金经理的案头。在键盘的敲打声中,汇聚成推动煤炭股暴涨的资本暗流。 “V形反转的前提条件是,去年的危机并不深。去年大宗商品市场泡沫崩溃,形成全球企业去库存运动,全在卖东西,没有人买东西,致使全球经济像自由落体一样下降。完成去库存后,大家发现金融危机也就如此,危机的伤害并不深。尽管反转只是一种预期,但市场先于实体经济做出反应。”朱平说。 在这一波反行情中,李驰选择了金融股。他是一家著名私募基金——同威资本的董事总经理。 “如果不是签证的时间迟了,我现在应该在新西兰滑雪。”李驰对本刊记者说。窗外,正是烈日炎炎,中午的深圳就像一个大火炉。2007年8月,在牛市5000点的时候,李驰将股票清盘,他先是和朋友们去新疆玩了一个月,然后又去了非洲、南极。作为私募基金经理,他比公募的同行们享有更多的自由。接受采访时,李驰穿着黑色麻布上衣,像个江湖大哥。 “去年,有媒体说我是最潇洒的投资人。其实,你们是回头看我潇洒,当时看我多‘愚蠢’。”李驰说,“2007年8月份我卖掉股票,后面5个月一声都不敢吭。市场又涨了两个月,不断创新高,上涨了1000点。看看去年8月份以后我博客上的评论,都认为我是多么‘愚蠢’。实际上,后面5个月股市都在5000点以上晃悠。” 股市涨到5000点已经接近了李驰所能接受的极限了,万科已经赚了10倍,招商银行也赚了5倍。他选择了清仓等待。 2008年,李驰通过信托公司发行了3只信托产品,其中最早的一只“新华同威一号”就募集了2.37亿元。股市下跌到2700点后,李驰重新杀回股市。越跌越买,到指数回到2000点左右完成建仓,“建仓的时候市场还在下跌中,我就说我是阿Q;接着跌,我就说我在做善事。我找出各种理由买,不涨我就等着。我的一句口头禅是:等待是价值投资精髓。好东西,迟早有人像疯子一样来抢。”今年初,他写了篇文章,认为目前是35年来最好的机会。 在A股市场,李驰买入了招商银行和中国平安,他的想法很简单:“在2000点左右的时候,这两只股票都比香港的H股便宜。同股同权,假定香港人不笨,那就是我们蠢。难道他们不知道招商投资永隆银行的故事么?没有听说平安投资富通200亿打水漂的故事么?那么,为什么全球投资人都愿意用更高的价格购买这两家公司?我们假设市场是有效的,那么错误就一定不会延续太久,市场其实永远在不断纠错的运动中,所以我配置了这两只股票。”李驰说,“所以现在国内证券市场形容起来尽管不好听,但确实如此,就是6个字:人傻、钱多、快来。赚钱的秘密是可以公开的,就是买便宜货,但不是便宜没好货的那种便宜货”。 李驰在去年3月4000点时发行的第一只信托基金现在已经获得了44%的收益,去年8月8日发行的第二0信托产品在分红后也获得近50%的收益,都跑赢了指数。 2700点以后,李驰没有沽出过股票,“冷清的时候,买也对,不买也对,卖是错;热闹的时候,卖也对,不卖也对,买是错。现在应该算是热闹的时候了”。 各自出发 李驰与朱平都生于上世纪60年代,同为浙江大学的校友。对于这代人来说,资本市场是一个新奇而充满诱惑的地方。 1988年,李驰从浙江大学力学系研究生毕业,专业是流体力学,与航空航天关系最近。1989年,他南下深圳特区,先后任职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园、中国宝安集团、深业集团和香港怡东国际财务投资有限公司。 刚到深圳的时候,李驰在蛇口上一个为期3个月的培训班。学校的门口有人摆了张桌子,卖深圳安达公司(深圳老五股,现ST国农)的股票,100块钱一张。他发现,好多人买了之后,一两个月涨到了107~108块钱,就卖掉,认为很好赚钱,殊不知后来这张“纸”涨到了3000块,上涨近30倍。“1990年,我上了投资原始股的一课。”李驰说。 他还目睹了另一家中字头的企业来深圳创业的“奇迹”,投入300万元买了“深原野”的股票,同样涨了近30多倍,变成了1亿元。但这家公司最终仍然以关门告终。“从概率上说,绝大多数投机没有好下场。” 90年代的深圳,财富就像沙子,被风吹来又吹走。暴富与破产的神话轮番上演。李驰真正进场炒股票,是在1992年之后,1993年股市正是热闹,“我们当年进场,和2007年进场的人没有区别”。 “1997年有一家中资公司,1块多钱上市,第一天涨到了3块钱,后来又涨到了13块。该公司董事长告诉当时一家银行董事长的夫人,说我们的股票还能涨,她12块多进入,一年的时间最后跌到了1块多。那只股票我也在8元多时买了”,李驰说。 90年代的股市,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幼年期。前5年是短线暴利的巅峰,刺激得像香港电视剧,每天有人一夜暴富,有人破产出局。后5年,则是坐庄最凶猛的时期。投机是资本市场的主旋律。 当李驰在深圳小打小闹地开始自己的资本生涯时,在上海的一家交易所里,朱平也完成了与股票的第一次接触。 朱平生于1969年,199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他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物理学家。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马鞍山,在一所师范中专教了3年书。1993年,他考入上海财经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读研究生。“时代真的变了。”十几年后朱平说,“我们那一届100名同学,最初只有两个人在证券行业工作,现在有一半的人在做金融工作,在证券公司的就有1/3。” 读研究生时,朱平拿出几百块钱生活费和同学合伙买了只股票——永生股份。“当时,有位同学快过生日了。我说,如果赚了钱,就拿出来大家吃饭或者买礼物。等到第三天,突然涨了10%,又等了两天没动静,我就把它卖了。赚了100多块钱。”朱平回忆说。但当时,他并没有对这个行业产生特殊的兴趣,“最初我不会想到做投资这个行业,我想去外企做营销”。 1996年朱平毕业,中国经济正经历着通货紧缩时期。工作不好找,他就去了一家儿童服装公司做市场经理,月薪1000多元。这份工作只做了11个月,一名在广发证券工作的同学,将朱平介绍过去。做服装销售一年,朱平攒了1000多元,他用大部分积蓄买了一张机票,前往广州面试。面试成功后,坐火车回上海收拾东西。当他再次来到广州,成为新组建的广发证券发行部的一名新员工时,几乎已身无分文。 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资本市场的新时代开始了。这一年,朱平去了广州,李驰去了香港。李驰在深圳公司驻港公司工作,负责公司的投资工作。也正是在香港,李驰见识了真正的资本市场,得到了更残酷的教训。 “刚去香港的时候,我们是抱着炒一把的态度,尽管已经很小心了,而且还是选择了高速公路股,又是打新股,结果还是损了手。”李驰说。 有意思的是,让李驰“损手”的就是刚刚回归A股即被疯狂炒作的“四川成渝”。1997年,这只股票首先在香港上市,算上发行佣金价格是1.55元。李驰觉得价格很合适,就用了几千万元去买。结果上市第一天就跌破发行价,跌到了1.2元。“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要在内地股市,绝对股价这么便宜的股票第一天应该是涨到天上去,怎么可能跌破发行价?”李驰说,“刚到香港,我简单地认为,几十块钱的股票就比几块钱的有价值,这是一个多么愚蠢的认识。现在已经深刻明白,市盈率才是高低贵贱的标准,低市盈率区间买,高市盈率区间卖,没有一次错。” 这只股票生不逢时,一年后最低跌到了0.3元。在1998年的一次强劲反弹中,它回到了1.4元多,李驰把它果断出清,很幸运亏钱不多。又过了10年,这只股票还没有回到曾经的高点。 “我知道了,香港的股票还会跌破发行价,便宜不代表不会继续跌。即使跌到了1分钱,10股并一股,也可以继续跌,这就是所谓的垃圾股股价完全可能是无底洞。”李驰说,“如果当时买了垃圾股,用香港的话说是,可能永远回不了家乡了。说到成渝高速H股(香港名)的股价,也是10年才还乡啊。” 经过这次教训后,李驰认识到什么是价格什么是价值。 在从上海到广州的火车上,朱平说他翻来覆去地看一本名为《投资银行学》的小册子。这本册子的作者是陈云贤,当时任广发证券总经理,现任佛山市委副书记。对于接下来的工作,朱平有些茫然。 事实也是如此,他在发行部待了3天后就被派出去做项目,为准备上市的企业准备材料,做发行。“差不多什么都不懂,一名同事现场指导了我半个小时,我就出发了。”朱平说,“开会的时候遇到问题,我就去洗手间打电话回来请教。” 接下来的几年,朱平奔波于四川、北京、湖北、湖南的众多企业之间。“当时上市公司质量比较差,大型国有企业根本就不会上市。只有小型的省属的国有企业谋求上市,这些公司的资质都不太好。当时有一家湖南的岳阳纸业,产能规模在几千吨,设备都是70年代的,但这10年里规模增加了10倍,资产也增长了几十倍。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想找个净利润3000万元的企业都很困难。”朱平说。 机会来了 世纪之交的香港沉浸在科技股的泡沫狂欢中。“当时的中移动、联想等大市值股票,都涨了大约10倍,科技股的市盈率都很高,市场极其疯狂。”李驰说,“我们这次的成绩比上次好,都赚钱了。” 这时候李驰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回头再去研究巴菲特、彼得·林奇等大师,发现他们说的话都是发自肺腑没有任何包装,“真理其实挺简单,关键在于人们往往不相信真理就这么简单”。 2001年左右,李驰和合作伙伴韩涛一起在深圳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迈出了私募生涯的第一步。此时,除了B股外,他更多的参照系还是香港。“2003年再回到香港的时候,我们感觉不能随便再炒了,风险非常高,要踏实地以做事业的心态投资股票。”李驰说,“因为像盈科数码(现在改名为电讯盈科,已经5股合1股)这只全香港人都在买的股票,都会从20多块跌到8毛多,还有什么不能跌?”

2000年,广发证券筹建易方达基金公司。朱平进入易方达,最初担任基金经理助理,2002年开始担任“科汇”的基金经理。早在1992年,中国就有了第一只基金。但真正的中国基金业的起点是在1997年。这一年的11月,《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颁布,随后第一批基金公司诞生。易方达是第二批获批的基金公司。 2002年以前,国内基金业仍处于发展阶段,公司研究体系、投资体系、风险监控体系都不完善。“我们在筹建之初,就按照证监会的要求向国外机构学习经验,建立了投资股票库,以及相应的投资制度。”朱平说。 证券工作的几年间,阅读一直是朱平的日常生活。“看得比较多的是巴菲特、彼得·林奇的书。有本《美国的十大基金经理人》令我印象深刻,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巴菲特、彼得·林奇、索罗斯、罗杰斯等投资大师的特点和风格。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书也都读了,包括《股票作手回忆录》、费雪的《怎样投资成长股》等,还有各种关于交易的书如《短线是银》什么的。”朱平说。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