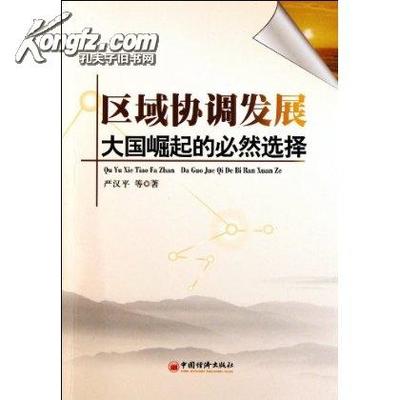作者:翟东升
通过WTO的规范和约束,商品和服务如今可以基本自由地跨越国界流动,但问题在于资本的流动还缺乏一个类似的多边国际法体系的保障。一直以来,美欧日等国都极力将多边投资议题纳入WTO框架内。 在此问题上,南北矛盾体现得特别明显:资本输出国主要是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资本输入国。后者很想吸引外资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但是又很不愿意承诺向外国投资者提供高度的保护,因为那意味着对自己主权的减损和未来政策选择空间的限制。在一些左翼政府和理论家(比如阿根廷的卡尔沃主义)的倡导下,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都团结一致地反对西方用国际法为其资本输出保驾护航的阴谋。
因为穷国们的捣蛋,综合性多边条约总是搞不成,怎么办?那就把它们撇在一边,富国们关起门来自己搞,毕竟FDI中有八成是在富国间流动的。要是哪个发展中国家脑子开窍了想加入,就让它自己申请。在此思路下,经合组织OECD的29国于1995年开始围绕“多边投资协定MAI”进行谈判。其目标有三:第一,提供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规则,为国内外企业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并享受前后一致的投资待遇;第二,设定高标准、自由化的投资保护;第三,规定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让外国企业可以状告东道国政府违约。MAI谈了三年半最终失败了。这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无关系:上世纪90年代后期欧洲多个中左翼政府上台,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人对资本自由流动的负面代价心存疑惧,各种非政府组织出于各自目的大吵大闹,再加上各国商业团体的支持力度普遍衰减,OECD搞的多边投资条约与WTO框架下的努力一样付诸东流。 既然全球性的不容易谈成,那就搞地区性的。在地区自由贸易区条约中,把资本与贸易捆绑在一起,是个挺高明的招:你想和我搞自由贸易,那就得承诺保护我的投资。在这种捆绑策略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就范了。比如美、加、墨三国的北美自贸区NAFTA和美国同新加坡等国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中,资本自由流动终于得到国际法的高度保障。这里又产生了溢出效应:已经同西方签订了高标准投资保护协议的国家(如墨西哥和新加坡)再同别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时候,基本上都会要求沿用此前同美国签的那种高标准格式。 因此,近年来各国间的双边投资条约的签订数量和对外资保护程度都大大提高。到2005年底,全球已经有了将近2500个双边投资条约,其中越来越多的条约是以美国范本为参照对象的。其高标准保护体现在三个方面:准入前国民待遇,征收条款和例外以及投资者诉东道国机制。以前,是否允许外资投资本国市场是需要东道国政府批准的;一旦外资享有准入前国民待遇,那就意味着外资在开业和并购时的市场准入上与本国公民无异。征收,是政府对内主权的一部分,条件必须是出于公益和非歧视性的,而且按照美国人的“赫尔规则”,东道国政府对外资实施征收或者相当于征收效果的其他政策后,必须给予“充分、及时、有效”的补偿。投资者由于东道国政府在上述问题上的违约行为而遭受损失,可以在世界银行下设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起诉东道国政府。 当然,从法理上东道国手中还是有几个安全阀门的,因为ICSID公约授予四个权利:“逐案书面同意权”“当地救济优先权”“东道国法律适用权”“重大安全例外”。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时候保留这四个权利,就可以避免陷入阿根廷现今的困境:上世纪90年代阿根廷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右转,草率地签订了一系列高保护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如今政策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伤害到外资的潜在利益,结果频频被告到ICSID,罚了数十亿美元。 中国该怎么办?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双重身份中,一方面我们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这要求我们在签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或者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尽可能保留主权从而保留未来政策调整空间;另一方面我们正在迅速成为资本输出大国,这就要求通过高标准的国际协议来确保投资安全与自由。国际经济法的老专家陈安教授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路:我们的外资主要来自发达国家,所以跟他们签的协议尽可能采用低标准,这样他们比较难告倒中国;我们的对外投资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原料生产国,而这些国家本土的法律体系不健全,所以应该跟他们签订类似于美国模板的投资保护协定,一有问题直接去ICSID解决而不是在当地法院。两类协议之间的自动联系机制在于最惠国待遇(MFN)原则,那么我们切断这个自动联系的办法就是在与发达国家签的投资条约中明文排除和限制MFN条款在争端程序中的适用。这样的政策自由,在反思“市场换技术”的大背景中显得尤为必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