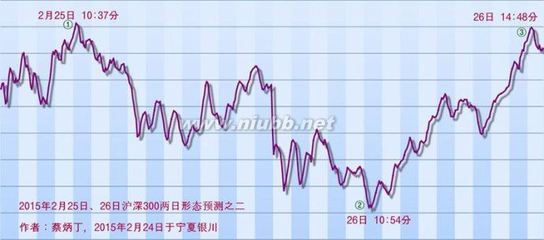文 |马宁
一位朋友看了我大部分读书评论之后,对我说:“你的骨子里就是个农民,所以你以农民文人的身份自豪,为农民阶层鼓而呼”,我大吃一惊,事实上这些年我最大的努力是尽量擦掉自己身上的农民习气,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方式。读者这么理解我,要么是我的努力成效不够,依然以一种农民的生态出现在城市里;要么是我的朋友理解有误,至少我自己内心有一个清晰的向度:我不可能仅仅为了农民的表面财富才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只是为农民的权力说话。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总是站在公平结果的角度同情农民,却没有去思考农民权力的式微。久之,我们的农民情结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公平、粗糙的愤怒。我们与历史里那些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领袖并无二致。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农民都应该拥有参与到这个市场里的基本权力。所以,与其说我是在为农民说话,不如说我是在为所有权力被剥夺的中国农民说话。或者说,中国人都是农民,因为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我意识到包括我在内的诸多中国人,他们参与市场的权力,仍然处在一种被剥夺的历史范式之中。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态势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正是抱着上述心态,我在3 月读到了加拿大柯鲁克夫妇的两本书《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据称,这是一部不同于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社会史,讲述的是普通民众的事,并且是由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讲述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追述了20 世纪30 年代十里店的村民们如何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自己的村庄,协助八路军展开斗争;并讲述了后来他们又如何着手推翻旧的地主- 雇农制度,使土地回到耕者手中。将问题讲得最中肯的是那些有阶级觉悟,敢于同侵略者作斗争,带头推翻旧地主-雇农制度的贫农和雇农们。这一部分贫农和雇农分得了土地,掌了权,后来被称为“新中农”。 显然, 柯鲁克夫妇对这些打土豪、分田地的行动赞美有加, 认为“他们的成就是了不起”。柯鲁克夫妇还遗憾的认为,有一个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相当一批人,因生性胆小或无助,未敢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所以没有得到足够的土地,仍然很贫困。 70年多年后的今天, 我们带着某种对历史的审视来读这样的书,体会更多的似乎是某种讽刺。至少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需要理清。其一是当年的推翻地主雇农制度,事实上破坏了中国农村既有的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并导致70年以来,中国人在思考农民土地制度问题时,把当年的这种破坏行径当成了一种经济学前提。这正是到今天为止,广大农民在产权意义上被这个市场遮蔽的主要历史原因;其二,当年农民们通过暴力手段将地主的土地抢夺之后,并没有按照某种乌托邦思想的设计,真正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70年的历史演进并没有维护农民的土地权利,反之,国家以某种人格化的强权形象出现,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农民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一无所有,当年地主悲惨的命运同样降临到了这些曾经斗志昂扬的农民身上。 历史再一次以土地产权意义上的错误戏弄了中国农民,并且这一次的错误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里大大小小的农民性错误基本没有区别。它只是一次平常不过的农民起义,没有人站在土地产权的经济学常识上去思考,更没有人怀疑通过暴力的手段进行土地变更是否恰当,这种暴力会给以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所有的人都站在某个狭窄的角度里孤芳自赏,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堆廉价的颂歌。柯鲁克夫妇的这两本书应该可以归到这样的颂歌里。今天我们看这样的书,首先是反思,其次是在比较翔实的史料里进行反思。这样说来,这两本书的史料价值还是比较明显的。几年前,我曾经读过另一本类似的书:威廉·辛顿《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1 )。在某种意义上,辛顿和柯鲁克夫妇异曲同工,都对暴力性的土地分配进行了赞美,而忽略了土地产权危机。倒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对上个世纪30年代的长江下游自然市场进行了理性调查,揭示了土地私有、副业、贸易和运输业对农民经济的重要影响。今天,苏南经济的态势,事实上是对费孝通当年描述的经济态势的一种回归,是对中国农民在土地问题上和自由贸易问题上的一种偿还。只是我们还偿还得不够,更加本质的农民权利至今还被某种威权攥在他们的手里。
有一个问题在这个时候需要提出: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农民的贡献在哪里?答案其实是明显的,第一是农民通过责任田的形式解决了中国人的饥饿问题,第二则是农民以“民工”的身份介入城市经济,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业制造和城市服务职能。吉林省省长韩长赋为此写作了一本新书《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是最近几年国内直面农民工问题的专著。该书试图突破传统方法论范式,找到农民工问题的发展规律和客观趋势,并试图构筑农民工社会支持体系。韩长赋属典型的学者型官员,在团中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部、国务院研究室担任过显著职位。他的书里明显规避了过去土地制度问题上的错误,也在农民的权利问题上进行了理性思考。这让我们看到,高层可能并不是一味的画地为牢,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农民问题能走上自由权利的轨道,而得以最终跳出以暴易暴的历史窠臼。 不过, 韩的著作并没有触及到土地权力问题,更没有对农民利益和政府利益之间的博弈进行更直接的思考。事实上,这正是我的兴趣所在。去年,我一直都在继续读奥地利学派,尤其是米塞斯的书,并对今天中国主要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态势有了更加宽泛的认识。我想说的是,21世纪开端的中国经济格局,可能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40年代前的欧洲大陆存在某种类似。当时,整个欧洲差不多被一种看起来伟大、光荣、正确的全能政府所统辖。这种全能管理最明显的地方,是在大学。大学的产权完全属于政府,因此理所当然地由政府来行使大学的管理职能。所有大学都接收教育部的管制,就像警察局接受警察局长的控制一样。而所有的教授同巡警和海关人员一样,都是国家公务员。政府管理的方式直接从任命大学校长开始,他们通常只任命那些值得政府信赖、可靠的人,任命那些与政府观点完全一致的、相信政府万能的人。为数稀少的自由主义学者们试图从教育部的全能权力中捍卫知识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但政府权力在手,社会约定俗成,他们的声音被视为大逆不道,并迅速被埋没。 米塞斯和他的学生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度日,并最终决定逃往美国。美国得以享受到自由经济学派的巨大成果,但是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自由主义经济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排斥。教授们把视野局限在狭隘的领域,大家都不关心政策的未来后果,而政府对这样的行为和立场竟然予以奖励。人们的工具理性上升到了偏执的地步:劳动经济学家只研究劳工政策的后果,农业经济学家只研究农业价格的上升。他们都只是站在政府压力的角度看问题,根本不关心最终的社会后果。他们已经不是经济学家,而只是特定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的解释者。 米塞斯认为,20 世纪早期盛行欧洲的极权主义,是“官僚体制在教育领域占了上风的产物,大学为独裁者铺平了道路。”今天中国的大学缺乏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已经是一个显在的事实。我曾经在一个私人场合与清华大学的一名知名教授谈及农民土地私有化的问题,面对我的疑问,他的态度甚至是激烈的,认为我提出的问题,碰到了党的底线,没有必要继续讨论下去。教授的心态我是能够理解的,就像当年的韦伯夫妇天真无邪地赞美苏联一样。可是几年以后,当韦伯夫妇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然科学杂志》提倡“数学中的党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外科学中的纯洁性”,他们还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那么现在, 究竟有多少看上去有影响力的官员和学者能直接指出:中国农民问题可能不是我们看到的表面公平问题,而是一个权力问题,我对此抱以谨慎的悲观。农民需要在土地私有权、自由贸易权和信息知情权等方面享受到国民待遇,这几乎只是一个常识,就像韦伯认为数学中肯定没有党性一样。我还相信,无论是何种意识形态,中国农民问题只有沿着权利的层面去建设,才可能找到正确道路,仅仅在结果的公平层面偶尔施舍、互相攻击,也许又会绕到以暴制暴的历史旧路上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