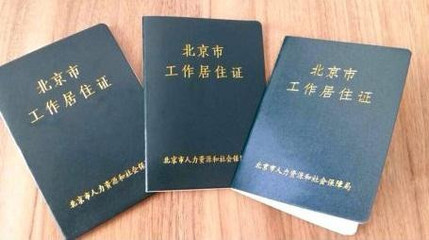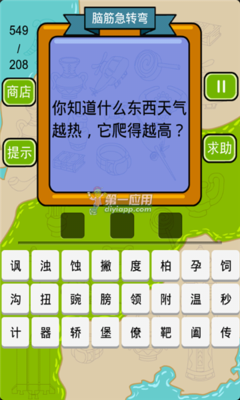2013年8月,央视推出电视剧《推拿》;9月初,话剧《推拿》在国家大剧院首演;电影《推拿》亦有望年内公映—这是继2008年毕飞宇出版《推拿》、2011年凭此小说获茅盾文学奖后的又一场“推拿”热。 “这一年多,我总去推拿中心—当然,还是没有毕飞宇去得多。”话剧《推拿》的导演郭小男说。 排演这出戏,缘于郭小男对边缘群体的关注,也缘于自己被他们深深打动,郭小男介绍,“城市里的盲人推拿师,多来自农村以及文化偏落后地区。实际上,他们能够进入城市,学有所长,以推拿谋生,一定已是人之菁华。他们所经历的苦难、黑暗,所承受的扭曲、压抑,都可化作启迪我们的点滴”。 9月5日,国家大剧院和上海戏剧中心联合创制的《推拿》话剧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首演,剧中重要角色的共同身份都是盲人推拿师,故事讲述的就是这群盲人的日常生活、情感关系,展现的则是以拆迁推拿店为线索的矛盾冲突。 动不了的正常人 横亘在剧组所有人面前的第一大问题,是学习模仿盲人的举止言谈以及衣食住行等所有生活方式,这让大家感到陌生而且困难 。“演的时候,要使我们变成他们,要能说服观众想象他们之前没有想象过的。”排演之前,除了钻研小说原著,男主角张宗琪的扮演者吴军介绍说,演员们足足花了一个月时间“下生活”,去上海盲童学校和推拿房,实际参观、体验。 接近盲人的“下生活”远远带来了超出原先“他们真可怜”的肤浅感受,“他们的生活真不容易。要说他们和健全的人有什么不同,我觉得他们甚至比我们还要全面。”吴军面露敬佩之情。 “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男女之间打情骂俏、健步如飞,不自在、动不了的人反而是我。我在里头贴墙站着,他们都能感觉得到。”吴军这么形容自己站在推拿房里的感受。 “我花钱,要学他们是怎么推拿的,我说学就行了,不用真推。他们说,你好歹也试试我们的手法啊,让我们摁两下不久就会了?!”吴军笑,说盲师们还偏偏不愿只做示范,非要平等地服务到位,好让他们下次还来,“实在精明”。

吴军说,面对盲人按摩师,除了模仿其生理姿态和推拿术,还有一种潇洒的生活姿态,学起来就难了,“他们会像唱歌一样跟客人说话,逗得客人直乐,唱的内容大概是‘没什么大不了,没什么大不了’”。 盲人们的生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样与世隔绝。郭小男说,就他看到的推拿师们而言,“都‘摸’过了《推拿》,也有电视,抱着听《甄嬛传》。” 盲人歌手周云蓬担任话剧《推拿》的音乐推广大使。按原先预设,郭小男想让周云蓬负责整出话剧的音乐创作,这个计划最后失败了,“他无法观看整出戏,体会不到我们想要表达的那种情绪”,让郭小男惊诧的,是周云蓬的方位感,“停车场里,他直直地走到我们面前,说,你们久等了。盲人听觉已经被全方位地利用,像海底雷达一样”。 拒绝来自观众的可怜情绪 “盲人推拿的故事不好排,改成话剧形式尤其难。一位盲人还好展现,但如果舞台上有一排盲人,再用戏剧的形式表现就有可能失之单调,舞台就会失控——只能得到观众的可怜。这不是我想要的。”郭小男如此说明《推拿》的舞台戏剧效果实现上的特殊性。 “如何在表现悲恸与驾驭悲悯,要求普通同情与净化观众心灵之间达到平衡,我们反复摸索了很长时间,”郭小男介绍,这实际上意味着剧中必须有两种系统:“表现盲的原貌”与“间离盲的情感”。 “毕飞宇写书是极其写实的。日常生活,滴水不漏,也有现代主义的意味,将所有人纠集在唯一的场所推拿店里。”郭小男以一个话剧导演的方式解读了原著,并决心放大狭小空间的人际亲密关系及个人内心活动,由此“把沉默的记忆换做影像和声音的片段,唤回幕前,让盲人们普遍经历的不能听见的和不能看见的转换为被听见、被看见。” 话剧开场即是盲人们在蓝色背幕下姿态各异的剪影,他们以一组集体造型亮相,展示了抽象的定格瞬间。 随后,剪影血肉丰满为各位人物。伴随“涌泉穴,申脉穴,太冲穴”的画外音,盲人角色一一出场。舞台上,男女老少推拿师们都穿白衣,每人坐一把白色椅子,整齐地坐成一排,各怀抱一块拆卸好的人体模型器官,或推背部,或拿肩部,或捏足部,或按腰部。 “老板,重不重?对,我家是××的,我干这行已经很多年了。”伴随推拿动作,各色方言的自我介绍此起彼伏。在当盲人按摩师之前,他们是打工妹、失业矿工、农村少年等各种“弱势群体”。在虚无的空气里,他们与各类器官的主人说话,与观众们对话,推销自己的推拿技术,展示自己的推拿人生。 与详细并彻底自报家门的推拿师们相比,真正有形的客人始终缺席。整出戏中,前来获取服务的客人们集体隐没,他们被白色帘子隔开,被塑料肢体代表,唯一获得表达的机会借由盲人之口说出—在这个舞台上,双眼健全的客人是一种微弱的存在。 如何表现“盲”? 话剧《推拿》的台词表现形式,一为普通话,一为以南京话、苏北话为主的地方方言。“这是一个发生在南京的故事。”郭小男强调。 与毕飞宇展现日常盲人推拿师这一独特社会群体的努力类似,话剧演出中融汇方言与普通话也是为此,“之所以要保留角色各自的方言,是为了想要重构边缘群体的生活原貌。我让演员去学习陕西话、南京话、苏北话,因为在这些地方,盲病可能出现得尤其多。” “保留原貌”的副作用是剧组集体浸入“我是盲人”的情绪中—包括导演。“我一排《推拿》总会哭。每场戏演出结束,所有演员都要抱头痛哭一次。”郭小男如此倾诉自己这次排戏的个人体验,“实在是太难了,太恐惧了。”吴军也说,“闭上眼睛演戏,有时就那么一瞬间,能体会到无边的恐惧。‘哗’地一下,全身都汗透了。” 剧中,每位演员处理“盲”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郭小男认为,最后每位演员都找到了让自己舒服且独特的表现方式。“都红的眼睛那么大,睁开就没有说服力了,不像盲人了。所以,她是全程闭着眼演戏的,只有在转身的时候睁眼调整一下方向。张一光就是一刻不歇地翻白眼,两个半小时,从头翻到尾。金嫣则是不停地眨眼、转眼、抽动五官,因为她的角色有光感的,所以总是试图看见。”演出后,郭小男重放了一遍排演视频,镜头放大了演员们的面部肌肉运动,他看着镜头说,“演员们可谓倾其所有”。 “摸美”一幕里,演员沙复明要求摸一摸都红的面孔—那是人人赞为美丽的女人面孔。舞台表演中,面对观众,沙复明站立在推拿椅之上,都红站在沙复明之前。沙复明没有真正地抚摸都红的脸孔,而是在空中向观众展现他充满律动的抚摸—他摸到什么,就念出来,“眉毛,眼帘,鼻子,嘴巴,甚至是呼吸”。舞台背景投影出都红微仰的侧面,背景色彩魔幻斑斓。所有人都看到了,惟有都红和沙复明这对爱人各自哀戚:“什么是红,什么是我名字里的红”;“我摸得到长短大小,冷热干湿,可就是摸不到美。”在沙复明摸与“看”的过程中,观众们也被舞台画面引导,随着沙复明的号召,以集体视觉抚摸着都红的脸部轮廓,一起感受着都红的美。。 让看不见的盲人的情感和精神视觉化、听觉化,这就是郭小男导演整出戏剧的关键之处。戏中还原出的画面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连贯叙事,而是一段段突然重现的幽灵般的回忆:满台讽刺的掌声,刺耳的车祸现场,幽灵般逡巡怒视的后母,矿井塌方的惨状……深埋在诸人回忆里不能说的创伤,都一一变成了剧场中所有人都可见、可听的碎片。 在成为盲人按摩师之前,他们一一经历了些什么?《推拿》正是如此试图挖掘盲人们生理病痛的前史,在舞台上多时空地交错反映盲人们的心灵创伤经历—无论盲与不盲,这也是在场所有人一起经历的一场心灵之旅,正如郭小男所说,“再无我们、他们之分,展现的是整个人类从黑暗到光明的追求,这才是这部戏的意义所在。”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