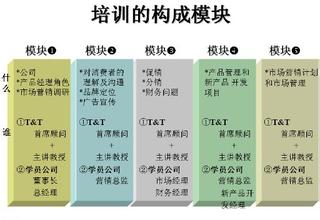打电话到服装工业发展协会(Garment Industr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GIDC)的时候,没人接我的电话,电话铃只是一直不停地响。几天之后,我才通过电子邮件收到回复并被邀请前往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GIDC总部。收到邀请后,我决定前往服装工业发展协会。我先乘坐地铁到达西34街,出地铁后经过一个时髦的小小精品店,精品店的入口挂着一面横幅,写着“价格是王道”。我走到街对面铺满砾石的第七大道,也就是世人熟知的时尚大道,走过Joey,一家折扣批发店,在那里我曾买过50件1美元的丝网印刷的T恤。数月之后,我一位买了这种T恤的朋友告诉我,她的T恤已经脱线,可不可以换件新的? 直到转向西38街,我才终于看到熙熙攘攘的人流。经过一些藏在脚手架后面的布料商店和缝纫店以及一辆正在卸货的卡车(卡车里装满了裹在塑料袋里的服装),我来到一座具有20世纪初风格的大楼前。进电梯后我按了5层,最后敲响了一扇没有任何标志的门。一位个子很高、长得很精神、穿着仔裤和贴身衬衫的男士出来应门,然后把我领进了一家小房间里,招呼我坐在房间中间的椅子上。房间里除了两张空桌子和几个货架的衣服,什么装饰也没有,也没有其他员工。安迪·沃德坐在我对面。“我们已经裁员,”他说,眉毛高耸,流露出自嘲的神情。在这里我连一部电话都看不到。除了眼前的这个人,没人接电话。这就是我对服装工业发展协会最初的印象。 过去10年,服装制造业被认为是美国衰退最快的行业之一,排在它前面的只有报纸发行业、有线通信业以及纺织厂,纺织厂和服装制造业这两个行业其实是密不可分的。12007年前的这10年里,服装制造业有65万人失业。2我猜想这种情形也许与廉价时尚工业的出现有关,并开始关注位于纽约市的服装工厂,希望一探究竟。 结果我发现,GIDC其实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这个组织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类似于驻扎在曼哈顿服装中心(Garment Center)的管理机构,位于34街和42街之间的西区,那里见证了服装贸易的繁荣发展并逐渐走向萧条的历史。GIDC成立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律师事务所及其他机构入驻服装中心的大楼,这里自1987年起就被划定为只允许与时装相关的企业进入,为此它向房东许诺会提高租金。这其实是很难办到的,纽约已没有几家服装制造商能够填补这里的空间。服装中心有900万平方英尺的面积可用于服装生产,但沃德说只有不到1/5被使用。 这些天里,GIDC正忙于帮那些独立服装设计师和仅剩下的能够处理他们订单的服装厂联姻。“如果有人想做晚礼服,我们就会帮他们找家工厂,”沃德解释道,“我们帮他们处理采购和销售。”GIDC曾经雇有多位职员,有一家很大的办公室和像样的产品陈列室,但由于未能及时交纳租金,他们被迫搬了出来。他们的抱怨很能让人理解,因为部分原因是前任主管管理不善。但纽约市和纽约州政府也停止了对他们的资助。所以领薪水的员工已经被解散,只留下了安迪·沃德,事实上他也有好一阵没拿到薪水了。他现在是在零报酬的情况下勉力支撑着。“我就是GIDC,这个地方已经完全没落,”沃德说,“我们已经接近死亡。”整个美国的服装工业的现况也可以用这句话来描述。 每年都会举办梅赛德斯-奔驰时装周,是800多个时装公司的总部所在地,纽约是毫无争议的时装设计之都。3但这里曾经也是服装制造工业的中心。早在1900年,服装制造业就是纽约市最大规模的工业。20世纪时,美国女性所穿的绝大多数时装都产自这里。这里也生产男装,虽不如女装那样兴盛,规模也不容小觑。几十年来,服装中心的人行道简直无法让行人通行,每个小巷中都堆满了纺织面料和一排排装满成衣的货架。安迪·沃德办公室的下面是各种与服装制造业有关,如经营纺织面料、纽扣和针头线脑的商店。如今,整个“生态系统”仍然存在,只是规模要小得多了。 服装中心曾是移民和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努力工作的地方。这个行业提供了很多蓝领和中产阶级的就业机会,包括中间商、批发商、推销员、印花工人、制版工、剪裁工和大量缝纫机操作工。如今纽约仅存的几百名服装制造工人仍然艰难维持着体面的生活,凭着自己的技能和经验,他们一年能挣3万~10万美元,包括各种福利在内。4 在一年之中,我走访了纽约的多家服装制造厂,服装中心对我来说变得非常熟悉。过去在我看来是弥漫着悲伤和没落情绪的地方,如今却在熟悉之后呈现出另一种面貌:这里曾是制造时装,而不是消费时装的地方。它完全不需要显得光鲜亮丽。仍在这里孤军奋战的设计师和服装制造厂与那些锁眼工,以及售卖衬里、热熔衬、线、针和摁扣的店面在这里相依为命。 达尔玛制衣厂(Dalma Dress Manufacturing)位于纽约市,在整个服装工业更依赖进口的大环境下,这家公司历经了30年的风云变迁,始终屹立不倒。自20世纪70年代起,公司就已经在服装中心扎根,一开始是占据了西39街的一家两层楼的工厂,雇用了200名工人。创立之初,达尔玛是为曾辉煌一时的大型服装制造商Abe Schrader和Malcolm Starr生产质量优良但价格适中的女士服装。Ralph Lauren和Bill Blass曾是它最大的客户。达尔玛完全没有想到,就在制衣厂成立的时候,美国服装制造业的巨变同样拉开帷幕。“一切发生得都太快了,我们指的是70年代末期,服装行业自此开始走下坡路。”制衣厂的经理迈克尔·迪帕尔马说,正是他的父亲阿曼德开办了达尔玛制衣厂。 达尔玛制衣厂弥漫着一股怀旧的气息:一卷卷的布料、勾勒出每件衣服技术细节的图纸、小小的车间里散落着各种女装人体模型。当迪帕尔马和我在他的办公室交谈的时候,一个女裁缝冲了进来。“这是机器缝制的。”她解释道,手里拿着一件镶金色珠子的长裙,如果零售的话可能要几千美元。“这我不管,”迪帕尔马咆哮道,“我只要它能结实点。”裙子上的拉链曾是用缝纫机缝上去的,但迪帕尔马确信由于裙身太重,拉链会被撕掉,除非接口的地方是手工缝制。他是一个神经高度紧张的人,嘴里冒出来的服装行业的专业术语在我听来像一门外语。他也会花很多时间待在车间里,帮帮工人们的忙,使工厂能够继续经营下去。他告诉我:“没有人会坐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干。” 在早年间,达尔玛制衣最常接到的订单是为Ralph Lauren这样的客户制作1000件女士衬衫。“那种订单是我们最想要的,我们称之为‘创业基金’。接着一切都变了,”迪帕尔马指着他办公室的一个衣帽架说道,这个衣帽架在我们的交谈中代表亚洲。如今,整个制衣厂的规模缩减到一层楼,员工的人数也只有约40人,专为两家赫赫有名的美国时装设计师缝制高档晚礼服和婚纱。过去,达尔玛和纽约其他制衣厂都会婉拒这种订单,因为订货量不大且需要大量人手,而如今它已成为服装中心的生存之道。“高档礼服一直都有市场,”迪帕尔马说,“但是你不会想要去拉这种订单。你只想回到家,彻底地放松,知道周末又会有500件完工。困难一直存在,但没有人想要去找这种订单。” 因为多种原因——为一个订单安排人手、训练工人需要时间和金钱,因此服装制造厂偏爱大批量、复杂程度低的订单,因为产量越高,分摊下来的成本就越低。越是简单的款式,就意味着订单完成的速度越快,也不需要先进的缝纫技术和专业机器。不管订单的量大还是小,工厂的投入成本是一样的,包括购买面料和线、购置机器、制造和装运样品,以及购买包装袋和洗标。 朱厄尔是一位位于孟加拉国(以下简称“孟加拉”)达卡市的制衣厂厂主,这家工厂为Echo、Universal Studios和Umbro(耐克的一个二线品牌)供货,他告诉我他更愿意接受来自大公司的大批订单,因为这样他可以收回投资成本并且创造可观的利润。“不管是生产500件还是5000件,我的维护成本是一样的,”朱厄尔说,“订货量越大越好,肯定更好,制衣业主要是走量,这也是那些大公司赚钱的原因。” 朱厄尔的工厂,Direct Sportswear Limited(DSL),雇用了大约200人,每个月生产超过40万件T恤和运动裤这样基本款的单品。只要一个客户订购的数量达到几十万件,他就能大大降低运营费用。如果1000件衣服朱厄尔给出的定价是10美元/件,那么数量越多,价格就越低。“如果它们订的是10000件,我就能降到5美元一件,”朱厄尔解释说,“成本能减半。”到了某个点规模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时候,价格就不能再低了。到哪个水平工厂既能获利又能给顾客提供最低价?在DSL,朱厄尔给出的答案是令人咂舌的25000件。“这是最大数量。”他告诉我。 早在20世纪30和40年代,在纽约周围的几个州,服装制造业就在追求更低工资和更便宜的价格,西至西海岸,南至美国南部。但是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低价还是来自海外市场。安迪·沃德的祖父在缅因州拥有一家毛纺厂,而他的父亲曾拥有一个大型男士服装品牌New York Sportswear Exchange。安迪·沃德说,到海外市场寻求低价使得美国国内的服装制造业立即失去竞争力。“当每个人都转向海外市场的时候,我们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他说,“从此以后,你只能到亚洲生产服装。这个盒子再也无法关上了,我们同样再也回不到过去了。盒子打开了,一切完结了。” 就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美国开始从日本进口棉质服装。10年后,来自中国香港、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服装开始涌入美国市场,但规模相对较小。1965年,进口服装只占美国服装总销量的不到5%。迪帕尔马告诉我,款式更简单的基本款单品是最早迁移到海外生产的,只因为在手机、传真机或者互联网还没有出现的年代,这样更便于沟通。“一件衬衫长什么样?有两片前襟、一片后背、两个袖子、一个领子、一个口袋,再钉上纽扣,”他描述道,“我刚才在一分钟之内解释了一件衬衣是什么样子,这在电话里就能谈成。”然而在早期,进口服装的质量很难把控。 如果想要理解为什么整个服装制造行业都迁移到了海外,只需要知道即使把整个服装行业转移到低工资国家,人工成本仍然在服装制造成本中占较大比例,就能明白了。据最近所做的估计,原材料占整个制衣成本的25%~50%,人工占20%~40%。5“服装制造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不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你需要有人坐在缝纫机前。”迪帕尔马说。服装,即使是在工厂里生产,也是在生产线上手工完成的。缝纫机与其说是机器,倒不如说是工具,它实际上只是加快了手工制作的速度。服装制造业独一无二的劳动密集型特点,使缝纫成了全世界最普遍的手艺,也是服装行业最普遍的工种。 服装大都为手工缝制似乎显而易见,但正是这一点对服装的定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支付给缝纫机操作工的工资和付给服装制造厂的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服装的价格。要让车子更便宜,就得寻找更便宜的零件。廉价服装的确依赖更廉价的原材料,但是迪帕尔马告诉我,两个国家,例如中国和日本在布料上价格的差异可能只有50美分,还不足以影响服装的定价,“这起不到任何影响,”迪帕尔马称,“那并不是我赚钱的地方,人工才是。在美国有劳工法,我支付的工资不能低于法定最低工资。”为了生产廉价服装,只能寻找廉价劳动力。 在美国各地的劳动力成本各不相同。安迪·沃德告诉我,纽约一名熟练技工的工资是12~15美元一小时。而好的制版工能挣到17~18美元一小时。根据政府给出的数据,美国缝纫机操作工人的平均工资就低得多,只有9美元一小时,或者1660美元一个月。但是与多米尼加共和国(以下简称“多米尼加”)的最低工资相比,又好得多了。多米尼加在自由贸易区内,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4900比索,合150美元一个月。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近年来大幅度上扬,但在沿海省份的最低工资仍然只有147美元一个月。6孟加拉在2010年11月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但只要求工厂付给缝纫机操作工43美元一个月。如今美国制衣厂工作的工人尽管按美国标准工资偏低,但也比中国制衣厂的工人挣的4倍还要多,是多米尼加制衣厂工人的11倍,是孟加拉制衣厂工人的38倍。 以下只是一些例子,旨在证明工资之间的巨大差异影响了服装的定价:杰夫·卢兹是J.Brand(一个高级牛仔品牌)的主管。他告诉《华尔街日报》,该品牌一条定价300美元的牛仔裤如果是在中国生产,价格可能降到40美元。7我问迪帕尔马,要做一件有衬里的、带皱褶、黑色涤纶迷你裙,他的工厂定价是多少。我在Urban Outfitters打折的时候花30美元买过一件,并且把裙子带到了他的工厂。在我还没有说完的时候,他就开腔了,“30美元。”但他给的价格不包括面料的成本。我拿着同样一条裙子在中国的4家工厂询过价有三家报价5美元,另一家高端的工厂报价12美元,包括面料的价钱。在孟加拉一家工厂报价也低于5美元。有一家工厂提出可以低于1.5美元一件的价格帮我运到美国,使得一条这样的裙子的总成本比达尔玛制衣厂的一半还要低。尽管这家工厂就在纽约市,而且可以做一条这样的裙子。 当然,美国也有很多工厂支付的工资低于法定最低工资,并且利用低工资在一个一心只想降低价格的行业里竞争。美国与血汗工厂的联系也和工业革命的历史一样古老,反对血汗工厂的运动早在1911年就已经在服装制造业展开,当时在纽约发生的那场臭名昭著的Triangle制衣厂大火夺去了146条生命。工厂主为了防止偷盗而把工人锁在了工厂里,有1/3的工人因为想从窗户跳下而摔死或者倒在了坍塌的消防通道里。 有些服装商人则把目光投向了曼哈顿唐人街内非法经营的工厂。莎莉·瑞德是一位服装制造和质量控制专家,在纽约的服装制造行业工作了30多年。她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市中心的居民区内那些热火朝天的小工厂。那时,她的客户是第15街一家意大利人开的工厂。这家工厂专门制造带衬里的运动夹克,单价在42~48美元。一个位于唐人街的工厂将这种运动夹克衫的售价压低到28美元,结果不仅导致她的客户被迫关门停业,也使纽约市其他合法经营的工厂生产的运动夹克失去了竞争力。 为什么价格差异会那么大呢?一家工厂生产的运动夹克得要48美元,而另一家生产的同样产品却只要一半的价钱?“它们付给工人的报酬肯定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我敢保证,”瑞德回忆说,“就在那家报出28美元低价的工厂里,肯定到处都爬满了蟑螂还有老鼠,而且那里肯定没有卫生间。”唐人街的很多工厂都位于破旧不堪的建筑物里,瑞德还记得那些工厂地面打的洞,就因为老板懒得装修卫生间。 如今,唐人街里那些过去10年曾经生产出大量廉价服装的工厂多数已经被关闭了。那里不再有制衣厂,地产开发商的开发推高了那里的租金,那些小工厂比位于服装中心的工厂更快地被扫地出门。沃德估计说,直到2003年年末,唐人街还有250家服装批发商店。“现在只剩下20家了。”他说道。有一家位于唐人街的大型工厂,一个周末可以生产4万件衬衫,做工也不错,但现在这家工厂也关闭了。 20世纪50年代,在洛杉矶的服装制造业兴起了压缩工人工资的势头,后来这股势头又蔓延到纽约。20世纪90年代末期,洛杉矶有12万人在服装厂工作,如今那里的服装制造业在全美也是规模最大的。8西海岸的服装工业和纽约的很不一样,东西海岸之间也没有直接的竞争。东海岸专注于制造更加正式、个人定制的服装,就像是以20世纪60年代为背景的电视剧《广告狂人》(Mad Men)里演员们所穿的女士长裙和男士西服。而今天,纽约仍是美国制作男士定制夹克或者高档晚礼服的首选之地。 洛杉矶是更具有加利福尼亚度假风格的运动休闲服的诞生地,时尚界人士将宽松的运动短裤和瑜伽服统一称为休闲运动服,这样显得好听一点。这些宽松、轻巧、随意的运动服正是大多数美国人平日的穿着。加州时装协会的会长伊尔丝·梅切克在20世纪60年代运动休闲服在西海岸开始兴起的时候就已是服装贸易行业的从业人员了。她记得当时女性已经开始厌倦纽约那种束腰紧身、带衬裙的裙子,转而选择加州人喜欢的更简单舒适的款式。“我们发现,一夕之间纽约的时髦风格和加州的休闲风格之间出现了对立。”梅切克回忆说。近几十年来,洛杉矶也建立了庞大的牛仔服制造业,这里生产的牛仔属于高档牛仔,零售价超过150美元/件。 我在2010年8月参观了洛杉矶的一家服装厂,也见到了进口产品对那里的服装行业的冲击。接待我的是一位大学生兼职翻译米歇尔和一位在洛杉矶做了20年缝纫工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卢普·埃尔南德斯。10年前,埃尔南德斯带头发起了一场反对Forever 21的运动,当时在洛杉矶市中心制衣厂工作的缝纫工拿到的工资比法定最低工资低得多。9埃尔南德斯就是那些工人中的一个。自那以后,Forever 21开始将一部分生产转向海外,但一些时尚灵敏度更高、需要尽快在美国国内上市的服装仍然在洛杉矶生产。 埃尔南德斯现年37岁,身高一米五三,全身上下充满活力,穿着一件黑色细肩带紧身背心,带着金色十字架项链,涂着鲜红色的口红,描了眉毛。她带领我们走进位于洛杉矶市中心西第八大街和南百老汇大街之间的一家工厂大楼,Forever 21及其二线品牌Reference仍然有些是在这里生产。大楼的一层有6间工厂,工厂环境很简陋、面积也很小,每间工厂只雇用了20多个西班牙裔妇女和几个男工人,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在用缝纫机缝纫并将做好的衣服放在架子上。 洛杉矶所有的服装工人都是按完成的衣服数量计算工资的(即所谓的计件工资)。例如,像埃尔南德斯这样的工人修剪衬衫,包括剪去线头什么的能挣4~5美分。工厂付给他们的工资只需要达到最低工资标准就行了,而不管需要完成多少件才能达到这个水平。理论上,有经验、干活更快的缝纫工就挣得更多。梅切克说:“法律是即使你完成的件数达不到最低工资的标准,老板付给你的工资也不能低于最低工资。”但洛杉矶很多工厂的工人都没有这么幸运,或者这就意味着他们得完成堆积如山的工作才能挣得微薄的工资。 埃尔南德斯告诉我,她认识的洛杉矶的绝大部分服装工人需要一天工作10小时,一周工作6天,缝制了无数件衣服才能达到最低工资标准。我问她怎么知道得如此清楚?工厂跟工厂之间的工资标准不是各不相同吗?她气氛地说道:“18年前我在这儿工作的时候工资就都是一样的了。”“实际上由于生活成本的提高,我们现在的工作量更大了。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生计。” 那时埃尔南德斯正在为American Apparel工作,这是一个针对年轻人的时尚品牌,以大胆出位的广告和全部产品在洛杉矶生产而出名。2009年10月,一个联邦政府组织的调查使这个公司不得不解雇1500名据说是未经登记在册的工人,那个时候正是25年来失业率最高的阶段。很多被解雇的工人已经在这个公司工作了10年甚至更长时间。此事导致整个工厂人手不够,政府便将当时正处于失业的埃尔南德斯分配到了这里。梅切克告诉我,颇富争议性的反移民法导致洛杉矶失去了很多最有经验的服装工人。埃尔南德斯也同意这种说法,她告诉我:“因为当时失业率太高,很多人被送到了American Apparel的工厂里,但是他们对做衣服一窍不通。很多人在那里只是占个地儿。” American Apparel除了拥有自己的工厂,使用国内的工人,也在其他方面独辟蹊径:它为工人提供医保、股权,还会偶尔让工人享受免费按摩。然而据埃尔南德斯说,这些举措仍然不足以让服装工人成为美国经济的受益者。她告诉我,自己根本买不起零售店里的那些衣服。一件系扣衬衣就要58美元,听起来似乎还不贵,但对一个制衣工人来说就是天价了。我问埃尔南德斯是否喜欢自己这份在American Apparel的工作。“我们待在American Apparel是因为这里能够保障我们至少获得法定最低工资,”她说,“还有休假和加班工资。”但是她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有多好:每天必须完成的定额太高(1天2300件),而且还得紧赶慢赶地才能完成,压力很大。她说:“American Apparel只是没有其他工厂那么糟糕而已。” 起初,洛杉矶的低工资使它的服装业得以在全球更具竞争力,但是由于情况的不断恶化,低工资、糟糕的工作环境和缺乏工作保证已经成为了普遍做法。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劳工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凯蒂·库安说,要让洛杉矶的所有工人加入工会从而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今这个行业正日益全球化,”凯蒂·库安说,“所以工会也很难出台一个措施既能有效地把产能留在美国又同时能提高工人的工资。”即使是American Apparel这个在业内被认为是改善员工待遇的领头羊企业也没有加入工会。一个叫做UNITE HERE的工会组织曾试图在2003年劝说这家公司加入工会,以期为员工提供带薪假期、更便宜的医保、更有效率的生产方法和监工对工人更好的态度。10但是这个尝试以失败告终——当时这家公司宣布工人不想要加入工会,而工会则宣称工人是受到了管理层的胁迫。凯蒂·库安告诉我:“我们总是嘴上说洛杉矶工人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太差,但是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住在加州的墨西哥。” 在我去洛杉矶的前几周,我开了7个小时车穿过大烟山,穿越佐治亚州和南加州交界之处,最终到达南加州的格林维尔。这里是美国正在消亡的纺织业重镇的中心,这个重镇位于I-85公路边,南至格林维尔,北至格林斯伯勒。我去那里是为了拜访奥林·凯克,我父亲儿时的朋友,在纺织业工作了30多年。凯克是一位体贴、热情的长者,带着一副宽边墨镜,穿着一双运动拖鞋。他开车带我沿I-85号公路来到离格林维尔几英里的南加州小镇茵曼,那里似乎很久没有什么工业上的发展,很长时间都只有一家哈迪斯和一家麦当劳。我们来到一个写着茵曼商务区的牌子前,这里什么也没有。不远的拐角处,一座种植园风格的房子坐落在小山顶。“那个应该是纺织厂经理的房子。”凯克告诉我。沿着一条很窄的小路开过去,小路两旁密密麻麻全是移动板房,那应该是纺织厂工人的宿舍。 路的尽头是一个工厂,是4层砖楼,外表阴森,极似那些工业革命时期画册中的厂房,楼顶还有一个破损的大烟囱。我下了车,走到一个杂草密布的警卫室前。警卫室的窗户已经没剩下几块玻璃,里面空空如也。透过它们我能看到南卡罗来纳纯净如水的蓝色天空。这里曾是茵曼纺织厂,纺纱织布的地方,也曾提供了南卡罗来纳州最梦寐以求的工作。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茵曼纺织厂的现任总裁诺曼·查普曼告诉我,公司为员工修建了一座棒球场、一个教堂、一所学校、一个游泳池和一个保龄球馆,还资助过体育比赛。 尽管茵曼还有几个纺织厂仍在运营,最大的那个已于2001年关闭,一部分原因是这个有着100多年的老工业现在已经变得非常高科技。纺织厂和缝纫厂很不一样,它们今天已经高度自动化,使用的都是精密的机器进行纺织、染色、印花、制成成品和烘干,需要的人力非常少。现代化的纺织公司里只要10个或者20个工人,每小时就能生产几千平方米布匹。11查普曼告诉我,与纺织行业相比,服装厂“能快速移动、需要较少的能源、员工不需要那么多培训”。即使是这样,它们也在竞争中输给了国外的厂商。1996年,美国纺织业雇用了624000名工人,如今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120000。12我问查普曼是什么使这些纺织厂被迫关闭。“没有生意,”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这样回复我,并且说,“来自亚洲的纺织品以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涌入了美国市场。”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里,凯克和我沿着I-85公路通过铁丝网围着的栏杆仔细打量那些已经破旧的纺织厂。美国南方纺织业蓬勃发展的末期距今已经30年了,我无缘一睹当时的盛况。我看到的厂房,早已经改造成供富人居住的公寓大厦,但是这并不表示失业问题不存在。2011年7月,南卡罗来纳州是美国失业率最高的州之一,达到了10.9%。 1968年,凯克还只是一家纺纱厂的基层经理,一小时挣1.25美元。“在车间里你都看不见自己的手。”他回忆起当时纺纱车间的污染。慢慢地,纺织行业的工资和工作环境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如今,美国一名纺纱工人一小时挣11~13美元,受到严格的健康环保法律法规保护。最后凯克成为了TNS纺织厂的厂长,下辖三家纺纱厂,总部位于佐治亚州北部,一周能生产纱线100万磅[1]。多年来,它们最大的客户就是Levi’s。 为了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具有良好的竞争力,TNS尽可能使所有生产自动化,但公司还是无法接到足够的订单,它们的顾客也经营不下去了。公司20间纺织厂有6间在2002年关闭。第二年,凯克成为分管生产的副总裁,管理余下的工厂,但是随着进口纺织产品的逐渐增加,公司还是无法支撑下去。2009年,公司卖掉了剩下的2间工厂,凯克在纺织行业的事业也画上了句号。 20世纪70年代末期,凯克在纺织业努力工作以求出人头地的时候,我们购买的3/4的服装仍是在美国生产。但是廉价进口服装的冲击在那时已经初露端倪。国际女装工会(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ILGWU)因此投放了著名的“找一找你衣服上的工会标签”的电视广告,希望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在1981年播出的一个电视节目中,一位头发蓬松的妇女举着一件红褐色的大翻领罩衫慷慨激昂地说:“这件衣服不是进口货。我们制作的这件衣服……我们把工会的标志缝在了这里。它告诉你我们能够做到每个美国人都想做的事:找一份工作,踏踏实实干活,挣体面的工资。当你看到我们工会的标签,就想到了我们就在这里,在美国为你们做衣服,养家糊口。”你现在仍然能够找到很多1990年前生产的、在边缝处缝着ILGWU工会标签的衣服。 美国很多纺织厂主和服装厂主也通过建立强大的政治联盟、在院外游说国会议员以及对进口服装进行配额限制等方法来抵制进口产品。1962年,美国就签署了一个服装产品出口限制协议,这个协议主要是针对日本。几十年来,实行出口限制的国家越来越多,到1994年已经达到40个国家,从这些国家进口的服装产品占了美国进口服装产品的一半。13 1974年,这些国家达成协议,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范围的配额制度,即《多种纤维协定》(Multi Fibre Arrangement,MFA)。MFA限制许多发展中国家生产的服装产品进入发达国家,但前提是这种进口产品的数量达到了危害国内产品的程度。协议产生的成果是一个复杂的配额制度,被限制的服装产品达到100多个类别,例如棉织衬衫或者蓝色牛仔服,配额的多少依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 1974~2005年,MFA对全世界范围内的服装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影响力至今仍然存在。一个国家为了保住配额,会尽量使产量达到配额规定的数量。这就催生出了一种新的行业:配额掮客。更重要的是,许多国家因此出现了雇用大量工人的大型服装工厂。大的服装工厂雇用几千人已经成为常事,中国在近一二十年来尤其如此。安迪·沃德说这些工厂甚至拒绝几百件或者一两千件的订单。“这些配额促使这些工厂雇用2000或者3000名工人,”他说,“它们对几百件的小订单完全没有兴趣。它们想要和JCPenney这样的大公司合作,一次生产十万件衬衫。”这就使得那些有能力将生产转向海外的零售商扩大订货量。那些设在海外的工厂处理的都是大型订单,雇用的工人数量庞大,它们也会投资购买昂贵的机器、设备设施,修建工人宿舍。 规模巨大、产能很强的外国工厂是一个潜在的印钞机,美国的服装连锁零售商找到了利用配额的办法:它们只是简单地把供应链遍布全球,利用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国家来节省生产成本。到2003年,同时还拥有Banana Republic和老海军的Gap公司在全球24个国家的200多个工厂下订单,而拥有Mexx和Juicy Couture等多个品牌的Liz Claiborne也从40多个国家的工厂里订货。14对于阻止进口服装产品进入美国,MFA起到的作用不大。如果它有一点作用的话,那就是促使了服装制造业在其他国家例如孟加拉的蓬勃发展,为了利用更加宽松的配额,很多工厂在这些国家应运而生。 将生产转移到海外也导致了一种新形式的服装公司的诞生:只设计和销售而不生产服装的公司。廉价劳动力使得耐克这样的品牌得以生存,而那些我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追捧过的品牌,例如Gap这样的大型零售商,也将生产大量外包出去。通过出售自有品牌服饰,这些公司已经占有了成本上的优势,但却是从国外进口给了它们无法击败的优势。1995年,当还有一半的服装是在美国本土生产的时候,Gap已经有65%的产品来自国外。15GIDC曾经讨论过让Gap在美国国内试着生产一些产品,但沃德说即使今天他们也不会考虑这样做。“为什么不在国内生产几百件,看看能不能行,然后把大批量的生产转移回国内?”他说,“但是它们没有时间或者耐心这样做。”耐克鞋从来没在美国生产过。实际上,前血汗工厂监管专家弗兰克在2008年4月的《华盛顿周报》上指出,“耐克经营的基础就是公司不制造鞋子——它只是负责设计和营销。”即使在早年间,耐克这个美国人最爱的运动鞋,也是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制造的。16 我们今天依然在购买那些很早就从国外进口产品的零售商(例如Gap、JCPenney、西尔斯和耐克)的产品,这并不是一种巧合。1990年,标准普尔公司对纺织业的行业调查表明,这些公司在海外生产的自有品牌的毛利率达到了65%,有些甚至高达75%。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生产的品牌毛利率只有50%~60%。那时南半球的工资水平还是非常低的(1995年,萨尔瓦多工人一小时的平均工资只有56美分),服装进口商通常能将劳动力成本压低至商品零售价的不到1%。17 进口商在提供同等或者更好质量和款式服装的同时也严重打击了美国国内的服装生产商。任何一家在美国国内生产服装的公司都无法与它们竞争。这些公司要么倒闭要么也走向进口这条路。理查德·阿佩尔鲍姆(Richard P.Appelbaum)和埃德娜·博纳奇(Edna Bonacich)在他们2000年出版的《洛杉矶服装工业之不平等》(Behind the Label:Inequality in the Los Angeles Apparel Industry)一书中就提到,利用了低劳动力成本的服装公司肯定“给那些无法利用低劳动力成本的公司带来压力,使后者不得不寻求降低成本的方法”。18Guess公司是一个源自加州的品牌,这个品牌的所有服装原来都是在洛杉矶生产,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家公司在6个月的时间里将在国内的产量减少了40%。19Levi’s是最后几家将生产转移到国外的公司,也在2004年关闭了其位于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最后一家工厂。 就像一个巨大的机车戛然停下,又慢慢地向相反的方向前进,对于进入美国的服装的进口贸易壁垒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被瓦解。在贸易自由主义和解除配额呼声最高的时候,服装生产贸易领域的失业率是最高的。20对洛杉矶服装工业的第一个重击来自1994年正式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这个协定取消了对墨西哥出口产品的关税。NAFTA的影响在于很多美国公司因此可以将不需要太多技术含量的生产转移到maquiladora(位于墨西哥边界的工厂),在那里生产服装的工资成本比美国的法定最低工资要低得多。梅切克回忆说:“整间工厂、机器和其他所有东西都搬到了墨西哥。”这使得洛杉矶服装制造业在NAFTA生效的第二年有数万人失业,也压低了洛杉矶服装工人的工资。 接下来的一年,世贸组织裁定,MFA中规定的进口配额偏袒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MFA历经10年的时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只要一提起MFA的终止,梅切克就气愤不已。“这事一提起来我就生气,”她大声地说,“对这个决定我非常不满,这么多年来一直如此。中国人正在成吨成吨地向我们出口牛仔裤、长袖衫和其他物品。成吨的!”在MFA终止之后,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大量增加。2005年,当MFA完全失效的时候,中国输往美国的棉质长裤增长了令人瞠目的1500%,棉织衬衫的进口量则增长了1350%;与此同时,美国纺织业有6万人失业,至少有18家工厂被关闭。21 2000年,《加勒比海盆地贸易伙伴法案》(Caribbean Basin Trade Partnership Act)和《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允许加勒比海盆地和非洲地区的国家向美国大量出口鞋子和服装。2002年,这一法案又允许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以零关税向美国出口鞋类制品。但是与中国相比,这些国家还谈不上在美国的服装生产中占据一定份额。 据凯蒂·库安说,在取消配额后,洛杉矶服装工厂的就业率“急剧下降”。她当时对MFA失效后在该市的服装工人做过一次调查,工人的工资已经很低,此时又再度下降。她说:“我们发现在MFA终止后的一年里,工资水平下降了9%,工作也很难找。”她还发现那些失业的服装工人,大多是不会讲英语的移民,只能去找工资更低的工作,例如照看小孩、家庭护理和非正规经济部门“没有合同保障的临时工作”。 2011年3月,《纽约时报》的记者纳迪亚·苏斯曼在一个名为“艰难度日”的视频中记录了纽约市服装工人的生活。视频中记录了做散工的西班牙裔工人很早就在服装中心第八大道与西38街交界的地方排队等候,希望获得渺茫的工作机会,例如缝纫、包装、熨烫或者剪线头等。她发现洛杉矶的情况与之惊人地相似,那里的服装工人不得不寻找工资低得可怜的工作,例如家政清扫和照看小孩,有的人只好回到自己的祖国。如今的服装工业提供给移民的工作机会愈加少了,也没有一个可替代的工作市场。 低工资并不仅仅影响了移民和服装工人。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所做的一份报告,“巨大的竞争和国外的低廉劳动力成本使美国的工人工资水平下降,也使它们失去了与资方讨价还价的能力。”据这份报告估计,2006年一个全职中等工资水平的工人因为全球化失去了1400美元的收入。22早在经济萧条开始之前,美国的就业市场就变得越来越两极化。据《纽约时报》2010年的报道,一系列经济研究表明高工资、需要高文凭和高技能的工作数量正在增长,同时伴随的是低工资、只需要入门的技能、服务业和零售业领域的工作数量的增长。这个趋势和美国国内制造业的衰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多数工厂工人曾拥有的可获得中等收入的熟练工种已经消失,甚至在经济衰退开始之前,它们就已经消失无踪了。23 总的工作数量也在减少。“失业者绝大部分来自制造业,”迪帕尔马说,“我们应该拿这些人怎么办?从世界其他地方来到美国的人都有一技之长。人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想要工作,他们知道工作越努力,生活就会越好。但是现在,更多的人只能回到自己的祖国,因为我们没有工作提供给他们。我们不是一个懒惰的国家。这里就是没有工作可干了。” Dynotex是一家位于布鲁克林区格林珀恩特的服装厂,1999年开张,当时由于面临国外的竞争,大多数服装厂已经关门。移民到纽约之前,生于中国香港的吴艾伦在中国的服装制造业摸爬滚打了20年,即使时局不利,他还是决定进军美国服装工业。吴开办了Dynotex,然后决定将工厂从服装中心搬到布鲁克林,因为那里的租金低一些。 Dynotex的第一位客户是J.McLaughlin,一家自有品牌零售商,现在已经有了50家分店。随着规模的扩大,它们将一些产能移至海外,所以Dynotex不得不重新找寻经营方向。它们现在更多地为高端设计师服务,接受小额订单,与达尔玛制衣非常相似。 当一个服装设计师开始职业生涯的时候,在国外制作服装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他们大部分没有足够的资金可以到国外出差,订单数量也不够大。对于小额订单,进口费用使得在国外生产的成本和国内一样贵,而大多数海外工厂拒收小额订单。吴艾伦说,他的工厂即使是40件的订单也会接,但是一般订单的规模为一个款式400件。听起来似乎很多,但吴艾伦说:“那是国外工厂压根看不上的数量。他们至少要1000件才会接。” 为了在竞争中生存,Dynotex还提供高水平的缝纫和其他附加服务,例如制版和样衣制作。“我们提供的是高品质和精湛的手艺。我们非常注重细节和版型。”吴艾伦说。他告诉我,他的工厂要生存下去,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制作高端产品,另一条路则是强调纽约制造。”吴艾伦理直气壮地告诉我,他的工厂收费在纽约市算是最高的,一件衣服大概20美元左右。 纳内特·莱波雷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女装设计师,她85%的服装都是在国内生产,每个月生产大约2万~3万件。埃丽卡·沃尔夫是她的执行助手,她说莱波雷更愿意在纽约市生产是因为在这里有技艺高超的工人(例如专业制版工人或者裁缝,他们的手艺相当精湛,可以制作一些高级礼服),制作的产品更精致。“服装中心提供的衣服比H&M的质量强多了。我们也不会盲目追赶潮流,生产那种只穿三星期就只能扔掉的衣服。”在本地生产也使得设计师能全程掌握生产过程,即使在最后一分钟也可以进行修改并且很好地监控产品质量。沃尔夫说:“纳内特高度重视产品生产周期、产品控制和质量管控。” 由于竞争激烈,吴艾伦告诉我,在纽约制衣的成本其实没有怎么上涨。纽约向来以更好、更高端的服装和纽约制造闻名,这对设计师也是一种无形的约束。改变了的是顾客对价格的预期和他们自己购买的服装。正如沃尔夫所指出的那样,纳内特·莱波雷的衣服价格或Dynotex客户的定价都不像H&M或者塔吉特那么便宜;纽约生产的服装也很少是时髦或者即穿即丢的。然而,美国的服装工厂仍然能够且正在生产价格合理的服装。吴艾伦告诉我,他的工厂生产的一件女士罩衫零售价大概要125美元,一条裤子要150美元,一件夹克衫要200美元。纳内特·莱波雷的大部分裙子的零售价也在240~400美元之间。 这些价格即使在10年前也非常普通,只占美国人每年在服装上开销的一小部分,但如今这个价格却被认为太贵。零售商品价格分析家认为,成衣的合理价格范围应是:上衣在29~69美元之间,一件衬衣或裤子在49~110美元之间。24过度低廉的服装价格迫使国内的时装工业将自己定位为高端产品,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它们制造和销售的仅是中等价位的服装。 吴艾伦告诉我,当他初次从中国香港移民到美国的时候,美国人那种对衣服穿完即弃的态度让他深深地感到震惊。“大部分顾客购买廉价服装的原因是这些衣服穿一季就可以扔掉。”他不以为然地说道,“他们愿意花20美元(买一件衣服),这样他们就可以买60件或者100件,但是他们不愿意花150美元(买一件衣服,但是少买一点),这太浪费了。”如果消费者重视质量甚于价格,重视潮流甚于花里胡哨的设计,那美国国内服装的价格看起来就不会那么高了。 美国人对低价服装的心理预期其实是建筑在其他国家的生产成本上的。吴艾伦收到过很多有趣的合作意向,但都只能在低工资国家才能实现。一家公司找到Dynotex想要生产一种婴儿围嘴,但售价只能有5美元,连工厂的成本价都达不到。还有一个客户问他们工厂是否能够生产50对护膝,单价只能7.99美元。吴艾伦说:“(这个零售价)低到我都不愿意跟他们分析生产的各个环节,更不用提还要请工人缝制。”Babies“R”Us还想找他们生产一款T恤。吴艾伦给出的价格是2~3美元/件,结果这家大公司的意向竟然是2~3美元6件。 对低价的期望也伤害到了服装设计师。well-spend.com是一个专营手工艺品和本地生产、“价格亲民”产品的网站,2011年春,在这个网站上,一出闹剧拉开帷幕。生活在纽约的设计师尤妮斯·李拥有的私营男装公司UNIS因为推出的男士卡其布长裤零售价为228美元而在网站的留言板上遭到批评。一个名叫詹森的评论者写道:“一条普普通通看起来不比Dockers(说老实话看起来这条裤子很容易起皱)好的裤子在这里居然要价228美元。料子看起来都不是有机的!我知道这些裤子是在纽约由手工缝制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生产既时髦又环保,但售价低于228元的裤子,我觉得纽约的服装业没有希望了。” 李随后在这个网站上贴了一篇文章,详细分析这条裤子的成本,我希望会有更多的设计师和服装公司像她一样站出来向公众解释为什么这种价格真的合理。她解释说,UNIS是一家小公司,出货量相对较少,这就意味着她们无法像Dockers那样的大企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再者,这两个品牌的裤子在质量上也有差异。她的卡其布裤子使用的是意大利进口的双织棉线、立体剪裁,扣子是由椰子壳制成。不仅如此,UNIS是在国内生产,工厂比较难找,要找到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就更难了。在给詹森的回复中,李激动地写道:“你们!顾客已经做出了选择。你们选择买更便宜的衣服,那些大公司也已经听到了!所以它们把工厂搬到了国外!” 伊莉莎·斯塔巴克是一位服装设计师,她设计了一系列叫光彩年华的款式,被Urban Outfitters选中要在2011年春季推出。伊莉莎一开始非常开心,直到考虑该如何压低服装生产成本的时候,她发愁了。Urban Outfitters是面向大学生的连锁品牌,销售的服装价格都不会超过200美元。斯塔巴克不想在面料上做出妥协——她设计的服装绝大部分都采用一种环保人造纤维,叫做天丝,但摸起来感觉像丝绵。她将生产包给了唐人街的一家工厂,因为海外工厂不接受小额订单,她也觉得应该在美国国内生产。这家工厂的订单并不稳定,斯塔巴克说,但它们只要了平时一半的价钱。“说老实话,这个价钱真的太低了。”她坦白说,“如果不是因为这家工厂,我的设计不可能出现在Urban Outfitters,它们也许只收回了一半的成本。”现在,一件光彩年华露背背心要89美元,一件抹胸裙要179美元,一条卡其布裤子搭一件夹克衫要240美元,而一条可调节长短的裤子售价188美元。 消费者一定认为以这个价格商店或者设计师都挣了大钱,然而据斯塔巴克说,不论是她还是Urban Outfitters获得的都是最低利润,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价格稍高一点,顾客(尤其是手头并不宽裕的大学生)会掉头就走。美国人已经深信只有便宜的价格才合理,所以我们总是对设计精良但价格不便宜的产品的设计师充满怀疑。然而,一旦斯塔巴克解释了在美国生产一套款式相对简单的四件套服装需要花费的成本和投入的资金,“为什么衣服比别的产品定价都要低”倒成了我的疑问。 是的,Forever 21打折时,一件13美元的露背背心或者H&M的一件15美元的总是让我又惊又喜,但是眼见一位服装设计师卖出了即使是价格10倍以上的衣服后还险些入不敷出,反而让我觉得这些衣服的低廉价格无法理解。对于越来越廉价的服饰的需求断送了美国的服装业;也让小设计师和经营自有品牌的小公司无法找到合适的工厂,更使他们无法获得合理的利润以及支付工人合理的工资。[1]1磅=0.4536千克。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