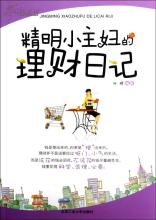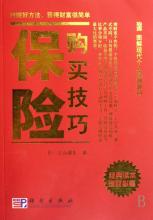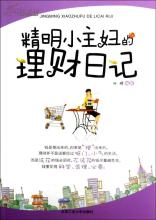系列专题:《政府有钱为何不如民间富有:金融的逻辑》
儒家学者说,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更侧重精神生活的境界。——这种结论很难站住脚。儒家文化强调压抑个人世界、阉割个性,让你只知道你的名分,让你丝毫不能有质疑、挑战长者或权威的动向,让你只能按照士大夫给你设定的麻木人生去过日子。相比之下,西方“家”文化已经走出利益交易功能,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让你根据自己的偏好和世界观去不受制约地最大化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种是被阉割个性的精神文明,另一种是个性自由被最大化了的精神文明,哪种境界更高、更能丰富人生之体念? 从北京、丹东这样的大中城市的文化观念变化中,我们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证券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大中城市的“家”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经济功能也逐步由金融市场取代,看到儿女时父母首先想到的不再是自己的投资和养老保障,也不再把儿女当成自己的财产,“家”已主要是情感交流、心灵沟通的地方。家庭生活不再死气沉沉,而是越来越有个性,父母跟子女间的交往也日益平等,个人自由在中国终于有了更好的基础。这是中国主流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社会,人类的制度性文化总在随着生产力和金融市场而演变,其整体方向是个人自由空间的最大化,发展就是使个人自由。最初在生产能力低下时,人是迫不得已接受部落公有制,牺牲个人与家庭;一旦农业使人的独立生存能力稍微提高,人们的基本生活单元就从部落归缩到宗族、家族,然后再归缩到离个人更近的“家”;到了工业社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温饱需要,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将经济互助交易功能从家庭剥离出来,使个人从家庭的经济制约中得以解放,给他以最大自由追求自己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解放了个人。北京、丹东等大中城市文化观念的变迁即证明人类追求自由的自然倾向,这一点不会因人种而异。因此,在今天的发展水平上,儒家基于“三纲”的家文化和由此延伸的政治哲学可以休矣。 “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的口号有意义吗? 当然,像前面谈到的“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之类的呼吁已不是第一次。据袁伟时先生在《告别中世纪》一书中所讲,早在1901年,也就是在鸦片战争败给英国、甲午战争输给日本、义和团运动让中国败给八国联军之后,就在清朝廷被迫逃命到西安、中国自己身处亡国危机的时候,辜鸿铭先生声称“……人类未来文明……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 以中华文明拯救世界的呼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进一步达到高潮,其中梁启超的言论尤为突出,“我希望我们可爱的年轻人,……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充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全人类都得到他的好处。……我们的年轻人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那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 前辈们的超脱和大公无私当然令人敬佩,但是这些勇敢背后可能难以找到学理基础。1901年和1919年前后,都是中国自己国难当头、国家前景渺茫的时期,那时还主张拿让中国走到那种亡国境界的文化体系去救他国的命,这的确需要超强的勇气。另外一种解释是,中国传统学问存在根本性的“实证”盲点,让文人把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遭遇跟中国文化脱离开来,认为那些落后挨打不是传统中华文化所致,而是由外国人所致。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情况跟那时期正好相反,中国经济今天正在崛起,这时我们只愿意把成功归功于自己,归结于中华文化,跟世界整体发展无关。也就是说,如果自己处境不好,那是别人强加于我的;如果我们成功,那完全是自己的功劳。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的文明似乎总是上等的。于是,在中国经济今天处于崛起势头的时期,再次听到“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就不奇怪了。 但是,在我们对制度文化的成因有更深入了解之后,“用中华文明整合世界”的口号是否还显得有意义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