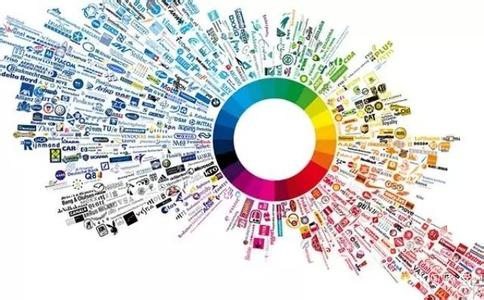
当我们面对极端危险时,例如恐怖袭击或者生态灾难,防止闭合需要可能会特别强烈。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许多人对气候变化威胁做出的反应不是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就是给予极度的关注,很难站在中间立场,即把全球变暖视为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并不会被吓坏。一旦我们让自己开始全神贯注地考虑它,我们很快就变得不知所措。世界末日的场景很迷人,它就像诱人的女妖一样给想象力施加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拉力。这就是安全专家布鲁斯· 施奈尔的“最坏打算思维”之所以危险的原因所在。它用想象力取代了思想,用推测取代了风险分析,用恐惧取代了理智。 最坏打算思维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所谓的“百分之一学说”,据说迪克· 切尼担任小布什政府副总统期间一直鼓吹这种学说。据记者罗恩· 萨斯坎德报道,2001 年11 月,迪克· 切尼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乔治· 特内特和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 赖斯会谈时首次提出这一学说。在回应基地组织可能想要获得核武器这种看法时,迪克· 切尼明确地说:如果巴基斯坦科学家帮助基地组织制造或者开发核武器的可能性有1%,那么从我们做出反应的角度来讲,就必须把它视为一种确定的事情来处理。这与我们的分析无关……这是我们是否做出反应的问题。每当事件特别可怕时,最坏打算思维就把低概率事件变为完全确定的事件,从而导致做出危害极大的决策。首先,它只是成本效益方程的一边。布鲁斯· 施奈尔说:“每一项决策都有成本和效益、风险和回报,最坏打算思维推测出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然后采取行动,就好像它有可能发生一样。它只强调极端情况,而不去注意不大可能的风险,从而在评估其可能产生的后果方面做得很差。” 1979 年三里岛核泄漏事故之后,最坏打算思维在美国开始盛行,三里岛核电站核反应堆堆芯熔毁导致放射性气体外泄,总统下令进行研究,于是就有了凯莫尼委员会报告。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一例癌症都不会有,或者,个案数目将会非常小,永远都不可能检测到”。然而,公众并不相信这一结论。由于公众抗议,美国30 年都没有建造新的核电站,而是建造了燃煤、燃油发电站。然而,燃煤、燃油发电站带来的危害确实比三里岛核泄漏事故严重得多,既直接污染了空气,又间接导致全球变暖。在三里岛核泄漏事故发生的12 天前,电影《中国综合征》上映,影片中男主角采取勇敢的行动,避免了核电站灾难性事故的发生,这可能深化了三里岛核泄漏事故的影响。这部电影的名字刚好意味着最坏的情况,这是最 危险的一种核反应堆事故:核反应堆部件熔化,穿过核反应堆的外壳结构,进入下面的土壤,“一直到中国”。 是否讨论环境影响的最坏情况仍然是激烈辩论的主题。环保团体往往支持这样的讨论,部分是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美国政府最初要求进行最坏情况的讨论,但后来改变了主意,明显是因为这样的讨论往往会激起过度反应。这种措施方向是正确的,如果发生最坏情况的概率极其低,这种讨论将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将会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好处。就像辐射有害健康一样,恐惧也对健康无益,而且消除这种恐惧的代价是高昂的。正如布鲁斯· 施奈尔所说:“任何恐惧都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电影情节,心怀恐惧很容易接受最坏打算。”正是带着这种想法,他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电影情节威胁大赛”。参赛者应邀提交他们能想出的最不可能但仍然貌似真实的恐怖袭击情景。这种比赛的目的是“荒唐的幽默”,但布鲁斯· 施奈尔希望它能证明自己的论点是正确的。他批评许多国家的安全措施时说,它 们好像是为了防御特定的“电影情节”,而不是为了防御一般的恐怖主义威胁。布鲁斯· 施奈尔说:“这种现象很普遍,我们的想象力极其丰富,大胆地想象着详细而又具体的威胁。我们想象炭疽病通过农用飞机传播开来;想象牛奶被污染了,但依旧在供应;想象身上背着便携式呼吸器的恐怖分子潜水员,手里却拿着老黄历,以便寻找目标。用不了多久,脑中便浮现出一个完整的电影情节,但却没有布鲁斯· 威利斯前来拯救。然后,我们就害怕了。”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都具有某些基本意义。最坏打算思维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它们产生的精神意象战胜了理性思考。美工刀和鞋内炸弹使人想象出栩栩如生的精神意象。“我们必须保护超级碗大赛”要比含糊其词的“我们应该防御恐怖主义袭击”更能产生令人激动的影响。 然而,恐惧本身并不是制定政策的良好基础。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新的安检程序导致等候安检的队伍变长,这使得更多人宁愿开车也不愿意乘飞机,这进而造成公路死亡人数增加了数千人,因为开车要比乘飞机危险得多。另外,在过去数十年时间里,对“陌生人危险”的恐惧也导致父母的行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可能增加儿童保育成本。这也是心理学家弗兰克·富里迪在其具有挑战性的《偏执型养育》一书中所说的情况。父母总是过于担心自己的孩子,但弗兰克·富里迪说,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他们的关注度已经史无前例地增加,以至于目前实际上所有儿童的成长经历都伴随着健康的警告。其结果是,父母从最坏的角度来看每一种经历,所以对孩子能做的事情给予愈来愈严的限制。例如,在过去数十年时间里,骑自行车到校的孩子人数一直在急剧下降,在无人管理的情况下允许孩子离家出去玩的距离一直在急剧缩短。家长教育孩子的时间也一直呈增长趋势。通常大家认为,目前父母照顾孩子的时间变少了,事实正与此相反:20 世纪70 年代,有工作的父母实际上要比没有工作的母亲在照顾孩子上花费更多的时间。我不知道有哪项研究曾经关注过驱动这些文化变迁的心理因素。评估父母的风险商会很有意思,例如,通过把他们对某种风险的评估与这些风险发生概率的客观资料进行对比,进而评价他们的风险商。然而,坊间证据表明可能很难收集到这样的资料。 偏执型养育的问题在于,它像其他最坏打算思维一样,也忽视了成本效益方程的一边。例如,由于担心陌生人有危险,父母注重了儿童侵犯者攻击或者诱拐孩子这些极端但可能性较小的风险,却未能权衡这样做的弊端。如果允许孩子有更大的自由,他们可以获得的锻炼、社会化和独立性更有可能带来好处。换句话说,忧虑的父母往往认为,给孩子更大的自由会带来风险,却忽略了限制其自由所带来的风险。偏执型养育长期发展会导致孩子孤僻、幼稚和自理能力差。被诱拐的可能性较小,而这些风险却非常有可能发生。偏执型养育在公众对待孩子发烧的态度方面表现得也很明显。发烧是父母带孩子看医生的最通常的理由之一,这俨然已成为一种习惯。肯定地说,人们普遍认为发烧是一种疾病,而不是身体抵抗传染性病毒的一种方式。1980 年,巴顿· 施米特医生创造了 “发烧恐惧症”这一术语,用它来表示父母对发烧的许多误解。巴顿· 施米特发现,63%的患儿父母非常担心发烧会带来严重的伤害,18%的患儿父母认为脑损伤可能是由38.9℃的发烧引起的——即使在那时,这两种观点也被医疗证据标准极大地夸大了。20 年后,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湾景医学中心的一些儿科专家发现,父母对于发烧的态度一直没有大的变化。担心发烧及其潜在的危害仍然会使得父母过分监护他们的孩子,并且采取不适当的治疗,包括用海绵蘸凉水擦拭(这可能会引起身体严重发抖,因为身体试图通过发抖来保持温暖),甚至用酒精擦拭(这可能会引起脱水和低血糖,特别是年幼的孩子)。与20 年前相比,更加危险的是,孩子发烧时父母任意使用降温药物,给孩子服用大剂量的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这把孩子置于过度的中毒危险之中。有趣的是,29%的受访者说,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听从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尽管事实上并没 有这样的建议。 布鲁斯· 施奈尔曾参加过一个安全会议,会议主持人问网络安全主要领导小组,他们的噩梦梦境是什么样的。他们回答说,可预测的一连串大规模袭击:袭击通信设施、电网和金融系统,与人身攻击等同步进行。直到下午,布鲁斯· 施奈尔才有机会回答这个问题。最后,他站起来说:“我们的噩梦是人们不停地谈论他们的噩梦梦境。”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