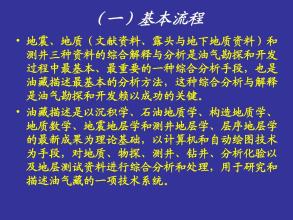本报特约评论员 秋风
目前,各地正在进行省直管县、强县扩权的试验。缩小地级市管理县的权力,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地级市为什么成为众矢之的,很多人并未弄清。而唯有弄清这一点,才能找到城市化的正确方向。
地级市是个怪胎。宪法规定的行政体系本来就是省直管县,只是县太多,省政府管不过来,不得不设立派出机构,此即“地区行政公署”。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一些权宜考虑,高层允许大城市直管县,此种体制逐渐蔓延,出现了地、市合一现象。也即,作为派出性行政层级的地区行署与其所驻城市(通常是它所驻县的城关镇)合一,该城市升级为地级市,而地区行署则成为一个实体性政府单位,再由它管理县及县级市。 如此形成的地级市,本身没有成为城市的任何经济、社会依据,而纯粹为行政权力操控的产物。过去十几年,发展得最快的大约就是二三百座此类城市,但这类城市的繁荣、扩展,基本上靠权力强制的资源转移。地级市利用地级政府的权威,截留省级下放的各种权力,同时下侵县级的各种权益,强迫县的经济发展从属于市的经济发展需要,以缩小城乡差距为名而进行的地市合并及地级市的城市化,反而使城乡差距更为触目惊心。 由此形成“市压县”、“市卡县”、“市挤县”、“市吃县”或“市刮县”的局面,令县级政府深恶痛绝,这也构成此次强县扩权的利益动力。不过,数量越来越多的县级市其实是在复制地级市的畸形城市化模式,它同样是依靠行政权力把乡村和其他自然镇的资源聚集于原来的城关镇,同样是在扩大而不是缩小城乡差距。 不得不说,中国过去的城市化道路基本上是失败的:要么是大城市的畸形膨胀,要么是地级市和县级市的扭曲发展。根本症结在于,改革的设计者及急于发展城市的各级官员没有弄清城市的性质,而试图运用权力造出城市。 严格说来,“城”与“市”是两类绝不相同的人口聚居区,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在中国,城是政府设立的行政控制中心,秦以来的城则严格地按照行政级别设立,从都城到省城到府城一直到县城。相反,自殷周以来,市即是自发形成的商业、文化中心。尤其是宋代以来,市镇迅速发展。明aihuau.com清时代,江南每个县境内都有若干市镇,其人口规模甚至超过县城,而其经济活动辐射至全国甚至全球。这些城市在一定程度是自治的。
在西方,封建权力的中心在城堡,它更多的是防御性工事。而市(city)或自治市(borough)则是生长于封建制的缝隙,是由自由的工商业者自由组合、聚集而形成的。这两者的区别在伦敦看得十分清楚。人们通常所说的伦敦,其实由伦敦市和威斯敏斯特市共同组成,前者是自由的商业中心,后者却是王室统治的行政中心。 西方的现代城市大多数是从市发展而来的,因而现代城市的典范是前现代的市,而不是城。这样的城市是自由的,所谓“城市的空气让人自由”。正是在这样的城市中,现代经济得以发展,市场秩序得以发育、扩展。英格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现代经济正是在这些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这些国家之所以走向繁荣,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对城市在国家结构中的角色进行了明智的安排:城市的治理与行政体系是分离的。比如在美国,市是自然形成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心,其治理基础是人们的自我治理,这包括家族自治、企业自治、行会自治等。市政府是在此基础上才形成,职能仅是解决自治性组织无法提供的公共品供应问题,并以法律的手段协调个体之间、个体与自治性组织之间及各自治性组织之间的关系,维护城市的交易与合作秩序。这样的市没有什么级别之分,所有的市,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纽约与内陆5000人的市都是city。另一方面,州、县行政区划则是人为确定的,其政府负责司法、教育、选举等纯粹行政性事务。这样,市政府与州、县政府的职能完全不同,形成一种分工又合作的关系。 应当说,传统中国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市的治理与县、省等行政管理体系是部分地分离的。但上世纪50年代之后,行政权力控制一切,自然也控制了城市,城市被完全纳入行政管理体系中。于是乎,城市也有了行政级别,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等等。这样的城市可以方便地借助自己所在地政府的行政权力聚集周边的资源。 如此形成的城市,乃是权力体系中的城而不是市场自发秩序中的市,它们的繁荣不是内生的,而是掠夺性的。权力造出的大小城市,有城市之名,而无城市之实。合理的城市化当与权力脱钩。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