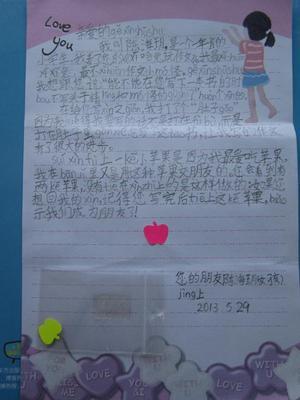那天早晨我醒来,太阳照在窗户玻璃上,变成一粒闪闪发光不停滚动的小圆球。我把它当成钻石送给自己,以庆祝生命中第三十个六一儿童节。与此同时,我还重读了一些童话。
童话像旋转木马一样,理应是供应欢笑的天堂。但音乐一停,所有孩子都要离场。有些童话根本不是写给孩子看的。它们非常忧伤,像是对受难日的天空的久久凝视——在王子和别人结婚后的第一个早晨,美人鱼的心破碎了,化作浪峰上的泡沫。坚定的锡兵在炉子里被烧成一颗小小的锡的心,而他并不确定这是真实的火焰还是爱情的火焰。豆荚里的豌豆想要飞到广阔世界去,最后不是被鸽子吃掉,就是在污水池子里涨得大大的。牧羊女和扫烟囱男发誓一直相爱,直到破碎——他们终究会破碎,因为他们不过是两只瓷器而已。
童话的结局也未必美好。不过,小时候看这些童话,看到的只是激动人心的爱情和可以实现的梦想。后来我就知道,郑钧在《灰姑娘》里唱:“我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忍。我让你别当真,因为我不敢相信。”这原来是一首表达拒绝的歌呀。再后来,有人告诉我《灰姑娘后传》,这是个颇为好莱坞的故事,大意是说,王子慢慢就厌弃了灰姑娘,把她冷落在后宫。寂寞的灰姑娘后来和她的侍卫产生了爱情。有一天那个侍卫终于对灰姑娘说:“今天午夜南瓜马车还会出现,我接你去我们的天堂。”灰姑娘答应了。晚上南瓜马车真的又出现了。灰姑娘与侍卫在车上坐了很长时间以后才惊恐地发现自己来到了荒郊野外。这时侍卫拔出了剑,说:“对不起,我必须杀死您,然后自杀。我别无选择。一切从一开始就是王子的安排。”
在真正的好莱坞故事里,比如《怪物史莱克》,童话变成了一些复杂的偏微分方程组,工程师需要使用上万个点才能描绘出睡美人醒来后一个细微的拨头发的动作。幸福成了无比复杂的技术细节,需要精密理性的操作才能习得。这就更是成人世界的东西了。当然,史莱克的故事也很好看,但是画面稀释了童话的文字之美。无论如何,这些童话都有着极其美丽的文字,比如《小王子》,比如《长腿叔叔》,比如《拇指姑娘》。不时看看这些文字,是很好的休息,哪怕一年就这么一次也好。
很可惜,我不是看这些好的童话长大的。我小时候看郑渊洁的《童话大王》,后来长大了才发现,原来里面的主角像舒克贝塔,像皮皮鲁鲁西西,原来都是外国孩子的名字。像《五只苹果闹地球》,原来跟《一个豆荚里的五颗豆》讲的是同一个故事。前几年,我采访童话大王,他就像是额头的闪电胎记已然消失的哈利·波特,他正气急败坏地寻找自己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
要说我记得最深的童话,其实是《狼来了》。第一次,狼没来,第二次,狼也没来,第三次,狼终于来了,小孩被吃掉了。很可惜,我并没有从这个故事里学到诚实和勇敢,恰恰相反,我完全被吓唬住了。我养成了胆小的毛病,这个世界稍有风吹草动,我便惶惶不可终日。我为了一只可来可不来的狼而吃不香睡不饱。我还特别悲观,因为无论如何努力,狼还是会来,小孩还是会被吃掉。最终,这倒有点像是《豌豆上的公主》里的女主角,她即使隔着二十张厚床垫和二十条鸭绒褥垫,还能被一颗豌豆弄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这倒不是娇气,这完全是一种拒绝进入现实世界的神经官能症。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