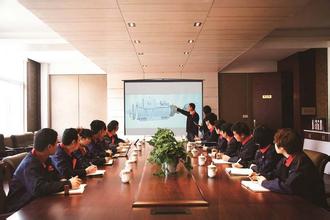
会议一般都是这样开始的。“我只说三句话……”,然后,一天的时间就这样消失在黑洞里。每一个人都筋疲力尽,觉得自己的身体是个额外的巨大累赘,只想速速去饭桌边摆脱掉它。他们抬起脚来,好像脚腕子上绑着生锈的铁锚。他们艰难地移动着、移动着,竟然终于来到了会议室门口。最后,他们把沉重的身体抬到这个悬崖边上,“嗖”的一下就消失不见,好像顺利地沉到了海底,并且再也不会漂回海岸了。
A是一位口若悬河的著名作家。他跟我说,好些年前,公开讲话是一件让他感到特别害怕的事情。他的第一次演讲就留下了阴影。“前面是张维迎,后面是周其仁。”他带着成功者的微笑轻描淡写地说,“我拿着稿子读完,红着脸走下台。”他还补充说,千万别用“我只说三句话”开头,一旦这样开头,你一定会发现自己只有两句话。
开会的本领绝不是单靠朗读报纸就能习得的,你还需要学习不说话的本领。众所周之,B是个开会高手。退出多年,然而官威犹在。他往那一坐,就是一景。他一句话也没说,可你绝对不想惹他生气。他是那种惯于发号施令和控制局面的人,并且,即使意识到这一点,他也丝毫不想掩饰这一点。至于周围的人,他们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却丝毫不想改变这一点。我在去年冬天见到他的时候,房间如此之大,无人挑战他的权威。他的眼睛间或一轮,翻译吓得直吐舌头。
在经历过很多迫不得已的勾心斗角之后,C终于如愿成为B的合作者。扑克牌翻到了正面,民主就像桌上的烟灰缸一样公平均匀。心愿达成以后,C还是和以前一样理智、谦逊、笑容可掬。所有人都想看到他歇斯底里的样子,但他这方面的才华在片场就用光了。他还自称是个“疯子”。最后他跟我说:“我是个介于疯子和天才之间的人——可这话我说不合适呀。”他的内心世界,有一部分,始终未曾开放。他是一个比其他不切实际的人更实际一些的人。他扮演的角色就和电影里一样,是个呕心沥血的杰出青年。
D是C的好朋友。他很安静,但那不是因为他没有发言权,而是出于某种克制和自我挑战的游戏。他叫人琢磨不透,拿不准他的野心和虔诚哪个更多些,他是否曾经一心想要成为什么人,当别人一心想要成为他的时候,他成了谁。
粉丝过多。每一次,D都以这样的方式离场。他像误入骷髅岛的探险船长一样,连走带跑地逃脱大批野蛮人的追逐。他的手下们无权端起轻机枪扫射,但是他们很有默契地在他身边筑起可移动的铁桶阵,每一只铁桶外头都是软钉子。
这张鸡蛋一样光滑、中间镂空的圆桌,能在它边上入座,是许许多多小人物、商人和暴发户的梦想。会开到一半,被我发现了这么一个人,他就是为此而尽心尽力奋斗的人,也是个精明的人,但是他坐在角落里,脸涨得通红,像个受惊的小孩,始终没有觉得自己是这个游戏的参与者。我的采访要求让他如释重负,因为他终于有借口去水面上透口气了。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