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国三、四线城市还处在生长期,未到升级换代阶段,但也同样面临如何取舍的问题。我觉得,这种选择应该是站在一线思维的高度,从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寻求经验教训,进行主动的、有前瞻性战略定位,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创新之路。
赶上区域经济的动车组
城市不论大小,发展总是跟周边或者更加宏观的经济区域开发联系在一起。虽然对于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大城市效果不明显,但对于三、四线城市而言,区域经济调整的优劣甚至可以在第一时间决定其以后的命运。
谈到区域经济开发,与中国最有可比性的当属美国。同为地域辽阔的泱泱国度,先行一步的美国,在城市开发与区域经济的协调方面,经验远多过初学乍练的我们。
回首美国的区域经济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成长历程,人们常常惊叹于它的自东向西依次推进且有条不紊的开发特征:19世纪上半期,美国新兴市场经济由初兴到完善,顶推东北部成为全国经济核心区;19世纪下半期,工业化进入鼎盛时期,中西部一大批工业城市兴起,与东北部经济互动;20世纪中期,西部和南部相继崛起,高科技和服务业长足发展,与东北部和中西部形成此消彼长的博弈态势。
从积极层面看,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客观上形成了分时期、有重点开发局面。每一次转移都是一个更高的起点,逐级递进。如东北部在欧洲近代经济基础之上,直接转移其工业革命的科技成果,很快成为美国最发达地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中西部靠近东北部,有地利之便,其工业化规模大,资金和技术力量雄厚,为其形成重工业区提供有力支撑;西部和南部在新科技革命的支持下,后来居上,新兴工业和服务业长足发展,其中的硅谷和奥兰治县(该县如作为一个国家看待,其GDP可跻身世界前40位)令人刮目相看。而其城市化率先进入大都市区发展阶段,为赶超东部奠定了坚实基础。
根据区域经济的区划理论,任何地区都可分为核心和边缘两大组成部分。美国后开发地区作为边缘地带,不断超越核心地区,区域经济得以优化和重组,带动全国经济发展。与之相似,我国的中部、西部作为全国经济区划中的边缘地带,在新的转型时期,也会获得同样的机遇和历史的垂青。先有美国经历在前,后有我国自身东部转型的经验教训,我国三、四线城市建设已站在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天时、地利,再加上一线思维,后来居上指日可待。
但区域经济调整是把双刃剑,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美国在其在西部和南部新兴地区的竞争面前,东北部和中西部被迫做出产业结构调整,用高科技企业或新兴制造业取代传统制造业。调整的代价是沉重的:大量工业企业远距离迁往西部或南部内陆地区,或者是从城市中心区迁往郊区,出现所谓制造业空心化。此转型历时约三四十年,方有大致眉目。但这个过程耗时费力,很伤元气,部分城市甚至从此一蹶不振,最极端的莫过于一度被揶揄为20世纪新版“鬼城”的底特律。在这些城市中心区,企业动迁后遗留大量工业用地,开发商弃之如履。与其耗费人力物力清理这些地块上的废弃物、残存化学元素和重金属物质,不如到郊区空置土地实施全新的开发。地方政府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对其进行修复,而盗贼和瘾君子的频频光顾,更加重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和复杂性,无奈之下,只好由美国联邦政府出面,发起全国性的“棕色地带”改造运动。清理成本与当初建设这些设施的经济效益相比,得不偿失。个体城市支付沉重学费的也不乏其例: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波士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铺设高速公路的狂热时代,数条高架快速路穿越市区,把好端端的市中心商业区分割得七零八落,从此经济凋敝,人气骤减。痛定思痛,波士顿人经过十余年的辩论,最终决定斥资146亿美元,实施“大开挖”工程,把十余公里长的高速公路埋到地下,以恢复中心商业区原貌。该工程历时15年,不久前刚刚完成。以此天文数字的资金缝合历史创伤,是美国市政工程史上最惨痛的一页。日本上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时期,也有大量工业设施建在市区,后来其制造业外迁,遗留地块种上了花草树木,表面看景致宜人,但每到春季开花时节,会有很多人染上奇怪的花粉过敏症,后来才发现是这些花粉含有工业遗留的有害化学元素所致。
今日的美国和日本等国,都在为当初规划失策买单。这些教训,对于正在承受经济转型阵痛的我国一、二线城市来说,是迟到的告诫;但对于伺机而上的三、四线城市而言,其警示作用却正当其时。
找准自身的区域定位
接下来的问题似乎更为明确,就是三、四线城市该如何确定在区域性经济分工中的定位。一个成功的国家或区域经济,需要的是合理组建的城市梯队。在这样的梯队里,城市之间讲究的是分工合作,协调发展。
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城市化人口达到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将进入新型城市化阶段。在此阶段,经济活动和人口流向有相对集中和相对分散两种形式。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经济活动向大中城市集中,构成不同规模的城市化区域(有大都市区、城市群或大都市连绵带等不同表述方式)。另一方面,在这些城市化区域内,经济活动又是相对分散的,其边缘地带(郊区和周边农村地区)将优先发展,结果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统筹发展。
我国三四线城市,要把握这个发展走向,有所准备。第一,尽量向城市化区域靠拢,除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地区已初步形成的似大都市连绵带外,中部和西部正在形成大小不等的城市群,都将是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重头戏。根据最新研究,中心城市周边的小城市(类似我国的地级市或县城)经济宜相对独立,与中心城市之间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不同于传统的卫星城。此类城市理想的人口规模是15万到25万之间,一般距离市中心区30至50公里。这个观点可资参照。第二,在城市建设的整体规划时有预留空间,城市和周边地区,须通盘谋划,不要全挤在中心城区。打破已经形成的“欧美的城市、非洲的农村”的尴尬局面。换句话说,三、四线城市有望成为新型城市化的主力。
但这并非意味着,三、四线城市都要向一线大城市看齐,一味追求做大做强。根据中心地学说推导的规律,城镇与城镇以及城镇与周围地区之间互相依赖、互相服务,有密切联系。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有规律性可循,城镇规模越大,其数量就越少,即城镇数量与规模成反比关系。大中小城市的经济结构要与此相适应。小城市不必大兴土木,兴建五星级酒店和CBD或总部基地,克隆沿海城市发展模式。
“城市经理制”
三线和四线城市一般规模较小,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它们更贴近市场的一面。机制灵活,反应快捷,与地方企业关系更密切,企业发挥作用空间大,这可能是此类城市的一个共同的优势所在。与企业同行,成就城市发展新战略的例证,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比比皆是。
早在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就曾有大批“城市发展倡导人”活跃在州、市两级议会厅,为城市发展建言献策,筹集经费,争取政策倾斜,成为城市发展史上一道别致的风景线。这些人,有很多是企业老总或经理人。
到19世纪末美国经济起飞时期,也是大企业的黄金时代,大企业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企业化管理。其后不久出台的泰勒制和轰轰烈烈的进步运动,更使企业化管理思想盛行一时,成为经济领域的时代风向标。
而将企业化管理思维推向巅峰的是城市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全新市政体制:城市经理制。这种体制把企业经理人制度引入市政体制和市政管理,一经推出便大获成功,好评如潮。到今天,采用这种体制的城市占美国城市总数的一半,在人口为25万以下的城市中最为流行。担任城市经理者,大多有企业管理的经历,美国企业家从此与城市管理结下了不解之缘。另外,美国实行地方政府服务外包,也为企业提供了很大的施展空间。
我国目前实施的国家创新体系,依靠的中坚力量就是企业,企业界在三四线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也将得到充分体现,大有可为。
神圣、安全、繁荣,缺一不可
资深城市研究学者乔尔·科特金在其经典著作《全球城市史》中得出结论:一个城市要持续发展,必须具备神圣、安全、繁荣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这些要求当然不仅限于纽约、伦敦、北京和上海等名都大邑,即便位居三、四线的中小城市,也同样有此诉求。
所谓神圣,是指道德操守的约束或市民属性的认同,是城市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所谓安全,指一个城市所能提供的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所谓繁荣,主要是指经济基础坚实,市场完备,运行有序。在世界历史上,因欠缺某一条件而萧条甚至消亡的城市屡见不鲜。
当下,我国城市化进入高峰期,各地城市都在千方百计求发展,对经济繁荣的关注绰绰有余。同时,由于我国总体政治局面稳定,和谐社会深入人心,拜大环境所赐,各城市安全可保无虞。但是,距离神圣的要求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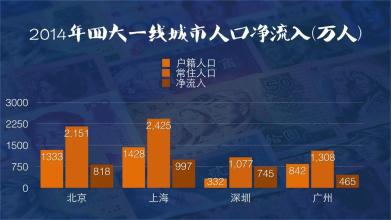
美国在其草莽未辟的殖民地时期,就很倚重文化和人文精神,“常青藤”系统很多学校相继于17世纪问世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段佳话,1743年富兰克林更在费城创办第一个哲学协会。有位美国学者这样评价:“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尽管就行业而言有90%的人口从事农业,但在文化意义上90%是城市化的居民。”
美国西部在开发过程中,处于草创阶段的城市就有了较完备的文化设施。以1848年“淘金热”起家的旧金山,5年之后,就有了2个图书馆、2个历史协会和一所加州科学院。到70年代,其歌剧院12个,有“剧院城”的美誉。西部文化与其经济一样,跨越式发展,很快与开发较早的东部平分秋色。
19世纪末,在美国工业化处于巅峰之际,由学术界牵头发起了城市美化运动,试图通过解决工业化时期城市建筑和城市风格雷同问题,规范城市秩序和礼仪。以巴洛克风格取胜的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是该运动一个典型写照,至今人们仍欣赏有加。
无论我们是把历史的镜头前推还是后移,都会看到浓厚的文化气息弥漫在美国城市空间,助推城市经济繁荣和文明升华。比照我国,悠久的历史、千差万别的山水风景与人文风俗,更是塑造城市文明的绝好基础。这一方面,我国西南许多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三、四线城市先行一步,在利用自然风景资源优势,塑造城市文明的同时,也进一步助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走出了一条经济与文化合作双赢的新路子。
说到底,文明建设和城市发展息息相关,这应该是一线思维的题中应有之义。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