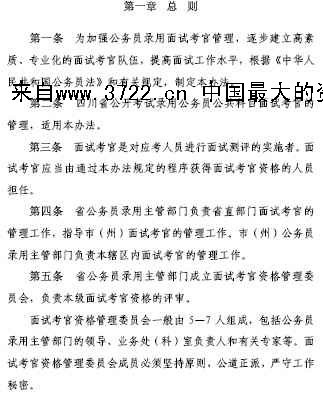——专访学者汪晖
我们要避免把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意识形态化,要批判性地思考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同时又要对已经取得的成就重新估价
汪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
《读书》杂志前执行主编。
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代表
文 | 本刊记者 丁伟
不能断裂看30年
《中国企业家》:2008年奥运会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转折点吗?
汪晖:开幕式有说好,有批评的。我基本上是肯定的。批评的人说形式主义,历史叙述不清楚,但是这些问题我不觉得奥运开幕式的导演们能负这个责任。知识界对整个20世纪中国如何估价的问题,实际上是混乱的。中国经济的起飞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经呈现了。北京奥运会让我们比较清楚地意识到,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一个事情都是全球性的事情。另外,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至于有多大的转折,我不太知道。
《中国企业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仍处于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吗?
汪晖:我可能跟一些朋友的看法不完全一样。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仅仅从30年算起。今天关于改革的叙述,有一部分过于受制于七十年代特定时刻的官方叙述,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以开放而言,中国不是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美的媾和、中日的建交都在这之前。中国重返联合国也是在七十年代初期。尽管有“反右”、“大跃进”、“文革”,但是不等同于那个时代的中国就是封闭的中国——中国跟苏联、东欧国家之间,跟拉丁美洲、非洲第三世界都是存在开放关系的。断裂是存在的,但并不是截然前三十年后三十年,而是有连续性的。没有这个前提,我认为很难解释改革开放基本的历史。
我个人对改革的成就是非常肯定的,问题是不能简单地割裂历史。官方叙述处于特定的条件,应该改变。我们今天再来看需要把眼光拉得更长一些,否则这样的割裂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今天社会面临的最大困境。简单地说,企业家、有钱人都会特别充分地估价30年,但是普通的大众、工人、农民会怀念毛泽东……一个知识分子不能看透这个断裂背后的问题,对于中国改革不是真正历史的分析。
《中国企业家》:人们回顾历史时不可避免有美化的嫌疑?

汪晖:既有美化的一面,又有丑化的一面,比如把过去说得一无是处。中国大部分人,至少在知识界主流,尤其是企业家、经济学家,都会充分肯定改革的成就。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出改革没有完成的结论,但是在讨论怎样进一步改革这件事上,结论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到了一个阶段——是摆脱各种各样的幻想和迷信的时候了,重新回到对我们自己社会经验的总结。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是必要的,但是重新做历史分析更重要。因为要避免把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重新意识形态化,这种意识形态化是阻止人们对进一步改革深入思考的障碍。无论是知识界还是整个社会,都必须展开这些问题,否则用这些空洞的教条,同时是压抑性的教条,对一个社会的再思考是没有好处的。
我记忆中的八十年代
《中国企业家》:你们这代人当年的理想、在时代大背景下的状态是怎样的?
汪晖:我觉得很难用一代人来概括。一方面它模糊得有道理,但另一方面又不是有道理,原因是一代人内部的差异太大了。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认为对于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的要求是必须的,一个文化上具有多样性的社会是绝对需要的,一个不能够被霸权宰制、拥有自己主体性的社会是需要的,一个对自己文明的信念和信心的社会也是需要的。这不是一代人,是晚清以来几代人共同的理想。过去几十年我们对当代中国有很多反思和批评,跟这种价值是有关的。不能够把改革垄断成为一部分人、少部分人的事情,这一点很关键。
《中国企业家》:你对八十年代有哪些深刻的记忆?
汪晖:现在关于八十年代的叙述,我觉得都太像一个明星似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八十年代中国改革主要的思路和主要争论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今天说的那些内容。那时候说到改革,什么样的理论是最重要的呢?比如商品经济、孙冶方提的价值规律,包括顾准很早也提出价值。八十年代初期还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异化问题,在这之后有所有制改革、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但你注意一下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是从哪儿来的?没有一个简单地诞生于八十年代。比如价值规律的讨论,最早五十年代晚期,到1975年前后有一场党内的大辩论,这些讨论到了八十年代成为改革的理论基础。八十年代如果离开了七十年代、六十年代是不能理解的。恕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很多比我更年长的人,似乎也忘记了这段历史。好像八十年代从天上掉馅饼,而且说的都是市场这些字眼。
《中国企业家》:就像胡风在建国后写的赞美诗:“时间,重新开始了”。
汪晖:今天中国社会遇到的问题,假定没有这么多批评的话,不可能改善得这么多。我1996年开始做《读书》杂志主编,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讨论——下岗、三农、环境、贫富差别、私有产权、宪政改革、全球化、亚洲金融风暴、教育改革、医疗改革、“9·11”……今天证明这些思考是非常必要的,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事实上,这些问题一定程度地获得缓解,但是也没有解决,有一些问题甚至扩大了。比如关于全球化,九十年代完全是正面的,认为全球化就是改革开放的最新阶段,可是没有思考其带来的复杂问题——民族主义、恐怖主义、金融安全、新的不平等……九十年代我们讨论发展主义,很多经济学家尤其是老一代很不满,说你们说的都是发达国家才会有的问题,可是过了不到十年,生态问题已经极端严重。九十年代中期一批知识分子讨论苏联和东欧改革,指出自发的私有化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腐败和不平等……也很快被压抑了,主流不愿意听这些意见,可是国企改革当中所产生的问题跟这个密切相关。
(《中国企业家》曾经做过“拉美化危机”的封面)我在1995年的《读书》上讲这个,当时就被批,说你怎么这么左,反对改革开放。当年拉丁美洲有“三驾马车”的问题,即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拧成一股绳,这个现象在中国已经到处都是了(典型的比如汽车工业的开放)。如果当时多总结一些经验,而不是放在一个简单的改革、反改革的框架下,把这些问题打开,对中国更好地改革很显然是有帮助的。
《中国企业家》:问个肤浅的问题:这些反思难道不是经济学家应该做的事吗?
汪晖:“我不觉得当代的经济学家有什么特别的特权能够对改革过程进行解释;经济学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学问,造诣高深者和初出茅庐者经常处在同一起点上。许多问题的解决不需要多么复杂的理论,与此同时大量习以为常的常识不时会发生很大的问题。”这是郭树清在《中国经济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中说的,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
我们是跟着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争论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坦白地说,对改革过程的了解不会比今天这个学科的很多人更少。这些公共问题即使在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着分歧,更不要说中国今天绝不仅仅是发展经济的问题。我觉得经济学家在中国社会包括言论界所居的特殊位置,是一个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其实在全世界也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做这个事儿,社会学家、人文学家都起过很大的作用。
我知道很多经济学的朋友很不满,觉得这些年舆论对他们批评很多。为什么?你的解释很多时候是无效的。有时候我看薛暮桥早期的文章,有非常实质性的内容。他回忆在抗日战争时期怎么利用货币政策、市场要素来进行解放区的变革,才会发现他们那代人对这些东西也不陌生……我们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都看不起前头的人,再看看人家曾经做过的工作就知道,没那么简单。就好像现在有人说中国第一回有市场,这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是。
打破教条,丢掉幻想,继续战斗
《中国企业家》:置身改革大潮,你们感受到时代的风起云涌吗?
汪晖:我们在八十年代肯定感受到改革风云,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很多导师们都是直接参与改革的。我们二十多个博士跨学科在一起,左的右的都有,郭树清搞宏观经济,樊纲比较早主张私有化,左大培研究弗莱堡学派,王逸舟研究政治经济学……我们这个小小的集体里发生了很多争论,比如说吴敬琏这一派和厉以宁这一派围绕着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的争论,都是在我们那个空间存在的。置身其中不置身其中既有差异,但是还依赖于不同的人站在什么历史视野里看待自己经历的事情,也就是说反思能力的问题。
《中国企业家》:八十年代以来有哪些有影响的文化思潮?
汪晖:我觉得很难笼统地讲。八十年代早期有思想解放运动,也有文学运动。中期以后有新潮小说、前卫艺术,涌现了尼采、存在主义等思潮。到了九十年代逐渐重新开始对传统和历史的再总结……但是回头看,这些过程中有一些泡沫,比如存在主义,今天还有多少我也不太知道了。我们对于任何一个潮流都需要加以警觉,对它的边界进行界定,因为即使是再伟大的进步,也总有它的另一面。我们在《读书》做了十多年的讨论,不管引发了多少争议和批评,几乎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被承认是真实的问题。其实十来年算什么预见性?可在今天还在继续讨论这些问题。这个社会越来越短视,各种各样的言论、政策往往是直接的、应付性的,缺少长远的历史视野,这是普遍的状况。
《中国企业家》:任何国家转型期都经历过各种冲击,中国这是一个特例呢,还是……?
汪晖:像中国短期内这么大规模、而且是在全球化下发生的剧烈转变还是非常特殊的,是很了不起的。我们跟发达国家比有很多问题,这个没有错,可是中国人在三十年当中发生的巨变,你不能怀疑他的创造性。(李敖说,现在“形势大好,人心大坏”)还有一个说法叫“乱七八糟,生机勃勃”。中国确实有活力有能量,但文化的创造不是依靠于一时的,需要很长的时间,经济的发展已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中国企业家》:“自由主义”批评“新左派”站在想像的世界里批判现实世界的不合理,后者反唇相讥,前者是否站在想像的世界里认同了现实世界的不合理呢?这种争论是在饶舌吗?
汪晖:无论你对现实、未来的思考,没有想像和理想是不可能的。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他是不是有理想,而在于这个理想到底从哪儿来的?是从历史实践里来的,还是一个单纯的空讲?汪丁丁跟我的讨论发生在1999年,可是那个基本问题在今天我不觉得有多大的争议性。我大概是最早对哈耶克主义在中国的流行提出批评,不是说哈耶克理论不重要,我是反对教条——把市场化兜售成自发秩序这种说法,历史上完全站不住。必须打破不切实际的幻想,批判性地思考必须从中国自己的历史进程里总结,任何简单照搬都是不对的。但是想像仍然是必要的,没有想像就没有前瞻性,没有超越,没有未来。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