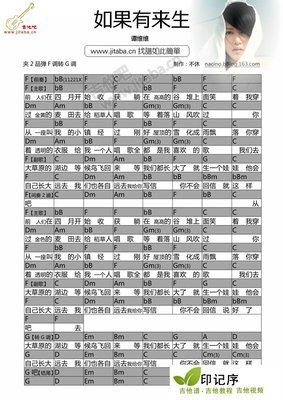崔健,吴思,龙永图,他们在见证中国转型30年的同时,自身也成为这个国家转型的符号,或主流或边缘,但统统都被时代淡忘
采访 | 本刊记者 刘建强 丁伟 雷晓宇 杜亮 蔡钰
文 | 本刊记者 刘建强
崔健。吴思。龙永图。
三个人互不相识。对这一组合,也都无异议。
并非风马牛。
先说崔健。已有定名,中国最伟大的摇滚乐歌手,以其横空出世的音乐为中国人打开一个无限广阔的精神世界,无数人的愤怒、悲伤甚至绝望通过崔健得到化解。毫无疑问,崔健的音乐被当作了对抗主流意识形态的武器(虽然并非他的本意)。崔健带来的并不是混乱,他从半地下转为地上的历程,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思想从一元变为多元的历程。
吴思。与崔健一样从体制内出来,寻找观察中国社会的最佳角度。如果说崔健曾长时间背负政治压力,吴思更多的时候则是面对自我的追问。他从一个极左的知青到一个不断超越自己的自由思想者的历程,就是中国人的思想从蒙昧到启蒙、从感性到理性的历程。
龙永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首席谈判代表。人们从龙永图身上看到的,是中国政府打开国门的决心和为此付出的努力。而在此过程中,又夹杂着来自民间的以崔健和吴思为代表的启蒙力量的被压抑。
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崔健由精神偶像被还原为一个普通的音乐人。这是权威打破者的必然归宿,尽管他可能有些失落。与此相似,当中国加入到经济全球化行列中后,作为曾经显示中国这一努力的符号,龙永图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在贡献出“潜规则”这一概念后,吴思的历史研究也被“百家讲坛”、《明朝那些事儿》之类的事件淹没。
30年来,时代面貌由革命的、激情的、浪漫的转为现实的、功利的、善变的。我们正在经历的可能是一个平庸甚至浅薄的时代。
也许这才是常态。
1978
1978年,在北京郊区插队的吴思拿到了高考成绩单,远远高于录取线。那年他21岁,已经在那里插队两年半,担任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副书记。停止10年的高考于1977年恢复,因为在公社的大喇叭里表过“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远扎根在贫下中农的心里”的决心,吴思当年没有参加。
看到成绩通知单,“我心中一阵狂喜,却故作镇静,不紧不慢地踱回宿舍,提了镰刀,按照往常巡山的路线出了村。走到荒僻处,终于按捺不住,一口气跑上十几层楼高的山梁,毫不气喘,兴犹未尽,又蹦了几个高。平静下来后,我为自己的反应大吃一惊,也为自己的大喜感到羞耻。我怎么这样?不是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吗?我那么想离开农村吗?我还以为自己对农业学大寨的伟大事业恋恋不舍呢。由此我也得到了一条经验:人们往往并不了解自己。”(吴思《我的极左经历》)
那时候,吴思怀抱的改造农民的想法已经产生了动摇。农民们对通过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进入共产主义毫不积极。“对自私自利的小生产者应该继续进攻还是维持现状,还是让步?”吴思带着这个问题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原来装了一脑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生活中被证伪了,受挫了,遇到了问题。这就是改革开放对我们来说的起点。”吴思说。
这一年,17岁的崔健已经吹了3年小号。这个朝鲜族小伙子偶尔会想起两年前毛泽东逝世。“当时有个遗憾,就是大家都想见他一次,结果没见着他就死了。”
这一年,龙永图35岁,身在纽约,是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随员。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他早不再感到惊奇。1973年,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要派十几个人到英国学习经济,委员会主任方毅想起自己被“打倒”时曾受到当时新分配来的大学生龙永图的照顾,就把他找来说:我看你就是品质好,你去。“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得到了一次去英国学习的机会。”龙永图说。乍到英国,但见汽车遍地、速度奇快,龙永图大受刺激。
其时崔健正待在北京的大院里,“特安全、阳光充足,每天就玩,不用上学。全世界我们最幸福,台湾人民等着我们去拯救。”国内的人忙着写大字报,龙永图在英国苦读,英文水平大进,为他20年后出任世贸谈判首席代表打下基础。
龙永图从外国人眼中感到了中国在进步。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方针确定,中国一改多年来拒绝任何国家援助的立场,这一变化让联合国官员非常吃惊。
在纽约,龙永图每个月有19美元的补助,可以全部攒起来。回国时,他带回去的一些小家用电器如录音机让家里人大开眼界。
1981
崔健进入北京交响乐团,成为一名专业小号演奏员。从一些外国留学生和旅游者那里,他听到了约翰·丹佛等人的磁带,并开始学习吉他演奏。这是一种他倾注了远比小号要多的激情的乐器,而且成为他日后舞台上须臾不离的武器。
大学三年级的吴思梦见了毛泽东。“当时人们都觉得做梦梦见毛主席是报纸上的假话,特别假的学毛主席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那会儿毛主席已经死了多年,但是我是真的梦见了毛主席。(梦里)毛主席在怀仁堂看戏,在我的前面第三排,我在他的左后方。他就一个人坐着,周围没人。我就探头看他,问能不能跟您说句话?他说行。”吴翻过两排椅子坐到毛身边。“我说,毛主席,您说的农村那个搞法,我非常认真地做了,不行,真是不行……我一肚子的东西在那儿,就是找不到一个简明的、一说他就能懂的话,最后就憋醒了。”
吴思的班里一共53个人,只有六七个应届毕业生,其余不是插过队就是当过工人,有一位已经生了四个孩子。“对农村问题最耿耿于怀的一个人就是我。”吴思说。他当时是班长。
吴思回忆,几乎所有同学都对前人的理论、大学要传承给他们的东西抱着很强的怀疑态度,很多事都会跟老师争。“甚至在考试的时候都不按照标准答案答,虽然也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于是大学对那几届的大学生来说,我们就不是到这儿来受教育的,就不是一个知识的接收者。我们到图书馆去看看法国人怎么说,英国人怎么说,美国人怎么说,还有民国的时候人们怎么说。但还是找不着一种让我们服气的世界观、一种解释。”作家阿城曾在查建英所著《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谈到,当时的大学教师对他们这些有复杂社会经历的学生很头疼,因为太不听话,但后来教师们又为再找不到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遗憾。
龙永图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总部区域项目官员,为中国开始接受联合国援助感到高兴。
1986
这一年的崔健已经被无数次地描写过。在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这个打扮得不伦不类的“歌星”第一次把《一无所有》喊出来。
“从字面上看它就是一首情歌。”2008年9月,47岁的崔健对我们说。从他说话的语气看,听众只愿意承认这首歌的政治含义这一现实影响了他。很可能,在崔健之后的摇滚道路上,他在不自觉地向他的观众靠拢。他们塑造了自己的代言人。
“当时首先开始不信任自己。”崔健回顾说,“从小的时候我们被灌输说我们是最好的,首先从这儿开始怀疑。比如说录音机是日本的好,音乐是美国的好,什么都是洋货好,外国人比咱们有钱。这些东西逐渐给我们带来潜移默化的自我怀疑——根本就不能叫怀疑,就是不堪一击。”在这一年前后流行的《乡恋》、《军港之夜》、《冬天里的一把火》以及更多的港台歌曲中,崔健迷茫又坚定的声音成为那些在新时代感觉失重的城市青年们互相认同的一个标签。崔健对于旧世界是留恋的,他表现的形式又是暴力的(摇滚乐加嘶哑的呐喊),这一奇怪的组合正显现出那一代城市青年对待变化莫测的时代的矛盾态度。
当崔健开始对之前价值观的反叛的时候,吴思也在试图重建自己的世界观。在农村,包产到户激发出惊人的生产力。吴思感到了震撼。“我做的那个梦(梦见毛)就是要向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妥协,但是分田单干,根本不敢想,我认为这是全面溃退,一夜回到解放前,退得太过分了。可是我心里知道突破教条后是什么样,因为我知道农民在自留地里面是怎么干的,在集体的地里是怎么干的,我也当然知道你把所有的地都变成自留地会怎么样。知道和真的看到还不一样,一看到还是深受震动。实际上我们自己心中早知道那个东西是对的。”
这时候的吴思已经成为《农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他显然是一个适合当领导的人)。在之前的一次调查采访中,他和同事合作写出了关于开封农民买不到“挂钩肥”的报道。按规定,农民在平价交售农产品后,国家应向他们平价销售化肥,但是在开封,农民们只能买市场上的高价化肥,“挂钩肥”都被有支配权的人“批条子”批走了。吴思的报道揭露了当地资源分配的另外一套规矩,并名之曰“内部章程”。这就是十几年后吴思提炼出的“潜规则”一词的前身。
龙永图来到朝鲜,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朝鲜代表处副代表。他从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度,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期间,他组织了一批朝鲜官员到深圳参观。
这一年,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申请,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方地位。
1992
邓小平南巡讲话,一度沉寂的改革重新启动,不带任何前缀的“市场经济”确立。
“这时候对市场经济已经没有什么抵触,知道它一路下来会成功,”吴思说,“只是觉得这个世界一下子成为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有点儿遗憾。”此前,吴思读了《资本论》。“我不得不学,”他说,“我以前一直顺着这个路走,没走通我觉得不是马克思的问题,我认为是自己没学好。那么,我只有学精学透了才能说走不通不是我的事,是你的事,不是我不懂你,是你的路就是走不通。”当吴思解决了自己“强迫症”一样的思想问题后,心里还有最后一个结:为什么大寨能成功,自己学大寨却失败了?
其时他已经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只是机动记者组的一个记者。他学习英语准备考托福出国。有人反映机动记者组有几个人整天不干活,社长找吴思谈话,问他“大家都有意见怎么办”?时任《农民日报》副刊部主任的刘震云给他出主意:你给我们写连载,然后你出你的国,写不完也没关系。吴思说自己想写陈永贵,想弄清楚为什么学大寨都失败了。
1993年,《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出版。书写完,吴思得出结论:不是我不好好干,实在是大寨这条路只是在各方面力量都很强的情况下,在局部才走得通。此时,吴思打消了出国的念头。
专辑《解决》在1991年发行后,崔健开始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全国巡回演唱会。他把自己对这个巨变的时代的思考、怀疑、嘲讽传达给更多的人。“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崔健带来的既是一个精确的诊断又是一剂对症的泻药,他替他的听众喊出了面对社会震荡的无力感,为那些想要重建健全心灵的年轻人提供了这种可能。“我愿以生命为代价去拥抱的不仅仅是一个作为歌星的崔健,”一位听众给崔健写信说,“而是一个理想,一个标志,一种精神的象征。”(赵健伟《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一无所有》出世六年后,崔健很快达到了他的巅峰。此后,对他的演出的限制巩固了他的“精神偶像”地位。
此时,为了改变西方对中国的态度,中国政府对外开放的力度较80年代更大。中国要求进入实质性“复关”谈判。一个偶然的机会(给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李岚清会见外宾时当翻译),龙永图与这一旷日持久的谈判紧密联系到一起。没过多久,龙永图被调到中央党校学习,1992年1月被任命为外经贸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很快开始参加复关谈判。“如果没有那次给李岚清同志做翻译的话,我也许当不了这个谈判代表。”龙永图说。1965年,龙永图从贵州大学外文系毕业刚分配到北京工作,因为一直没有跟外国人用英语交流过,所以在一个博物馆看到两个外国老太太就找机会上前搭话。他因此被警卫带到公安局盘问。坐在谈判桌上想起往事,龙永图一定感到恍如隔世。
1994
先是张楚《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何勇《垃圾场》、窦唯《黑梦》出版发行,稍后崔健《红旗下的蛋》问世。这些中国最优秀的摇滚歌者不约而同对横扫一切的商业做出了批判,与当时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彼此应和。“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像红旗下的蛋。”这是30年改革开放中间的一次阵痛,很快烟消云散。这种批判可能有对市场经济的误解,但更多的是对没有信仰支撑的市场经济的愤怒。
吴思从《农民日报》出来在香港明报集团投资的《桥》杂志工作。他在《农民日报》月薪105元,明报集团主席问他希望在《桥》拿多少钱。“我们壮着胆子说了1300元,其实对他们来说跟玩儿一样。”吴还想着《农民日报》的关系不能断,却被嘲笑:“瞧你们大陆人这点儿出息,你在这儿一个月挣那儿一年的,有什么放不下的?”《桥》出版三期后停刊,随后明报集团的各种业务撤离大陆。吴思失业了。他开始阅读《明史》。
龙永图成为外经贸部部长助理。
1998
“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你说所有人的理想已被时代冲掉了。看看电视听听广播念念报纸吧,你说理想间的斗争已经不复存在了。”(《混子》)崔健这一年发行的《无能的力量》继续了对时代的批判,但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跟以往相比,崔健新专辑的发行已不能称之为“事件”。一方面,他过去的愤怒很多时候变成了牢骚,另一方面,受他的音乐启蒙的一代已经在日趋多元的社会格局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崔健完成了他的伟大使命。
吴思进入《炎黄春秋》杂志社。受《上海文学》之约,他开始撰写有关明史的专栏。他组合出一个描述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的词汇:潜规则。在随后几年里,这个词迅速流行,成为人们概括当下现实的方便工具。吴思前些年投入股市的8万元增值了数倍,在股价有所回落后他全部卖出。
已经没有人再离得开商业。
香港于一年前回归。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但是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将近8%的增长。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正在成为这个社会的明星。经济成为社会的主要话题。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名气越来越大。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谈话:“有人以为中国政府不再把加入WTO当作一个优先任务,这是一种误解。我认为中国越早加入WTO越好。”

“我的谈判风格比较坦率,”龙永图说,“我能够做出让步的时候我就说我能做出让步,我不能做出让步的时候,特别是在那些关键问题上,就非常明确地告诉对方: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没有谈判的余地。现在我们碰到以后都是很好的朋友,因为那么多年,他们一直觉得我有时候虽然很生气,有时候也非常强硬,但是有一条,我没有故意欺骗他们。”
龙永图为实现国家意志所进行的艰苦谈判得到的并不都是好评,后来有人指责他在纺织品配额等问题上的让步是“卖国”。当然,在指责中,他也只是一个被借用的“符号”。龙永图为此对我们辩解说:“比如今天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将来会证明现在普遍的反对态度只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2005
这一年,崔健再次站到北京的万人舞台上,距离上一次过去了12年。
此刻登上时代舞台的是“80后”甚至“90后”,互联网成为他们的广阔天地,给他们带来更平等的话语空间。“芙蓉姐姐”在网上迅速走红,娱乐化一切成为时代主旋律。
中国已于2001年加入世贸,龙永图也在2003年离开仕途,受聘成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我的性格不适合当官。”龙永图说,很多人为他没能最终当上部长抱憾,他并无同感。
44岁的崔健谈及这场名为“阳光下的梦”的演唱会时说:“好像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因为这世界上有一群仍然坚持梦想的人。这场演唱会就献给仍然在坚持梦想的人们。”
演唱会上,崔健更愿意演唱他这一年发行的新专辑《给你一点颜色》中的歌曲,观众则更希望看到“新长征”时代的崔健。这是崔健无法超越的宿命。对于当下,每个人都只愿意相信自己的解释。
几年中,吴思先后出版了《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和《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后者没有引起前者那么大的影响。当时还没有“百家讲坛”。
2008
年初,崔健在北京再开《时代的晚上》演唱会。他看到工人体育馆的停车场上停着很多辆宝马、奔驰。“我的头发蒙。”崔健对我们说。
吴思希望自己能构建出一个与马克思主义比肩的理论体系。“这是我给自己规定的使命。”他说。
2008年8月8日,龙永图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80余位各国政要出席。“越是开放,就越安全。”他感叹。
龙永图打算成立一个基金会,用以帮助那些贫困的农村孩子接受教育。他在国外多年,不习惯喝洋酒、吃西餐,一听音乐会就睡觉。他不太了解崔健,但知道崔健版的《南泥湾》曾激怒了某位老干部。
他们现在只代表自己,他们成为了“个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