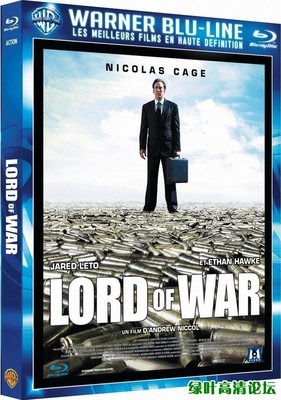谁在决定中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政府意志、商业利益、人文理想如何博弈共生?
文 | 本刊记者 雷晓宇
这还是我们熟悉的北京……和中国吗?
1988年,女作家林海音(著有《城南旧事》)重返北京,旧地重游,看着眼前面目全非的一切,难过地说:“我的城墙呢?!”
1999年,当美国哈佛大学规划系教授莫什·萨夫迪(著有《后汽车时代的城市》)重返北京时,难以相信那是他1973年第一次见到的城市,“二战后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城市建设,因而有机会从西方的错误中学到许多东西。”然而,他很遗憾,北京已经重蹈了西方城市化曾经的覆辙。
2008年,在关于旧城保护的《城记》热销五年后,新华社记者王军再次推出《采访本上的城市》,反思中国式的造城运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对他说:“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好好思考城市的本来意义了。”
在外国建筑师的这块“东方淘金地”、“实验田”上,中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式造城”模式。“鸟巢”、“巨蛋”、CCTV新大楼、“东方之冠”(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诸多标志性建筑展现了中国拥抱现代主义的努力,成为中国崛起的外在象征。
用十几年的时间爆发完成了西方数十年走过的路,中国的城市建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城市中国》杂志总编匡晓明对《中国企业家》说。
匡是“中国式造城”一词的始作俑者。他解释道,“中国式造城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模式,是政治经济文化各因素叠加所造就的疯狂速度,不是单方面促成的,也不是我们崛起了有意搞的结果。首先,体制上要快速决策,必须有效。然后政府要把钱吸引过来,如果自己没钱,就得把土地变现。第三,要扩大内需,土地兑现了卖不掉也不行。第四,产品还得出口,中国发展,世界买单。”
CCTV新楼设计师雷姆·库哈斯了解中国的国情,“我们在做一件在市场经济中绝不可能的事……CCTV新楼显示了当代中国的政治能量和经济能量。”他乐得见到这种“不可能的状态——改变着世界,却没有蓝图”,至少建筑师们可以接到很多活。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建筑热潮的洗礼,起重机、脚手架和想像力处处可见。北京有上万个建筑工地,占地面积近乎三个曼哈顿,耗资约1800亿美元,有人说,这是自修建长城以来中国最宏大的建筑工程。挑战重力和人们视线的新地标给人以一种晕眩感。不过,也许就像美国著名城市规划评论家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中写的,“我们用金钱扼杀了千姿百态的城市多样性,这有点像温柔的谋杀。”
在中国各个城市挥洒金钱、心血和想像力的建筑师、地产商、官员们因而受到争议。设计师欧宁对《中国企业家》说:“人们发明城市规划这个专业,原本是希望延长城市的寿命直至永恒,但不幸的是它常被称为城市的杀手;有人认为地产商们是为城市添砖加瓦,而历史保护主义者则认为他们惟利是图;有人认为建筑师们是城市的建设者,但有人也批评他们耽于自己的梦想,把城市当成白板……”
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张永和说:“今天在中国经历的是一场真正的文化变革,但那纯粹是出于经济发展目的,我们的城市没有变得更好。”
那么,是谁制造了这一片喧嚣?中国城市化进程背后有哪些推动力量?政府意志、商业利益、人文理想如何博弈共生?中国能够避免西方的弯路吗?这到底是灾难还是福祉?
奥地利一家“资产一号不动产开发公司”,购置了该国第二大城市格拉兹市中心129英亩的土地,其第一个产品不是设计图样,不是估算书,不是招标文件,而是一本名为《城市对自己的未来应当知道些什么》的书。32位市民,包括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工作者、企业家和学生等在书中探讨2017年的城市将是怎样的。中国能有类似的版本吗?
从经济角度来看,城市化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指标。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报告,2006年中国城市总数为661个,城镇人口57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43.9%,占全国GDP的比重为63.2%(132272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9.3%。
“大势是谁都挡不住的,”已经算比较有文化追求的地产商潘石屹说:“未来中国经济还会快速增长,将有几亿人加入到城市化的过程中,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最大迁徙。只有当你顺应了这些大趋势,你所做出的努力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才能得到市场和社会的承认。”老潘也谈城市复兴,却不讳言利益,“中国房地产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我不断地建办公楼,是完成这个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活着而聚焦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聚留于城市。”人类对于城市的想像从未终止,从古希腊的城邦,到狄更斯的“焦炭城市”,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然而,“现代社会从根本上禁止任何想要论证其合法性或局限性的企图”,海德格尔说。面对城市化的大潮,任何描述和批判都显得力不从心。陈丹青说:“我们还活得太近,近得没有资格评价今天的事情。从正面说,中华民族的承受能力、再生能力是非常强的,这绝对是悲剧,也绝对是喜剧。”
在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马可·波罗对忽必烈讲城市见闻。后者问,威尼斯呢?马可笑了,“你以为我一直在讲什么?每次我描述一座城市时,我都讲点威尼斯……也许,我不愿意全部讲述威尼斯,就是怕一下子失去她。或者,在我讲述其他城市的时候,我已经在一点点失去她。”我们在失去什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