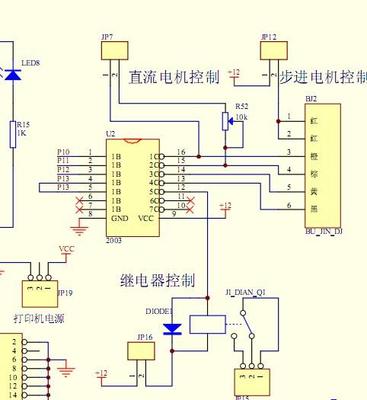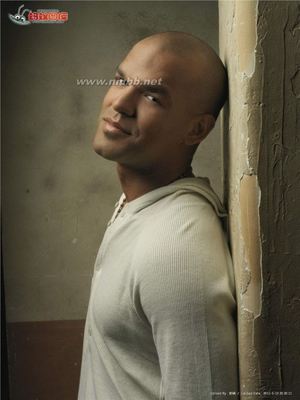为什么那么多国外政客在退休以后都开始对气候问题津津乐道?
文 | 本刊记者 雷晓宇
好吧,我得承认,这次我是标题党。我并未和前任英国首相共进下午茶。
不过,这个标题仍有出处。第一,3月18日,我的确在北京丽晶酒店见到了他,并且和他共处一室长达25分钟;第二,2006年11月,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位记者的确就气候问题和阿尔·戈尔喝过一次早茶,并且问了他三个问题:对大选失败作何感想;我们还能搭乘廉价飞机吗;凭什么不让中国人享受现代生活。戈尔当时的回答老练又聪明,让我在出发之前幻想,我是不是也能照样子跟托尼·布莱尔说说话、喝喝茶。
但是,我不但没有和他在这个黄沙蔽日的北京午后共进一次下午茶,甚至连话都没跟他说上一句。在一个房间里还有另外200多人的时候,你很难找到机会跟一个曾经在唐宁街十号呆了十年的人打招呼。
从布莱尔走进房间的那一刻起,我知道,很多在场人士都在苦苦压抑自己想要跟他合影的愿望。我身边的一位女士跟她的男伴说:“你觉得他什么时候讲完?我什么时候过去比较靠谱?”很多人其实并不太在意,布莱尔此行是参加由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和他发起的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主办的“中国企业与低碳经济”论坛。
他扣上深蓝色西装外套最下面的一粒扣子,从第一排中间的座位上站起来。他走上前去,给了上一位演讲者、阿拉善SEE会长王石一个眼神,然后从秘书长杨鹏手里接过话筒,又给了他一个微笑。他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这种公众微笑,开始发表他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观点。这微笑加深了他脸上的皱纹,但是因为他的脸并没有明显松弛的迹象,所以这皱纹并未减少他的魅力。他双手撑住小桌子的两端,然而身体保持笔直。他的肢体语言和说话方式跟以前在英国国会里并无不同。
提问比答案更精彩。有人问他,美国次贷危机会给低碳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担任美国摩根大通银行高级顾问的布莱尔也没说出什么新鲜的。他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强调,气候变暖问题很重要,我们都该做点什么。他说:“气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环境的事件,而是和其他的一些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事件都是相互关联的。”的确,这次来北京之前,他先在日本东京的二十国集团环境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次离开北京之后,他又会去美国耶鲁大学,举行一次同样主题的讲座。
布莱尔并不是我们见过的最出名的外国退休干部。3月18日这天,正好是美国发动伊战五周年。这一天,布莱尔的前盟友小布什在准备次日面向全国的纪念讲话。一年前的这一天,是克林顿第一次和希拉里共同出席她的总统竞选筹款活动,如今,决胜时刻也要来了。同样在春天,阿尔·戈尔做着和布莱尔现在一样的事情,并且已经凭此拿到了奥斯卡奖和诺贝尔和平奖。美联社曾经评价说:“布什和戈尔,代表战争与和平。”
为什么那么多政客在退休以后都开始对气候问题津津乐道?布莱尔曾因为对气候问题反应迟钝受到指责,就连戈尔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也并没有在气候问题上有突出的表现。等到退下来了,反而摇身一变,这是什么意思?有人在为布莱尔叹息,叹息戈尔比他退休早点儿——“有个人在唐宁街呆了10年后很不情愿地卸任,他很不开心地意识到:自己在能力和道德方面的声誉已经因为伊拉克战争而严重受损,他正在设法补救——现在他希望做些毋庸置疑的好事,他想挽救一些东西;比如气候变化,但阿尔·戈尔已经占据这市场;他渴望挽救非洲,但没有正式职位可申请……”
虽然没和布莱尔一起喝下午茶,但我和现场的人一样,至少感受到了他带来的碳排放的风。他对中国的企业家们说:“很多的商界和政界领导人都产生了一个共识,就是从现在到2010年之间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和挑战期,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理智的政治上的全球气候协定,这样才能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减排。”
 爱华网
爱华网